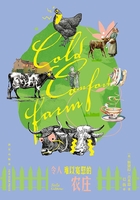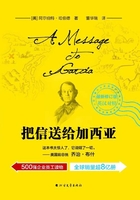搬出去的那天,王向阳很洒脱地对姚一红道别:欢迎早日归来。姚一红没有答话转身走了。她想王向阳应该知道,新的《婚姻法》规定,分居满两年,就可以无条件离婚。王宣在一边看着,对他们富有潜台词的表演感到索然无味。
但是,真的搬出来了,架势都拉开了,姚一红却没有勇气告诉“他”自己的行动。不知是觉得自己底气不足,还是害怕“他”最终的态度。这有些像玩扑克,到最后,快要翻底牌了,也许是张好牌,成就两家的兴旺,也许是个烂角,坏了满盘的风水。
或者,她之所以突然犹疑起来,只是由于一个电话。
在电话里,他们偶然谈到了一个明星的离婚事件,这是晚报上的娱乐新闻,说到底他们也都不是真的感兴趣,但既然谈到了,也就顺便说了几句。
姚一红是故意停在这个话题上的,有些借“题”咏志的意思:“我赞同她离婚。只要是因为爱,结婚是对,离婚也是对,因此,在离婚这个问题上,对当事人进行通常意义上的道德评判是没有意义的。”
“是吗。我倒有些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离婚都是一桩丑闻,都会引起人们恶意的猜测和联想,也是当事人是对个人尊严的放弃和否定……同样,只要是有一点头脑的人,就会明白,婚姻本身就是个悲剧,一会儿结了一会儿离了一会儿再结了,这都是白费力气,只是从一个悲剧进入另一个悲剧而已。”
姚一红不敢再继续下去了。她不知“他”只是泛泛而谈呢,而是有所暗示。但这次的通话给了姚一红一个提示:在她与“他”的交流上,他们显然还有很多空白点,这些空白点,也许就是共振点,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升华和愉悦;但也许,空白点就是分歧点,会成为某种陷阱和误区。无论如何,姚一红明白,她现在应该从“务虚”阶段进入“务实”阶段了。
于是,在搬出来的第二个礼拜,姚一红主动约了“他”再次见面。前面,我们知道,他们在刚刚重逢的那个阶段,有过一些频繁的约会,但最近半年,他们很少见面了。而现在的姚一红,从心理上看,有些“新生”的意思。因此,这次的见面,对他们来说,无疑是相对隆重的。我们也终于可以近距离地看看姚一红的这个“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
虽然是姚一红的提议,地点却还是“他”的定的,在他公司附近,一人一份简餐边吃边说。一方面可以节省时间,另一方面也显得不那么正式,以减轻约会双方的心理负担,对于姚一红,这的确是很必要的铺垫。
好了,现在可以看见,他们见面的地点我们很熟悉,对,就是那家楼下是红尘楼上是天堂的“早点茶社”,毕竟,这里对“他”比较方便,发生什么或不发生什么,“他”并不想避讳什么人,“他”做事一贯喜欢落落大方。
“他”来了,像姚一红心目的标准绅士那样提前到了,风度翩翩、顾盼自若——没错,你跟我猜得一样,姚一红的这个同学、这个“他”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前面早就认识的ED患者郝青白。
其实,早在王宣找到工作的那天,从姚一红的吃惊和她高超的掩饰里,我们就能感知,她对“大郝”公司有些敏感。是的,姚一红那天就知道,儿子进的是“他”的公司,但她真的很能保守秘密,至今,没有人知道这个巧合。一个秘密就孕育着一个故事,就像泥土孕育着一枚种子似的,不知道,这枚种子会在什么时候破土而出。也许,这秘密对郝青白并没有什么,对王宣,对青蓝,包括对王向阳,却是有些什么吧……
接着是准点赴约的姚一红,提前五分钟,她出现在马路上。远远的,透过“早点茶社”二楼的雕花窗户,带着一点俯视,郝青白看到了她。
她还是那样,跟二十五年前走在大学的操场上一样,在人群中像个女皇那样卓尔不群,自信、神秘、平静,同时充满着无法言说的女性风情。从那时到现在,郝青白最喜欢的就是她置身在人群中的这种与众不同的神采。他发现自己欣赏某样东西或某个人的方式跟别人有些不同,比如姚一红,所有那些追求者都折服于她的美貌、才气以及高傲,可是有谁注意过她在人群中的神态吗——她与大家一样在走在说在笑,可是她却与所有的人都保持着一种距离,好像她被一种特殊的气息所环绕着似的……
姚一红从郝青白的视线里消失了,他知道,她上楼了。果然,他回过头,看到她从楼递转弯处的屏风后出现了,走近了,对着自己微微点点头,接着她绕过桌子坐下了。
整个茶馆,突然一下子变得安静下来。
也许是出于一种默契或者惯性,没有炽烈的眼神或温热的拥抱,他们只是像两个熟人那样平平常常地坐下,一边点菜一边拉拉杂杂的闲谈。他们所醉心和追求的方式就是这样:尽管心中千言万语,但表现得大音稀声镇定自若。他们很少长时间的凝视,但是他们都知道,对方在看自己。太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们需要一个渐进和复苏的阶段。
过了好一会儿,郝青白才慢吞吞地有些斟字酌句地说:“一红,谢谢你提议的约会,很久了,只是听你的声音。不过,对我来说,那似乎已是我们交流的最佳形式……前一阶段,我曾经考虑过一件事,不过,最终放弃了,具体的原因……上次在电话我也提到过:反正都是悲剧,变来变去没有太大意义。总之,现在这样很好,我想我的生活还会保持原样,不会再有任何变化。”
在接到姚一红的电话时,郝青白就开始琢磨这段话,本来他以为他会难以启齿,没想到,说了也就说了,四周还是安安静静的,对面的女人还只是垂着眼睛。
是的,前一阵子,由于与姚一红的重逢,由于突然掠过他心灵的颤栗与感动,郝青白的确考虑过离婚。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对他是一个艰涩的命题。在对身体完全绝望之后,在半睁半闭地听任妻子与别人私通、并与其达成一个某种攻守同盟之后,他早已对自己的情感出口、入口已经全部打上了封条,在心底里,他已经预先把自己当作了一个废人,性无能了,爱便也无能,还能怎么样呢,爱上一个女人是罪过,被一个女人爱上同样是罪过。一直以来,在保守生理秘密的同时,他还在心理上保持着高度的警备,他告诫自己,要像远离病毒一样远离女人,他不想在这方面浪费无谓的时间与精力,增加那些枝枝叉叉的烦忧。
那么,怎么又会跟姚一红有了如此深入的交往以致最终让他动摇了信念的呢。也许,就像一个一直处于高度警惕状态的战士偶尔的疏忽吧,也许是姚一红的同学身份麻痹了他多年紧绷的神经吧,也许是他的生活中的确需要一个小小的安全的出口吧,他就那么顺其自然、毫无戒心地开始了与姚一红的交往,看着她,被她看,跟她说话,听她说话,一起吃饭,坐在不开灯的车子里看外面的人……不存在性别意义,没有任何暖昧的倾向,多么愉快,令人放松,他感到自己的脾气都开始变好了,那些应酬、客套、聚会、谈判、合同等等好像重新有了发生存在的意义,并变得可以忍受……
当郝青白发现自己渐渐习惯、依赖直至沉湎于与姚一红的见面乃至通话之后,他有些吃惊,这是怎么了?当心,她是一个女人!一个感情动物!他很快进行了严厉的反省与追究,最终,他勉强承认并接受了自己的失误,的确,他走得太远了,完全没有克制,不加防备……但是还好吧,并没有太大的破绽吧,他对姚一红说过什么吗?他流露过什么吗?没有,什么都没有!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必要立即中止呢!就像把伸出去的手重新缩回?把绽放出的笑容重新停止?不,郝青白马上否定了这一假设,为什么非得自我断送掉生活这唯一的点乐趣呢?为什么所有的婚外异性交往都要指向一种世俗的结局呢?就算一定要刹车,为什么非得是他来动手呢?姚一红不也是另一个当事人吗?为什么不能把主动权让给姚一红呢?
在郝青白的眼里,姚一红一贯那么富有主见,有方向感,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了,那么多出色的男生追求她,可是不,她到最后偏偏选择了一个普通得都让人不敢相信的建筑系学生,光凭这一点,郝青白就可以断定,姚一红是个自给自足、意志坚强的人,她这样的女人,不会落入情感生活的俗套,对可能发生的伤害,她天生就具有高度的免疫能力。所以,一切就由它去吧,她应该知道事情可能出现的各种局面和走向。
的确,坐在对面的姚一红仍旧低着头,几乎是不动声色地还在继续她的午餐,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心在一瞬间忽然跳得那么难受,像进入了恐慌的绝境!以她的智力,她怎能不领悟到郝青白方才那几句话的意思:他没有离婚,他也不打算离婚了。
令她心跳加快的不是他的拒绝,而是他拒绝的理由:都是悲剧!这算什么,难道因为人天生要死,大家都有理由去自杀或他杀吗?
郝青白估计得不错,姚一红是个神经坚强发达的女人,她有力地克制住自己,只淡淡地噢了一声。停了一会儿,她才礼貌地开口说:“的确,我也同意你的观点,人生本来就是悲剧,但是,我们可以让它的过程变得丰富一点。比如我,跟你的思路就不在一样,最近我在重新考虑婚姻,并且,已经开始……分居了。我现在单独住。”
“分居!”这个词好像刺激了郝青白,他不可避免地想到家中的妻子,是的,她逼着自己离婚的方式也是“分居”,“分”给外界看的“居”,好像到了这个地步,夫妻间的性,就成了一种立场的证明,或者战斗的武器!她们,这些女人们,不仅玷污了性,也玷污了她们自己的身体。难道,判断或区分一对男女的关系,除了“性”就不可能有别的标准和方式吗!郝青白有些失态,他想不到姚一红也会用这一套来对付男人,她凭什么去跟她的丈夫分居?以不爱的名义?以爱的名义?哦,她真的只是个女人。
“哦,你们女人,最擅长这一套了……”郝青白紧紧咬住牙齿,好不容易才克制住心头的愤怒。很久没有发过火了吧,他几乎都可以听到那熟悉的火苗的声音。
“怎么了?”姚一红很吃惊,她不明白他的脸为什么突然涨得通红,下颚上的肌肉紧张起来。
“哦,对不起。”凭着多年的修养,郝青白马上加以致歉,接着低头吃起东西,但他不是真的道歉,这一瞬间,他的绝望和仇恨也许包括了对所有的女性;并且,他还想到了姚一红的那位被蒙敝被抛弃的丈夫。嘴中食物一时味同嚼蜡。
他为什么突然有些紧张?难道他以为我故意说出“分居”是想逼着他做什么吗?哦,原来他是那样考虑问题的。姚一红也是一阵默默的感慨,但她没有生气,男人偶尔的失态只是表明他身上还保留着特别柔软的真空,是可以原谅的;特别是刚才,当郝青白的脸色突然涨红起来,眉骨突然跳了一下,姚一红又看到了他所掩藏着的抑郁与暴戾之气,更让姚一红感到了一种紧迫的责任感,她知道,郝青白的痛苦一定比他表现出的还要多得多。
姚一红几乎是好脾气地想,他对我、我对他,都存在一些误区,误区会导致戒备,这很正常,可以慢慢修正。姚一红一定没有意识到,在郝青白面前,她的脾气竟是如此柔和了、宽容了,简直跟在王向阳面前判若两人——这是否就是她所准备投入和追寻的爱情呢?她真的愿意如此委屈自己吗?
现在,他们都说出这次约会的主要内容了,尽管各自的内容都带给对方更多的压抑和不快。可是这不影响什么,他们知道,心里的那个东西还在,只是他们现在进入了交流上的瓶颈。
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重新继上话。像是为了分散一下注意力,郝青白跟姚一红谈起了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妹妹郝青蓝:“你跟她长得有几分相象呢!”,接着,又不厌其烦地讲述了关于一号选手、二号选手以及其他追求者的一些趣闻逸事,不过,郝青白没有提到最近的三号选手——当事情还处于现在时,还没有变成往事,进行谈论是不明智的。
姚一红的心情自然是纷乱的,她是个急性子,不太喜欢郝青白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她需要直接的、冷静的好好把一个问题谈透,从他们各人的角度和经验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郝青蓝长得是否跟自己相象、是否会找到合适的男朋友,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她对这个老姑娘毫无兴趣,也不欣赏她那样的生活方式……
郝青白注意到了姚一红的心不在焉,他马上体贴地打住话题,他想起了心理学上的一个提示:一定要让他(她)以“我”为主语进行谈话。于是,他像是饶有兴趣地重新问道:“那么,你也来说说,比如儿子?像你吗?一定也很有才华吧?”
郝青白没有意识到,他这会儿正试图控制谈话内容,因为他害怕姚一红会谈论他所不愿意的话题。他正在把这场谈话变成一场缺乏柔情的心理战。
姚一红的耐心快要没了,倘若对面坐的是王向阳,她可能早就拂袖而去了,可是,对面是他,在他面前,她一向是理性的、宽容的,怎么能像个中年妇女似的大发其火呢?毫无风度地丢下对方的问题不管……算了,正好告诉他那个小秘密吧,他应该第一个知道:“我的儿子,很好,问得好……嗯,青白,正好,有一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我儿子,他在你公司上班。”
“真的?哪一年来的?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我可以……”郝青白反映特别热烈,好像是想补偿什么似的。尽管这违背他一向坚持的用人原则,但他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欢天喜地的,好像他一贯都是这样乐于助人似的。
姚一红吃惊地停下筷子,她感到悲哀,她知道,郝青白的思维模式有些物化了,并且明显地言不由衷,为什么,他突然有了类似交换与弥补的暗示?
姚一红用眼光阻止了郝青白进一步的表白:“别说了……我只会让他自力更生,我也喜欢顺其自然。他进入或离开大郝,他在大郝出色或是平庸,应当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起。我本来……是希望能够帮你做点什么……”郝青白有些讷讷的,他发现,话题不是他能控制的了。
“青白,真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精神的羽翼最怕的就是世俗之网,你的妹妹,或者我的儿子,他们跟我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吗?很久没见面了,我们谈论这些干什么?”姚一红尽理压低声音,表明她不是发火,而是在谈话。“还有……你对我分居的反应,我认为非常奇怪……青白,各人都有各人的婚姻,各人的鞋子自己最清楚……的确,对你关于婚姻的决定,我感到很失望……但是,你放心,我决不会去乞求或逼迫什么……分居,是我自己的事,是我很早就打算的计划……你不要试图通过载培我的儿子来弥补,你不欠我什么……”
“一红,我明白你的心意。我的境界不及你的万分之一……不管你信不信,我其实是一百个愿意跟你在一起……”郝青白是转过头去说这句话的,他感到自己像个拙劣的骗子。“但是,一红,我们看透一点、看远一点……男女二性,在本质上就是敌人,相爱实际上就是作战,如果保持一定的距离,也许双方都会得以保存独立的身体与精神,但是太近了,比如结婚,这样,总会有一方在贴身的肉博战中倒下阵亡。这样的例子还少吗?再相爱的人进入婚姻,那种油米柴油的物质生活,就开始了对情感生活的慢性谋杀,最后有一个人倒下,不是精神倒下就是肉体倒下。一红,你是聪明的,你细细想想我的话……如果是真心相爱,我们,没有必要去开始另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