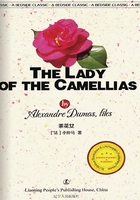种豆南山下
进入夏至,天气渐热,黄豆渐熟,有些豆荚开始爆裂,黄豆像子弹一样「毕毕剥剥」射出,在空中画些优雅的弧线,落地,欢跳几下,以舞蹈的方式,召唤我们去收割。
豆,又叫菽,起源于5000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作物之一。
“一些被遗忘于地窖中的豆子,经过220年后,依旧没有变味!”由于历史久远,我很难体会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当年向世人宣告这一发现时的喜悦心情,但从上述文字,从许多典籍记载,从豆类慷慨的赐予中,依然能够真切感受到豆的珍贵,豆的神奇。
“五谷则麻、菽、麦、稷、黍。”古人把豆与谷相提并论。若说中华五千年是一部农耕文明史,那么,豆便是不可忽视的章节。
黄豆是重要的经济作物,也是优质绿肥。“高粱少情义,黄豆多仁爱。”黄豆不像高粱那样,根须鹰爪似的牢牢抓住土地,猛抽养分—它懂得感恩,懂得反哺—根部许多小球似的根瘤菌,神通广大,可捕捉空气中的氮气,合成氮肥,回馈土地。20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的番薯地都先种早季黄豆;几乎所有的晚稻田塍都点过晚季黄豆。
早季黄豆种于惊蛰,晚季点于小暑。
惊蛰一到,潜伏了整个冬天的虫子纷纷出蛰,鸣叫的鸣叫,歌唱的歌唱,舞蹈的舞蹈,以春雷为伴奏,迎接早季豆种的光临。
种豆的时候,早起的母亲忙于煮饭,父亲忙于张罗物品。先在高耸的土粪堆上开出小沟,泼入平时收集起来的尿水,再用锄头拌和均匀。拌好的土粪,装在畚箕或筥里,踏得瓷实了,搭好扁担,等候在那里。
若是礼拜天,我也会抄起扁担,伸进肩膀,试担—拱了几下,腰却直不起来。我只能做些诸如扛锄头、拎豆种、提茶水、送点心等轻松的事。
其实送点心也不轻松,尤其是送有汤水的点心。我曾多次送过点心,第一次印象最深刻。那次送的是绿豆粥,清滂滂的。套用母亲的话说,那叫:一粒田螺九碗汤。凭我的力气,一个人完全可以担去。由于山路较远,母亲想自己送去。“谁煮粥?”我只好找了这个不让她去的理由。
“快去快回。”母亲正要担走。
我拉着篮子边沿,母亲说:“远路无轻担,路头担灯芯,路尾担铁钉,你担不了哦。”
我不放手。母亲只好依了,将扁担托到我的肩膀上,说:“眼睛觑路,莫觑篮。”
一个篮子蹾着盛满绿豆粥的陶钵,另一个装有碗箸和茶婆。木盖掩着陶钵。茶婆为瓷质,套盖,长嘴。担子并不重。可我才走几步,稀粥、茶水便不安分了,晃荡不停,像是下马威。
母亲见我走走停停,又喊道:“眼睛觑路,莫觑篮。”我的头像拨浪鼓似的转动,又看钵头,又看茶婆,总顾不了路。奇怪的是,我越在乎,它们越动荡。进入山路的时候,我低头觑路,腾出一只手稳住钵头,茶婆又动荡了,叮当响,嘴也喷水,盖也溅水。换了肩,伸手稳住茶婆,钵头又无法平静,稀粥像一只躁动的兔子,上蹿下跳,居然撞开木盖!我有点像路上那只努力推滚屎球的屎壳郎,推了滚,滚了推,顾此失彼,手忙脚乱,不知该怎样平衡自己,稳住它们。还是歇一口气吧。山路又崎岖不平,少有安放担子的平地。终于放下,翻开一看,茶水溅去三分之一,稀粥也损失不少。继续前行,我不管它们的动静,只顾低头走路。这时,它们既不动荡,也不飞溅,乖乖来到山上。
父亲和哥哥围拢过来,双手在自己的衣襟前擦了擦,各舀一碗,昂起脖子,歠了;又舀一碗,昂起脖子,歠了。
他们放下碗,嘴唇一抹,继续翻地、埯豆。埯豆跟埯麦一样,也要整畦、啄堀。山地极不规整,有的宽,有的窄;有的直,有的弯,奇形怪状。经过他们灵活处理,整出来的畦,啄出来的堀,倒也不失美感。
我帮助放豆种。豆种颗粒大,比麦种好放得多。通常每堀放两三粒,视土地肥力而定,瘦地三粒,肥地两粒。豆种从指缝间滑下,不宜挨在一起。
放过豆种,撒些土粪,每堀一小撮。轻轻挥动锄头,刮平豆堀,像是为豆种的简易穴居拉上窗帘,让它们舒舒服服地孕育下一代。
过六七天,豆芽探出头来,羞羞答答的,子叶像新娘的红盖头、绿花伞。
再过一个月,展叶四五片,简单锄一锄,随便施些农家肥,豆苗就会兴奋地长高、开花、结荚。
有些仿佛来自《庄子·逍遥游》的蟪蛄光临其上,翘着羽翅,“叽叽—叽叽叽”鸣叫。寻寻觅觅,最后在葱茏的白茅上,发现了它。正要蹑足走近,它却“叽里—”一声,远走高飞,像百灵飞翔似的,忽高忽低,泊于远处一片整齐婆娑的白茅丛中。紧跟过去,我有擒拿法,它有隐身术,技高一筹。刚刚离开,它又引吭高歌。踅回。它又戛然而止。
毛茸茸的豆荚渐渐形成、发育,凹凸有致,缀满豆萁。
连日来,我们全靠炒盐巴敷衍渴望抚慰的味蕾—母亲从豁了口的盐瓮里舀出几勺盐巴,爆炒之后,盛在碟子里,置于饭桌中央,或另加一碗韭菜汤。黑褐色的番薯米饭,衔在嘴里,味如嚼蜡—能馕下的,就馕下,馕不下的,手中的箸有如无奈的触角,伸到碟子里黏几粒盐巴,送入乏味的口腔,与迟淹的番薯饭混合在一起,“骨碌骨碌”滚下喉咙,或者舀一勺韭菜汤,协助遣送饭团。不过,炒盐巴常使我“坌嘴”—口水汩汩,将要呕吐。只得吸烟,吸上几口,即可止住涌泉似的口水。原来,炒盐巴具有催吐功能。
等待的时间总觉得漫长。终究不能等到豆荚成熟。“还是去拔些黄豆回来吧。”母亲终于发话了。
我迅速去后山拔一搂黄豆回来,一荚荚掰开,取出不胖不瘦的黄豆。
父亲唉声叹气:“煨虾不等虾尾赤。可惜!可惜!”
“囝涕留得住芋种吗?”正在厨房里煮豆的母亲扔出一句,如一团糯米噎住父亲。
“惊蛰种,夏至收;清明种,小暑收。”这是黄豆的成熟规律。进入夏至,天气渐热,黄豆渐熟,有些豆荚开始爆裂,黄豆像子弹一样“毕毕剥剥”射出,在空中画些优雅的弧线,落地,欢跳几下,以舞蹈的方式,召唤我们去收割。
割回的豆萁,经过暴晒,大多数黄豆能自觉出来。有些不愿离开豆荚的,可用扁担敲、木槌捶,也可踩踏,逼它出来。黄豆铺满一地,浑圆,金黄,粒大,不像现在外来的那些黄豆,瘦瘪,半青不黄,没形没骸。
豆萁是煮豆的好柴禾。有一次,我们围在灶边,看爷爷烧火,他抖动手中的豆萁,说:“萁是哥,豆是弟,哥欺弟,结果呢,萁也烧成灰,豆也煮烂了。”我们兄弟多,爷爷一直担心日后分家闹不团结,也像煮豆燃萁,骨肉相残。我们服膺他的教诲,兄弟情同股肱,从未红过脸。
当我们互掷器物嬉戏时,父亲就会教训道:“一粒白豆囝也会打死人的!你们晓不晓得?”我们立马放下武器,愕然不动。
我家每年都收黄豆三四百斤,算是大户了。我家常常处于“桶塌冇下箍”的状态,小小的黄豆被赋予太多太多的使命。
恩格斯说过:“蛋白质就是生命。”没有鱼,没有肉,没有蛋。只有番薯,只有青菜,只有少得可怜的大米。它们能提供多少蛋白质?缺少蛋白质的生命,能有多少质量可言?我从小就知道,黄豆滋补。“七粒黄豆,一粒鸡蛋。”那是农民的自嘲。不过,它也成了我最初的营养学启蒙。我还从一本书里看到黄豆的可贵—就蛋白质含量而言,黄豆最高可达50%,是小麦的3倍,是金豆、大米的4倍。换句话说,1斤的黄豆相当于2斤牛肉、3斤鸡蛋、4斤猪肉。那个时候,谈论营养是件奢侈的事。我更不敢做黄豆等值交换鸡蛋、牛肉和猪肉的美梦。我只会在开饭之前,先扫一眼饭桌,看看有没有炒黄豆,那种沾满盐花的香喷喷的炒黄豆;看看有没有烀黄豆,那种皱巴巴的咸得齁人的烀黄豆。若有,就多盛一点饭。若无,胃口就萎缩了。
母亲也会选个稍闲的日子,做一板豆腐。
推磨略比拖砻轻松。力气大的,一人即可磨豆浆,但要有一人站在旁边喂豆。
磨完豆浆,过滤。豆腐架是两根方木条做成的十字架,中间铆有铁钩,用来系绳,吊在梁上;状若剪刀,张翕自如。方木末端拴着绳扣。漉布约三尺见方,四角系于绳扣,酷似吊床。倒入豆浆,双手握住豆腐架的两端,摇啊摇,漉啊漉,豆汁射下豆腐桶。豆腐渣抱成一团,在漉布里翻跟头,像个快活的顽童。
豆浆倒入鼎里煮沸的时候,也可顺便挑起几片腐竹,晾干,金黄,半透明,一烫即熟,且不黏稠。不像现在的那些腐竹,要么久煮不熟,要么一熟就糊。
若不挑腐竹,就把豆浆舀入豆腐桶,凉到豆浆表面起皱纹了,浇下事先泡好的石膏水。通常按每三斤黄豆,用一酒盏石膏粉,加入少量水,泡成石膏水。石膏下多了,豆腐就太老;石膏下少了,豆腐又太嫩。真有意思,一大桶豆浆,石膏水一浇,像变魔术似的,瞬间凝成豆腐脑。
母亲把方形木框扣上豆腐板,垫好纱布,舀入豆腐脑,整好纱布的边角,覆过,扣下方木板,压上石头,榨干。
约略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它的洁白,是视觉上的美;它的柔软,是触觉上的美;它的香淡,是味觉上的美。
由于家口多,即使十分节省,甚至将豆腐埋入盐钵,使之成为咸豆腐,也只能匀过两三天。
“豆官哦—豆官烰。”
“豆官—豆官哦。”
叫卖的是乐庚婆。叫声像她的豆腐一样清嫩,每天跟钟声似的,准时来到厝边。仿佛每天早晨都是她叫亮的。
浓郁的香味像贼风,引诱尚未起床的我猛抽鼻子。
“刚的,热着呢,捡几块吧。冇现钱,不要紧,打赊。”她的臂弯挽着一扁篮豆官,耐心十足地站在厨房门口,一边揭起蒙住扁篮的纱布,一边向犹豫不定的母亲说。这是她一贯的台词。她对所有的乡亲都这么说。她始终微笑着的脸庞写满豆腐般鲜嫩的真诚。
母亲说:“炒豆腐渣还剩好多。”
是的,豆腐渣还剩半钵。豆腐渣也是向乐庚婆买的。每次都买很多,加些葱蒜和盐巴,清煮一大钵,能吃好几天。每顿一小炒,越炒越干,蓬蓬松松,有如锯末。气温高的时候,除了馊与咸,别无另味。不过,我的胃口向来不错—这样的豆腐渣,我也吃得津津有味—至今仍喜欢它,还在回忆呢。做豆腐的人几乎不吃豆腐渣。每天产出的豆腐渣,要么卖掉,要么喂猪。外卖一斤五六分钱。豆官烰也便宜,一块六分钱。母亲偶尔也买几块。就几块,当然要按“田字格”来切—将每一块都分成四份,一人一顿一份。只有来了客人,母亲才会阔气些,一块只分三份或两份。
从初中到高中,我的寄宿生活的饭配,与黄豆息息相关。除了偶有的豆官烰、咸豆腐或豆腐乳,便是豆酱(向供销社买的,1斤8分钱)、咸豆豉、酸菜黄豆、烀黄豆。其中任何一样,都可以帮助我度过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星期。吃到一半,生醭变质了,也舍不得倒掉。
于是,我盼望父亲能粜些黄豆,买几条带鱼或一包子回来。
炒黄豆还作为婚礼或过年的果子,被无数人笑纳。闲暇时,口袋放一把炒黄豆,最好是黏有盐花的那种,边走边吃,惬意得很。手头已有一把炒黄豆,再舀来一壶糯米酒,慢慢悠悠,蹾它几盏,快活得很。
“五谷宜为养,失豆则不良。”从营养均衡的角度论,日常生活中,豆也不该缺席。
性本爱丘山的我现在就想,以后退休了,也要去找个幽静的地方—那里有山,山上有树,树上有鸟;那里有溪,溪里有水,水里有鱼;那里有地,地里有土,可耕可种,依山傍水,建一座小木屋,享受亦耕亦读的生活。夜坐木屋,汲泉煮茗,看看闲书,写写闲文;日下田园,种种菜,种种豆,比如豇豆、菜豆、扁豆、御豆、刀豆、米豆、湖鳅豆,比如黄豆、绿豆、红豆、蚕豆、观音豆,还有许多不知其名的小豆。让五彩缤纷的豆花,点缀自己的生活;让神态各异的豆子,在自己的双手里滑动,在自己的日子里滑动,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滑动……
瓜瓞绵绵
各种丝瓜,大的,小的,长的,短的,有棱的,无棱的,纷纷登场,垂挂于瓜藤,随风摇荡。如风铃,如棒槌,又像许多感叹号,使颇具美感的瓜藤越发迷人。
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传统种植皆受命于农时。“清明一到,种瓜点豆。”大人们正忙于春耕。我和二哥则忙于种丝瓜、种金瓠。年纪尚小,但我们严肃对待,没有丝毫游戏的成分。
彼时的丝瓜没有大面积种植。丝瓜跟人一样,世界很大,而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却极其狭窄,不是田角落,便是地旮旯。
田垄是生产队的。所有田地都属于集体。能搞小自由的,仅限于自己所在生产队的那些田塝。别队的田塝,即使种了,也会被人毁掉。每年冬末或春初,我和二哥必做的一件事是:烧田塝、开田塝—烧掉旧田塝上的野草与杂物,宣告原主将继续耕种;找到新田塝,点一把火,烧了野草,表明已有归属。田塝小者如箕,大者似筥,再大也大不过竹匾。它们吸附在田塍凹处。远远望去,它们颇像静默的田螺。
田塝种不了大家伙—金瓠、瓠瓜和匏瓜,只能种些丝瓜或黄瓜。黄瓜也不大种,为主是丝瓜。种丝瓜不复杂,深翻之后,搜罗一些杂草,像煨番薯一样给田塝烧土,提高地温,增强肥力。基肥下也罢,不下也罢,反正丝瓜不会计较。不觉晓的丝瓜种子还在瓜络里继续它的春眠,虽然瓜络已被我们剪去一头,可听见种子“嚓啦嚓啦”的声响,却不见它出来迎接明媚的春光;用力抖了抖,它们才鱼贯而出,古币似的乌黑发亮,或落于掌心,或落入同样乌亮的瓜埯。瓜埯躺着两三粒丝瓜种子,撒些土粪,盖过细泥即可。七八天之后,便冒出小板斧似的子叶,像是问号,似乎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再过几天,嫩叶也出来了,碧绿而尖锐。那是丝瓜的宣言。
树大招风,苗嫩惹虫,向来如此。萤火虫、黄守瓜是丝瓜的头号敌人,嫩叶被打开许多天窗。好在丝瓜亦能忍受它们的侵害。丝瓜苗奋发向上,初生的瓜秧,用它灵敏、轻盈的卷须,钩住插在它身边的小竹竿,几度攀爬,几度滑落,但它凭借卷须的反复缠绕,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到顶,像一只飞累的蜻蜓栖息在那里,四处张望。初临绝顶,它有点怕,有点晕,摇摇晃晃的,伸出小手,希望谁能拉它一把。赶紧搓几条草绳,沿着田塍边缘,揳几根木桩,予以牵引。瓜藤一脚跨过,一路攀援,也就有了继续延伸的可能。它们一边伸展,一边开花,几乎每一节都开出一两朵花,有的是雄花,有的是雌花,酷似舞台上的道具—伞,朵朵金黄,魅力四射。那种色泽极纯净、极高雅、极温馨、极养眼,仿佛为金箔所造—即使金箔,也不可能有这般能耐,呈现如此高贵的气质。花美自有蜂蝶来,许多好事者,诸如蜜蜂、蝴蝶、细腰的马蜂、肥臀的胡蜂,还有不会采蜜的金龟子、蜻蜓、纤弱的豆娘、笨拙的七星瓢虫,以至于飞不动的蚂蚁,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像手脚不利索的依姆,借助于木桩和草绳,一步一歇,爬向自己神往的高地,致使整条的丝瓜藤显得热闹非凡。人无百年好,花无千日红,花开花落终有时。丝瓜花有的凋谢了,有的雌花则演变着,变魔术似的,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自己的生命,生出小拇指般毛茸茸的瓜瓞,有如碧玉簪点缀其间。它们大得真快,几天不见,便不敢相认了。
各种丝瓜,大的,小的,长的,短的;有棱的,无棱的,纷纷登场,垂挂于瓜藤,随风摇荡,如风铃,如棒槌,又像许多感叹号,使颇具美感的瓜藤越发迷人。茫茫田垄,就数它们最显眼、最风光。在人们视野里,水稻和田塍纷纷后撤,都成了丝瓜的宏大背景、义务陪衬。
凝视着忘我膨大的丝瓜,真担心那些纤弱的瓜藤不堪重负,胖嘟嘟的丝瓜会掉落下来。其实我早就听大人说过:“囝涕大,匏吊大。”担心显然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