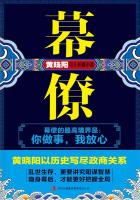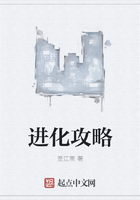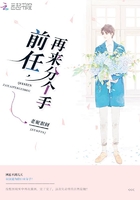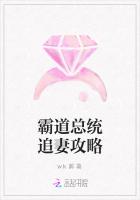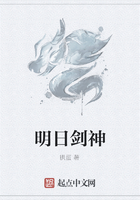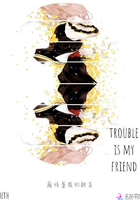作家对于人的价值的珍视,还从他对于时间的珍惜与写作的勤奋充分表露出来。“划右”那年他才24岁,而1979年平反返京,他已经是46岁、鬓发染白的中年人了。“没工夫叹息,没时间感伤。”这是作家发自肺腑的声音。自此,二十多年如一日,他笔耕不辍,想弥补因岁月的流逝而造成的重大损失。他像一头牛奋耕不息,出版了数十部作品。1996年他不再担任任何工作时,文怀沙打电话对他说:“文坛里又多了个生命力顽强的作家,少了个为别人拉车拉磨的驴儿。”
基于对人的价值与人格的自珍自重,作家已然成为文坛上一个自成方圆、有棱有角的汉子。他用四句话为人性画像:“圆者自转,方者自安,智者自视,愚者自持。”这也是他理解人生与人格的十六字真言。作家既是圆者,更是方者,因而无论在风雪驿路上还是在阳光大道上,他都自成方圆,既能自转,又能自安;作家既是智者,也是愚者,他的作品,他的人生,每每蕴含着大智慧,而他同时又是典型的愚者,因为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他对于文学事业过于执著的追求,更显示出作家难能可贵的愚人的品质,因此,他冷静自视,更善于自持。
幽灵与文化
品读从先生的作品,凝思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我总觉得,有一个幽灵,有一种文化,始终贯穿着他的作品,贯穿着他的人生。
作家应邀到汕头大学讲学,夜宿汕大校园湖畔的迎宾楼,梦中似听见声声警笛。那是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再现:作家在警车里被押往该去的囚笼。梦醒之后才知道那不是警笛,而是窗外林中鸟儿的高声夜啼。这个遥远而凄凉的梦,已跟随作家多年了。在莱茵河畔的波恩,作家梦中出现环绕劳改农场的大河,想不到它像影子似的,又追踪着来到了汕头大学。梦中,有一个幽灵,呼唤着混沌的文化。
为了驱散噩梦的阴影,作家索性披衣起床,去倾听南国鸟儿的夜半歌声,去欣赏湖中随波飘逸的小舟上的灯火。在湖边的夜游中,作家凝视着水波中的灯影,随着水波向湖中散去,形成一圈圈光的涟漪。两只小小的戏水鸳鸯,搅碎着一泓碧波。湖中的孤舟与鸳鸯,撩拨着作家的幽思,牵动着作家的幽灵……
作家驱车奔往澄海的樟林古港,从红头船的辉煌历史和船体残片中,感受到它的幽灵与文化,并意识到陈慈黉故居同这种幽灵与文化乃一脉相承,它们与作家长年所系的幽灵与文化,既相通,又相别。因而,作家在为淹没于万顷波涛中的死者致敬的同时,更为昨天的劈风斩浪、与海外文化接轨的红头船及陈慈黉们而高歌!
忧患意识乃是作家幽灵与文化中的重要内涵。从先生在致张光年同志的信中提及:“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他说忧患意识正是他的作品的魂魄。他认为:“凡是爱我民族爱到心疼地步的文化人,都有这样的十分焦渴的心愿和无畏的精神。”
享受寂寥,又是作家幽灵与文化中的重要特色。作为瓦斯检查员,作家必须经常独自穿行在许多条无人劳作的煤巷,感受着莫名的恐惧。走在无边黑色中,惟一可以听到的是,大山中的煤层“嘎嘎、叭叭”的断裂声——那是大山所独有的语言。一条条黑色的煤巷长达数里,作家独自走在其中,真有走到了冥冥天国的感觉。在这个天国中,原来有着许多活灵活现的生灵,而现在都变成了动物的化石标本。这些幽灵,永在肃穆之中。这儿没有第二个人,更没有阶级斗争,作家的思维自由驰骋,走累了,便在棚柱旁坐下,独享大山腹中难得的寂寥……作家常常久久而不愿离开这单人世界,因为他明白自己不过是社会上的一个黑色幽灵。
作家欣赏国学大师文怀沙常常超越人的正常思维的轨道,飞向天之穹地之垠,让人感悟到他那根不安分的艺术神经,纳天地百川于其心,而文化人的心及由心而生的幽灵与文化,则必不能丧失人文良知,良知乃是做人行文的基点,也是幽灵与文化之魂魄。此天经地义也。文怀沙如此,从先生也如此。
大自然的性格
我与从先生虽然交往不很深,但反复拜读其作品、品味其人生之后,深感他非常热爱大自然,而且对大自然性格的了解自有其独到之处。
作家时时注意着大自然的美态与性格。他应邀到汕头大学讲学,刚下飞机,在奔往汕头大学的路上,便注意并研究起南国的花卉来了。当他弄明白木棉花开得很早,是以花朵坠地来点缀春天的之后,他感到悲壮,更感到新奇——第一次知道百花之中还有以香殒玉碎来装点春天的,从而产生由衷的敬佩与慨叹。
夜宿汕头大学后,作家又夜半披衣起身,悠游湖畔,观察、研究起这里的湖水、树木与鸟类来。
在汕头,在关注大自然方面,作家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他对大海的兴趣。我陪他一路参观汕头港,他看海、问海、赏海、品海,精神之专注令我钦佩。作家非常理解大海的性格。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与几位作家曾在西沙群岛奔往南沙群岛的大海上,遭遇了强台风,那真是惊魂落魄的一幕:面对狂怒的大海,舰艇无奈地抛了锚。惊涛不断地冲击着舰艇,舱里的水杯在地板上来回打滚;被涌浪掀动的铁锚凶猛地撞击着底舱,发出声声沉雷般的巨响。作家深切地感叹:“只有在台风眼里感受过海,才能对大海的残酷有所悟知。”那些靠舵手掌舵、靠桅帆远航的木制的红头船,又怎能与大海抗衡呢?
人们呵,该怎样认识大自然?怎样认识自己?
“文革”期间,作家曾从一个劳改驿站转移到另一个劳改驿站,途经陕西与山西分界的风陵渡黄河大桥。作为黄河的子孙,作家渴望着看一看母亲河的身影。当列车穿越黄河时,落日已经西沉。作家将全部视力都投向母亲河,但令他伤感的是,他不仅没有看到古诗中“长河落日圆”的雄浑景象,连黄河的滚滚波涛也看不见。两岸黄沙向河床延伸得很宽,河心那几条被黄沙分割开的水流,小得像是溪流。这不禁让作家为之颤栗。他对坐在身边的妻子张沪说:“真想不到……竟是这副模样!”张沪答道:“山有老,水有老,流了五千年。它累了,像个活着的木乃伊了。”是枯水季节的缘故吧?反正它已过了青春期。记得唐太宗游黄河时曾留下诗句:“碧原开雾湿,绮岭峻霞城。烟烽高下翠,日朗浅深明……”这最后一句,便可推断当时的黄河水是清的。现在呢,一片浊流。那时,作家联想起毛泽东视察黄河并留下“河清有日”的题词,曾深深感动过这位作为热血青年的作家。多少年过去了,黄河却一年比一年浑浊。这不禁使作家顿生满腹悲怆,潸然泪下……
尽管母亲河的容貌令她的子孙们伤感悲怆,但作家依然割舍不下他对母亲河的深深依恋的情怀。1976年,就在作家即将离开劳改农场前往临汾文联工作的前夕,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再去看看黄河。于是,他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几十里地,来到黄河之滨的风陵渡,坐在河坡上,听黄河的涛语,看黄河的浪花,那滚滚东流的浊浪,虽说仍然令他神伤,但此刻他却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从花鸟、湖泊到大海,又从黄河到大山煤矿,作家总是关注着大自然的性格。命运将他带进晋东南的晋普山煤矿之后,作家又不断观察起大山煤矿,逐渐感受着煤矿的性格——它是以毁灭自己来照亮别人的特殊物质,这要经过从地上到地下,历经多少煎熬的痛苦,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这难能可贵的品质,正是人类自身所缺乏的。
作家说:“我喜欢煤,更敬重煤的性格。”在他告别煤矿之前,为了加深对煤矿的记忆,作家带走了一条磨得已经失去皮色的矿山皮带,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不顾有失大雅地系着它穿行欧洲。作家非常怀念那段挖煤的岁月,敬仰煤的品格。在作家漫长的劳改史上,挖煤是最值得回眸的一页,而煤的闪闪发光的性格,更是长久地感化着作家的心灵。
我深深感到:在作家漫长的人生历程中,他一直都关注着、讴歌着大自然的伟大性格,并为这伟大性格所影响、所陶冶。
亲情
作家对亲人始终充满着融融的亲情。
劳改生活数年之后,作家获得了第一次探母的机会,他的心兴奋得狂跳起来,却又是过街老鼠的心态,好在是晚上回家,路上没有熟人认出来。在破旧简陋的家里,他的老母亲和惟一的孩子小从众相依为命,靠贴火柴盒谋生。作家暂时忘却了世态炎凉与人间冷暖,在只有一天的假期中,与母亲和儿子共享了天伦之乐。但三年多梦魂萦绕的感情断桥,是难以用一天时间弥合起来的,作家终于在儿子的哭声中离别了亲人。
作家在张家口化工厂被大火烧伤经抢救脱险之后,又获得回家探母养伤的机会。这次探亲,除了再享天伦之乐,作家更是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而下决心再不能自甘随波逐流,为了母亲、妻子和儿子,作家要努力改变命运。
风浪再险恶,亲情的船缆也是扯不断的。“文革”中,作家的母亲脖子上被挂上“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他探亲时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在外头打探情况并待天大黑了以后,才悄悄溜进家门。他看见那块大木牌子又粗又沉,用铁丝挂在母亲脖子上,脖子被勒了一道深深的沟槽!从先生立即用手去摘母亲颈上的牌子,却被母亲拨开了:“不行!不行!”“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作家拗不过母亲,只好拿来一块布片,垫在母亲的脖子上。
“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儿子:“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是会来抓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为了不让孩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运动一来,妈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中去了。作家四岁丧父,母亲与他相依为命。母亲一直受着生活的煎熬。作家望着苦命的母亲,真想将妈颈上那块大木牌摘下来挂在自己脖子上。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母亲死活不肯摘下那块木牌。作家硬是从母亲颈上将木牌取了下来,答应一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直到凌晨三点,母子的主要话题,就是一旦发生不测,小从众的去向问题。其间,母亲不断打开手电筒,看着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四邻。四点钟左右,母亲催儿子立刻回农场。从先生像离开黑店的贼,失魂落魄地匆匆离家回场。
后来,母亲被遣送回乡,乡里又因她是丧失劳动力的老人而拒收。作家的心绪坏透了,常做恶梦。梦断残更之后,便再也不能入睡。想到自己四口之家,三口成了囚徒,且分在四个地方生活。到底犯了什么大罪呀?
母亲被乡里重遣回京后,换房搬家的命令下来了。街坊几个同命运的孩子帮着一老一小,把家搬进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破旧小屋,一年四季都见不到阳光。母亲每天扫街,孙儿怕奶奶累着,争抢扫把扫街,替奶奶赎罪。尽管儿子从众像只怕猫的小耗子,还是无法逃脱各种莫名的欺负与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