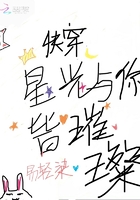奇怪的是,书房里没有人。可能是在他的卧室吧……泽颜犹豫了一下,还是想去找他问一句为什么,就沿着楼梯一阶一阶地往上走。
伊翎峰不在他的卧室,他坐在三楼楼梯的最高层,双肘压在腿上,手背抵着额,看上去十分颓废,“坐在我旁边吧,”他低声说着,“我是不是很混蛋?”
泽颜瞬间便理解了他,他也是在痛苦……“对伯母来说,也许每呼吸一秒,都是在受罪,死亡已经是解脱了。只是……你处理的未免太理性了。”在自己母亲生前,便开始联系殡仪馆的人,换作常人,肯定做不到。
“我不想让她再受罪了,每次看到她了无生机的眼神,都让我陷入无边的恐惧,她还是我妈妈么……我妈明明会有那么温柔的笑……你知道我跟医师说起安乐死时,我有多愤怒么!我连自己的母亲都救不了……我还算是个人么……”伊翎峰的情绪剧烈地波动着。
泽颜理解了他的铁石心肠,他是在逼着自己理性。伊家是站在高位的,总有人时刻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总有人想着把他拉下去,他不敢让自己露出任何软弱的一面,所以他必须铁石心肠。给自己的母亲,一个体面的谢幕。“殡仪馆的人应该给伯母化好妆了,要去看一下么?”
伊翎峰似乎是犹豫了一下,然后迅速站起身,几乎是冲下了楼梯。泽颜也站起身,跟在他身后走了下去。
“滚出去!”伊翎峰冲着屋里还在给宋可卿化妆的那人吼着,那人吓了一跳,然后赶紧弯着腰退了出去。
伊翎峰看着宋可卿那终于安详的脸,一下子跪倒在地。那个化妆师才给宋可卿画了一半的妆,绯红的脸庞像是讽刺,泽颜不动声响地递过一条温热的湿毛巾。伊翎峰接过,一点一点地把宋可卿脸上未完整的妆面拭去,然后拿起旁边的一只眉笔,仔细地给她画着眉,嘴里低声呢喃着什么,泽颜仔细去听,才听清那是声声的对不起。
妆罢,伊翎峰轻轻的在宋可卿的额头印下一个吻,轻声道:“妈,希望你下辈子,不要再有一个我这样的儿子。”他的眼眶有些红,却没有泪。直起身来,将宋可卿身上绸缎的寿衣理平。她的身体还是温暖的,伊翎峰握住她紧攥着的手,轻轻地把她的手指顺直,取出了那项链。
泽颜开口道:“让伯母带着它离开吧。”
伊翎峰缓缓地摇头,“这是我送给你的,我不会再收回,她已经不需要这个了。谢谢你……让她在最后这几天,能有点安慰。”
说着,将手里的项链递还给泽颜,泽颜便抿着嘴接过。
葬礼很肃穆,但却没有多少人,世上知道宋可卿活到现在的人少之又少。
伊棉撕心裂肺地哭着,“哥……你不是说,会治好妈妈的么?!你骗我?!你骗我——!”声音嘎然而止,她的面庞上突然出现了悲伤以外的情绪,泽颜看得清楚,那是仇恨。
“伊棉”的身份转换成了“伊诗琪”,从此恨伊翎峰的人又多了一个。泽颜垂下眼睑。
伊诗琪愤愤地站起身,走到伊翎峰面前瞪着他。伊翎峰抬头冷冷的看了她一眼,那眼神足以让人绝望。伊诗琪顿了一下,道“我再也不会回来了。”言罢,转身离去。
伊翎峰只是淡淡的看着。
棺木被土层层掩埋,他一直沉默着。
牧师作了最后的祷告,世界都静下了。许久,白罗风缓缓走来,站在墓碑旁,蹲下,抚着墓碑上宋可卿的照片。
伊翎峰忽然冲过去,揪住他的领口把他拽起,又挥拳将他打倒在地,用嘶哑的嗓音吼着:“你有什么资格出现在这里?!”
白罗风的视线越过他,仍看向墓碑,“不管怎样,我还是想来送她一程。”
“你配么?!”伊翎峰狠狠地咬着牙,压抑着想杀他的欲望。
白罗风笑着站起来,“我不配?我为什么不配?是她背叛我在先。你?你不过是他们苟且生下的杂种!你又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伊翎峰怒极反笑,一脚又把刚站起的白罗风踹倒在地,“既然这样,那我这个杂种!就用你的死来祭奠她!”
黑漆漆的枪口顿时指向了白罗风。白罗风冷笑着,“你连子弹都没有上膛就敢拿枪指着我?是太自大了,还是真以为你白叔老了?!”话音未落,便弹身向前,想要夺下伊翎峰手中的枪。速度之快,哪里像个老人。
“砰”枪响,白罗风愕然倒地。伊翎峰面无表情地迈步走到他身旁,抬脚踩在他的胸口,白罗风顿时呕出一口血。伊翎峰淡淡地说着:“在见到敌人之前一定要把子弹上膛,这可是你亲口告诉我的道理,白叔你忘了吧?”
最终白罗风也是不甘心的瞪大了眼睛,伊翎峰就蹲下,给他合上眼睛。
这个他曾经当做父亲一般尊敬的人,终究是被他亲手杀死了。
“将他的尸体怎么办?”泽颜走到他的身边,低头,看到他握枪的手仍在发抖。
“海葬。”伊翎峰的声音再次不带有任何感情,然后他转过身,“白罗风的后事你找别人去做,你来帮我预约一下孙不臣,就说我找他谈有关军火的事。”
王洛有事去了澳洲,最近他手下信得过的,就只有泽颜了。
回去之后,泽颜就给王洛打电话,过了好久,王洛才接起来,声音好像还有些疲惫,“小姐,什么事?”
“你在国内么?父亲有事要你帮忙处理。”
王洛又顿了好久,才又接道:“我现在在澳洲,还有些事,不能赶回去了,麻烦小姐帮忙处理一下吧。”
“哦,那也可以。”泽颜露出一个微妙的笑,“贵夫人身体怎样了?”
“……还好,”王洛又是一顿,“多谢小姐挂念。”
说完,王洛就挂断了电话。泽颜愣愣的握着手机,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回过神,赶紧把那手机扔在了沙发上,好像那手机是块烫手的炭。
她的眼神不停的波动着,神经质地呢喃着:“我怎么这样……我怎么可以这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