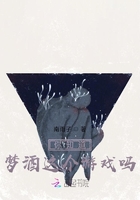而夏文渊此时则没心思跟这个怕老婆的二弟去计较什么,反而很轻松的去买益母草冲剂。
风轻呢,此时正蜷缩在暖暖的床上安静的思索这一天来发生的事情。
先是有关从金珍喜的脑海中提取的韩国李氏联合其他国家的财政集团所制定的那些对华阴谋,想着想着,便又想到了夏文渊说过的有关自己母亲的那些话。
嘴上再怎么说不想见她,可一个人的时候,风轻还是抵挡不住心底深处对母亲的渴望。
就算她再强,也不过是个女人而已。
这个世界上,哪个孩子不渴望母亲的怀抱,不贪恋母亲的溺爱,不想靠在母亲的怀抱里听她唱一曲催眠曲,美美的一觉睡到天亮?
一个人纵然活到五六十岁,在他的母亲面前依然可以撒娇,可以任性,可以耍耍小孩子的脾气。
作为子女纵然满头白发,在母亲面前依然是长不大的孩子。
所以,风轻就算说一千遍自己没有父母,自己是一个孤儿,也抵不上夏文渊那一句:不如我陪你去香港,去看看你的母亲?
她思绪正浓时,房门被推开。
天生的敏感让她立刻从沉思中惊醒,原本枕在腮边的手悄然伸入枕头底下,握住了碧灵玉簪。
卧室门被大大咧咧的推开,门口站着发丝凌乱的夏文渊。
“回来了?”风轻的手从枕头底下拿回来,轻轻地翻身,把棉被抱在怀里,慵懒的问道。
“还痛吗?我帮你买了这个。”夏文渊说着,走到风轻的身边,把那盒益母草放在床头柜上,却伸手去摸她的额头,“药店的人说,有些身体虚弱的人在这个时候还可能会发烧。你没事吧?”
风轻听明白夏文渊的话之后,目光落在那盒极其平凡的益母草冲剂上,很想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从心里骂道,你这个天下第一号的大傻瓜,难道忘了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神农氏后裔,自然懂得如何对待这些小问题,怎么可能会让自己再受这种疼痛呢?可是这一份简单的傻傻的关心,又让她视线渐渐地模糊,喉间有些哽咽,便悄悄地扭过脸,埋进枕头中,让自己眼底的酸涩渐渐地褪去,闷声说了一句:“困死了。你去别的房间睡,别烦我。”
“唔……我不碰你。也不去别的房间。”夏文渊说着,打开一包冲剂倒进水杯里,用热水冲开放在床头柜上,摸了摸风轻有些凌乱的长发说道,“一会儿把它喝掉,别等太凉了。那样就没效果了。我去洗澡,你喝了先睡。”
风轻点点头,没有说话。
夏文渊笑笑,起身脱掉外套,拿了浴袍进了洗手间。
当他再出来时,床头柜上那杯益母草冲剂已经被喝掉,床上蜷缩的人也已经沉沉的睡去。他轻轻地爬上床,把灯光调暗,然后侧躺着靠在床头安静的看着熟睡的女人。
巴掌大的小脸在这一刻特别安静。
没有了平时神采飞扬的笑和盛气凌人的怒,也没有了皱眉沉思和悲伤痛苦。她睡得像个婴儿一样安宁,仿佛是睡在温暖巢穴里的幸福的小鸟。任凭外边寒风暴雪,她只是安静的睡,安静的成长,安静的快乐。
这样的风轻,在夏文渊看来是那么柔弱,和这个世界上被男人捧在手心里的任何一个女孩儿一样,比如夏文涛的老婆卓文雅,比如夏文嬛,周密雨,比如杜思哲的女儿那个叫扣子的小姑娘……
这一刻,男人的情念仿佛成了某种羞耻的东西,夏文渊连想一想都觉得与眼前的画面是一种败笔,于是他轻轻地靠近,伸出手臂把熟睡的女人搂进自己的臂弯里。
熟睡中的风轻仿佛感觉到夏文渊身上的特殊味道,无意识的往他的怀里靠了靠,寻找到一个自己舒适的位置躺好,手臂不自觉地缠住他的腰,靠在他胸前咕哝了一句什么继续沉睡。
夏文渊苦笑,想起吃饭前自己在心里发的誓言,好像是说,不把她狠狠地折腾一顿就跟她姓?
哎!算了,跟她姓就跟她姓吧。对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较什么劲儿呢。
第二天风轻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枕在夏文渊的胳膊上睡了一夜,而这个家伙居然维持着一个十分别扭的姿势躺了一夜,估计睡得十分不舒服,这会儿虽然还在睡梦中,但却眉头紧皱,好像正忍受着什么酷刑。
于是她轻轻地动了动自己的身子,想从他的怀里挪出去,好让他睡得舒服一点,熟料刚一扭腰,便被身上的手臂紧紧地箍住。
风轻瞬间即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便不好意思的干咳了两下,说道:“首长,早上好啊。”
“嗯。”夏文渊虽然从理智上决定了放弃收拾这个女人,但他毕竟是血气方刚的男人。心爱的女人就在怀里软软的靠着自己,两个人相拥而眠,却什么事儿也做不成,可谓是对他最残酷的折磨。
“那什么,我睡好了。不如你先放开我,再好好地睡一觉呀?”风轻说着,又轻轻地动了动身子,试图在不惹怒他的情况下立刻这张柔软的床。虽然她有起床气,也很贪恋这张国王尺寸的舒适的大床。
“你再动一下,我不介意在你这种时刻解决要解决的问题。”
“唔,你好残忍。”风轻无辜的叹息,“怎么可以凌虐女人?”
“你才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小东西!”夏文渊低吼一声,双眼几乎要喷出火来。他喘着粗气静静的看着她,浑身带着蓄势待发的巨大压迫力,眼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