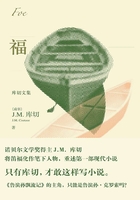------------
洋式大钟沉闷地发出一声咚响,尽职地提醒着人们此刻已是深夜,寒风透过衣襟侵蚀身骨,让人不由打着冷战。这个时间,寻常人家怕是早已睡下,隶军行辕内却是灯火通明。婆子下人们进进出出,眉目间都是藏不住的慌乱。
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呛人的烟味,仁德医院的那场大火来得太凶猛,又蹊跷。从前方派回来的卫兵,身着清一色的军衣,表情沉默却威严,怀中的长枪由月光一照,亮得刺眼。被强行拉来的吴妈只觉得自己的小命都要没了一样,想着这是做了什么孽啊,被这种人家请来接产。
“啊……啊……”
被安放在榻上的女人紧皱双眉,额上冒出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汗,明明是彻骨的痛,她却只是压着嗓子小声地抽泣。女人的双颊已涨得通红,她却还是拼了命地憋着气,双手胡乱在绸缎床面上划着,像是在找一个能够抓紧的东西。
吴妈看着心里不忍,将蘸着热水的毛巾递给旁边的丫头,自己倾身把手伸过去给她抓。榻上的女人果然将吴妈的手一下子抓紧,大颗大颗的泪珠也从眼角落下。
“妈妈……”
女子的哭声让吴妈的心不由得跟着疼。这样的打扮,这样的俊俏模样,想必也是一位大户人家的千金,可怎么偏偏就惹上了这样的人家,受这样的罪。
行辕里里外外差不多所有的丫头都用上了,烧水的、擦身的、点香的,所有人不敢有一点差池,都按照产婆吴妈的吩咐伺候着。可是都过去大半个时辰,那女人的双腿间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再去拿些热水来。”吴妈将手从女人的怀里抽出,又拿白帕子给她擦了擦额头的汗。老实讲,虽然吴妈已做了半辈子的产婆,这次接产却是她最害怕的。
吴妈只想着幸亏羊水还没破,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又将丫头重新热好的毛巾拿过来。她将女人的衣裙往上掀了掀,想给她擦拭一下小腹缓解她的疼痛。刚坐下,吴妈的脸却一下子变得煞白。刚刚还说羊水没破,这转眼的功夫,床单都打湿了一片。
吴妈让丫头在女人身下垫了几个羽绒枕头,然后赶紧起身给她揉着肚子。
“夫人,来憋住一口气,慢慢加劲儿啊,用力!”
床上的女人几乎全身湿遍,痛苦的哭喊让屋里伺候着的人全都捏了一把汗。
“再使点劲儿。”吴妈的整个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却还是没有看到孩子的一根头发。
毛巾“咚”的一声被丢进水盆里,吴妈慌慌张张地往帐外跑去,大喊着:“作孽,作孽啊,这可是要出人命了!”门一推开,正撞上要往里进的男人。
“干什么这么慌张?!”
吴妈抬头看了眼站在门外的男人,不禁一怔,这可不就是这大宅子的主人,自己那不孝子一心要跟随的隶军新司令段奕铭吗?来安亭之前,吴妈曾经在儿子拿回的报纸上见过他的样子,今日当真面对着面见着了,更是觉得这人一副天生让人惧怕的模样,眼神凌厉威严,眉间微皱,戎装金属肩章上还挂着从公署匆匆赶回时带着的一层薄霜。
“啊!”
半敞的屋内突然传来一声尖叫。腹间越来越严重的绞痛,让慕景仪终于再也控制不住地大声喊了出来。她双手紧紧地抓着枕下的床单,她疼,如万劫难复。
“她怎么了?!”段奕铭一把抓住吴妈的衣领,声音像是从什么器皿里发出来的一样,让她从头到脚直发寒。
“段、段、司令,太、太太怕是难、难产了。”吴妈没见过什么世面,竟被吓得口吃起来。
段奕铭推着她一起进了屋内,命令道:“赶紧给我想办法!”
吴妈哪还敢上前,“扑通”一声跪在原地,哆哆嗦嗦地说:“司、司令,这、这、老身也没法子啊,找、找、大夫,或许还能……”
“何家成!”段奕铭一掌又把门推开,脖颈上的青筋突起。他与产婆的对话,贴身随从侍卫长何家成早已经听得清清楚楚。待段奕铭一声令下,他便立刻带人驾车去了最近的诊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