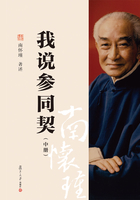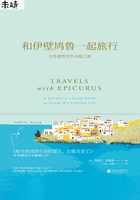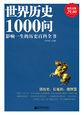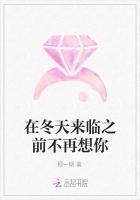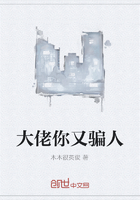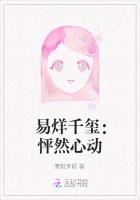人身最圣洁的器官是会说话的舌头,应该说到做到。
——谚语
言与行的关系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圣哲们所关注的问题。言,既是思维的产物,又是心声的表达,更是行动的宣示。在将思想和设计付诸行动之前,会有一个话语表达的阶段。这样的话语,既是思想和设计的表白,也是行动的动员与指引。人的行动有预先的设计,有连续不断的环节,有复杂多变的程序,而不像人之外的动物那样简单机械,那样无言而动,那样不宣而行。
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我们的先哲们非常重视言与行之间的紧密关系,在言与行的统一关系中来阐述“言”与“行”,以此来修身。《素书》云:“高行微言,所以修身。”孔子讲:“言必信,行必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历史的发展正被孔子言中,历朝历代的小人都是以摇唇鼓舌来乱行,作践人类高贵的天性——言行一致。由此,先哲们又一再强调“行”的重要性。春秋时期的庄子早就告诫我们:“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宋代的朱熹说得更为严重:“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印度有一句精彩的谚语:“人身最圣洁的器官是会说话的舌头,应该说到做到。”
在言与行的关系问题上,大体可以区分为四种情形。一是言行相背。言不及意也罢,言不由衷也罢,言以惑众也罢,都是言与行相背离,其特征是“声东击西”、“南辕北辙”;二是言出行无。常常是“干打雷,不下雨”,只闻言之声,不见行之影,其特点是食言脸不红,说话不算数;三是言出行缓。凿凿之言已落地有声,缓缓之行姗姗来迟,常常是错过了时机,耽误了事情,其特点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四是言出行随。语言像是被海浪推涌的涛声,闻其声近便见其波涌,其特点是说到做到,不放空炮,这是最应倡导的好作风。
言出行随,既是一个人的思维水准、表达能力的展现,又是一个人品德修养、行为能力的体现,更是一个人内外相应、高度负责的显现。
言出行随,重在一个“随”字。行动随着语言而产生,才能使得语言富有内涵、富有价值、富有生命力。先哲们总是告诫我们:“人前做得出的方可说,人前说得出的方可做。”(《史典·愿体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言辞是行动的影子。”萨迪说得更明白:“语言虽然使人成为万物之灵,只说空话也就不比畜生高明。”
言出行随,就是要始终不忘“言”之内容、“言”之目标,要靠“行”来完成、要靠“行”来实现。无“行”之“言”是空言,是妄语,是假话,是欺人之谈。行动迟缓也将贻害其“言”。“言语”都是有时间、条件和针对性的,都是有机缘、设计和阶段性的。若行动迟缓,不能紧随其“言”,就会丧失上述的方方面面,也同样会使其“言”放空。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言出行随,还要注意做到“慎言”。所谓“慎言”,就是当我们的行动能力与条件有限时,不可毫无顾忌地妄言狂语。要量力而行,也要量力而言。宁可把话说得小些,也要把事办得好些。大言不惭是万万要不得的。句句着实不落空,方是慎言。
在我们做事之前,往往要先“心动”,心不动则行不动。但是,社会的实践告诉我们:“心动带动行动,只有心动没有行动是空想,只有行动没有心动是妄行。”
最近我读了一本《西方文化史》,其中在叙述古希腊哲学家与近代知识分子的区别时,有“静观的人”与“行动的人生”的说法。当今时代显然更赞成“行动的人生”。马克思就说过:“哲学家从来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真正的关键是改变它。”所以徒尚宣言不务行动,遇事说大话吹牛皮,对自己的话不负责任的现象被人们称为“泡沫文化”。面对“泡沫文化”这种浮躁的风气,强调言出行随就更有必要性。
言出行随,是君子之风!是发展之法!是昌盛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