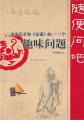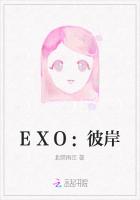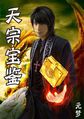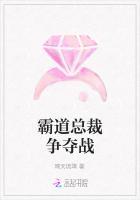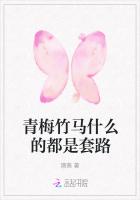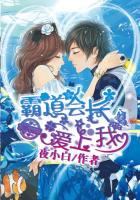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过。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见利思义”,这句话最早出于《论语·宪问》。多少年来,“利”与“义”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有人认为,在孔孟的儒家理论中,“利”与“义”是对立着的,取“利”则不讲“义”,讲“义”则不要“利”。其实,“利”与“义”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它们互相影响,存在于一个事物之中。当物质利益得到时,并不意味着道义上的丧失,当道义上达到完美境界时,并不是利益上必然受损。但是,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当“利”与“义”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与“见利思义”截然相反的是“见利忘义”。《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虽然是对人们行为带有偏见的解释——它忽视了“义”在人们心目中应有的地位与生活中正义可以战胜邪恶的现实,但它也道出了见利忘义和保利弃义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孟子·告子上》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就是说,求生存是我所希望的,求仁义也是我所希望的,当二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时候,那么我就宁可舍去生命而争取道义上的完美。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在生死面前,大义凛然,慷慨就义,他们连生命都置之度外了,更何谈从中取利呢?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见义勇为的人,在别人为难之时或危险之际,敢于挺身而出,不怕牺牲,维护正义,他们并不曾想得到什么利益与好处,所以他们的英勇行为是舍个人之利,求人生之大义。
孟子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过。”不合道义的,即使一箪饭也不能接受;合乎道义的事,像舜继承尧的天下那也不算过分。要把义摆在首位,决不见利忘义,更不能唯利是图,“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古时候,有个叫列子的人,家里很穷。一天,郑国宰相给他送去粮食,列子说什么也不肯接受。他妻子埋怨说,只听说跟有道德、有才学的人能过上好日子,可我们跟着你饿得皮包骨了,宰相让人送来粮食你又不要,难道你连妻子儿女的性命都不要了吗?列子说,宰相并不是真正爱惜我,只不过听人说我是贤人,他给我粮食是为了落一个爱惜贤才的好名声。如果有一天别人说我的坏话,他照样可以听别人的话来加罪于我,所以我不能接受。列子宁可清贫度日,也要维护自身的名誉、维护道义。
对于物质上的索取要讲究义,那么对待荣誉是不是可以不讲义了呢?楚昭王被伍子胥打垮,出逃在外,屠羊店的老板屠羊说也跟着出逃。昭王复国后,封赏随同逃难的人,屠羊说却不接受赏赐。他说大王亡国失位我没有过错,大王复位我又没有功劳,这赏赐我不能接受。楚昭王一听十分感动,要让他出任三公。屠羊说讲,三公职位比我杀羊为生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可我不能图荣华富贵而坏了自己的名声。三公之职不可谓不高,他不动心;昭王的封赏不可谓不厚,他不予理睬,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义重于一切。屠羊说要用自己的劳动获得应有的报酬,这样才心安理得。我们现在提倡要做于社会、于人民有益的事情,只有根除利己主义,克服“保利弃义”恶习,才能以义为重,见利思义,从而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
每个人都有物质欲望,在讲义的同时,不能忽视利的正当所取,否则只能流于空谈。只有利中见义,义中得利,以利见义,利义共存,才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北宋时期,在与党项族毗邻的边境上有一清涧城,时常遭邻敌骚扰,守城大将种世衡便奖励官吏与老百姓练习射箭,以增强防御能力,邻敌再也不敢侵犯。宋史上是这样记述的:种世衡曾督促吏民练习射箭,有过失的,射中就可释其罪,有请求办事者,也以能否射中来定夺。这样“人人自励,皆精于射”。如果种世衡不采取这种办法,只是一味地向老百姓讲大道理,动员人们练习射箭,是不会获得成功的。这就在于他把增强保家卫国的防御能力与群众的物质利益结合在了一起,让百姓得到了实惠,又提高了射箭技术。射箭本身是卫国人的一种本领,而学习本领又能得到实惠,这样百姓的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种世衡让百姓获利的同时又实现了“义”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