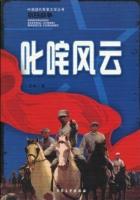王徽之(338—386),字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在《世说新语》里,有很多魏晋文人的潇洒故事,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这则“雪夜访戴”的佳话。
要论潇洒,能玩到如此令人叫绝的程度,从古至今,还无人与之颉颃。如今,不是没有潇洒的文人,也不是没有文人的潇洒故事,只是称得上为文人的今人,很遗憾,无论学养、教养、素养、修养这四养,实事求是地讲,较之古之文人要差池一点(有的,恐怕还不止一点)。因而,即使潇洒,也难免捉襟见肘,进退失据;纵有风雅,弄不好也会水尿裤裆,令人气短。
潇洒二字,谈何容易?也不是说潇就潇,说洒就洒的。冷眼旁观文坛半个世纪,有的,潇洒得起来;有的,潇洒不起来;更多数人,其实是在装潇洒。装,也就是演戏了,红脸、黑脸、白脸、三花脸、老绷着那架势,我看他们也挺累的。演好了尚好,演不好,拿不住那个劲,不知哪招哪式,露了马脚,不知哪腔哪调,错了板眼,一片倒彩,贻笑大方,也蛮不是味的。所以,从古至今,作家的内涵如何,才是能不能够潇洒起来的基础。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雪夜访戴”的主角王徽之的家族背景。
南北朝的琅琊王家,随晋室南渡以后,王徽之的叔祖父王导,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由于他的筹谋擘划,才得以使司马睿偏安江南一隅,使晋祚又延续了百年之久。所以,王家的门第之贵,南朝惟一。王徽之父亲王羲之,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大书法家。王徽之的弟弟王献之(344—386),字子敬,是与其父同样具有很大名气的书法家,为简文帝婿,任建威将军,吴兴太守等职。王徽之还有个哥哥王凝之(334—399),也是书法家,娶了谢家才女谢道韫,在这样一个风流蕴藉的家族环境下,一个个皆熏陶成“卓荦不羁,欲为傲达”的文人性格。
可以想象,从这样总揽过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的宰辅家门里走出来的年轻子弟,绝非今天那些有权有势有钱有背景人家的子弟,可以望其项背的。应该说,贵族这个衔头,谁都可以大言不惭地顶戴,但是,它也有四类:
甲,真正的贵族;
乙,暴发户式的贵族;
丙,装扮出来的假冒贵族;
丁,尚未洗净腿上泥巴的初始贵族。
这四类人站在一排,也许表面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本质上是存在着区别的。像王徽之以古老的门阀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潇洒,就以“雪夜访戴”这一场秀,不是随便一块什么料,就能行得出,做得到,秀得成的。
而时下那些认为有钱就能够买到一切,认为有权就等于拥有了一切的新贵们,我也真佩服他们那种以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的勇敢,觉得恶补一顿,便也八九不离十地像模像样了。于是,活像巴尔扎克笔下那些来到巴黎的外省绅士,勋章、宝石、假发、燕尾服、长柄眼镜、跳小步舞的紧身裤,都一律装备齐全。可贵族岂是好当的营生?一要有渊源,二要有传统,三要有气质,四更在于谈吐、举止、风度、仪态,所反映出来的器识、历练、修养、人品等等文化素质。一不留神,那呆鹅般的眼神,怔在那里,那傻张着的嘴,愣在那里,那习惯于跟在牛屁股后面的蹒跚步态,戳在那里,便把乡巴佬的本色,和盘托出了。
其实,有钱也好,有权也好,可以附庸风雅,无妨逢场作戏,但一定要善于藏拙,勿露马脚。即使你的吹鼓手,你的啦啦队,閧然叫绝,说你酷毙了,雅透了,您也千万别当真。别以为自己就是真雅,就是大雅而忘乎所以。记住******那首《沁园春》,也许是一帖清醒剂,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认为“稍逊风骚”,“略输文采”呢?问一问自己,究竟算个老几?
雅是一种文化、精神、学问、道德的长期积累的结果,雅是一种境界、意趣、品味、见识的综合素质的表现,琅琊王家,到了王徽之这一代,那记载着雅传统的厚厚家谱,不知翻过去多少页了?您哪,先生!所以,雅这个东西,表面上有,不算有,肚子里有,也不算有,只有骨子里有,基因里有,才算真有。
大家心知肚明,如今报纸上、电视上呶呶不休的那些文人雅事,只能说是要名、要利、要权、要色的赤裸裸自我表演,离真正的潇洒甚远。于是,谁也没有开会研究,谁也没有统一口径,约定俗成,一言以蔽之,统称之曰“炒作”。这个新名词,颇是那些急功近利的文化人状态的精彩表述。
中国文人的炒作行径,古已有之,并非什么新花样。老一辈,更老一辈,都玩过的,甚至玩得比现在的文人还地道,还高明,还不露痕迹,炒得你不觉其炒而堕入彀中。古人通常都是先炒自己,其次炒作品,因为那时不是商业社会,作品炒得再红火,与利益挂不上钩。多印少印,卖多卖少,随便自己。于是,王子猷就只有炒他自己。
不过,他的表演,固然有他的欲望和想得到的东西。但是,应该承认,他演技上乘,娴熟自然,不愠不火,恰到好处,不像时下那些下三烂的炒家,迫不及待,饥不择食,恶形恶状,令人不耻。这就是真贵族和装出来的贵族,真潇洒和做出来的潇洒,其不同之处了。
王子猷坐在船舱里,那一张脸上,炉火纯青得让你几乎猜不出他心底里,究竟在想什么。
剡溪,大约是今天的嵊县。旧时读郁达夫先生文章,知道他喜欢听“的笃班”,而且还伙同鲁迅先生一块去听过。“的笃班”,就是越剧的前身。从绍兴开车去这个越剧的发祥地,现在,估计用不了一个钟头。可在古代,得在曹娥江上坐一夜船才能到达。这位王羲之先生的五公子,欸乃桨声之中,雪花纷飞之夜,终于到了要去的这个地方。但故事来了,走到要去访问的隐士戴逵的家门口,正想举手叩关,忽而迟疑停住,然后转身返舟,依旧原路折回。
乘兴而去,去到了。兴尽而返,回来了。说白了,去,等于没去,说等于没去,可实际又还是去了。这位名士要的就是这份意思,见不见到戴逵,那是无所谓的。在意的是这个过程本身,过程既然有了,其他就不在话下了。
戴安道,《晋书》有其传,是一位很有名的隐士。隐士而有名,从道理上本说不通,但对旧文人而言,以隐求显,也算是一种猎取功名声望的手段,故而也不觉其滑稽。隐居的戴逵,半点也不寂寞,不但王子猷雪夜命舟专程探望,如尚书仆射王珣,如会稽内史谢玄,如太子太傅王道子,少傅王雅等朝廷显贵,都是他府上的常客。隐居,也是一种潇洒,隐居而不为人知,就潇洒不起来了,隐居而显达,隐居而名闻天下,那才是最了不起的潇洒。戴安道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这段风流轶事,经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记下来,大家读到这里,无不钦服,赞不绝口。
我也曾经心仪得不行过的,而且,还读到别人的文章,把王子猷这一次“雪夜寒江舟,把盏独酌人”的行径,足足那么誉扬了一通。但有时,细细考量过去,如果,王子猷去了剡溪,回到山阴,不那么张扬的话,除了他自己和几位划了一夜船,已经精疲力尽的船工,没有人会知道这次忽发奇想的旅行。所以,我一直以小人之心忖度,王徽之也是在演潇洒,在营造他在时人心目中的风雅形象。
好像,这位公子哥,也难逃炒作之嫌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膺服他的高明,高明在于他这样做了以后,不仅名噪一时,而且成为千古风雅。更高明的是,他这样做了以后,别人再也无法重新来过。他把事情做绝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地悠悠,只此一次,他独领风骚。你能不为这样顿成绝唱的“秀”,五体投地吗?
现在,即使你雇一架直升机,飞过去,又回转,别人只会视你神经有问题,而不会赞扬;知道这典故者,顶多笑笑,说一句东施效颦,就够客气的了。而且,我也不相信今日之现用现交的文人才子,会那么冒傻气,投资于一位马上见不到回报效益的隐士?除非那是一位刊发文章并附“美女”照一帧的同行,才肯去切磋切磋的。这也是当代文坛那些女作家的裙后,总尾随一大批护花使者的原因。
老实讲,从有皇帝那阵,迄至今日,写作和写作的人,基本上都很“物质化”了,功利的目的,压倒了其他一切。也许,在性腺、金钱、权欲的驱动下,有可能不辞劳苦,奔波于途,去做一件什么事,去看一位什么人,前提必须是对自己有利。但是,穷酸秀才,囊中羞涩,广文先生,捉襟见肘,想潇洒,爱潇洒,以潇洒自命,但要真的潇洒起来,也并非容易的事。而且,几乎很难做到王子猷如此大牌的潇洒。银两充足者,未必具有这等雅兴,而涌上来这份突发奇想的情致者,也不会绝对没有;可物质、精神两手均不硬,就大牌不了。所以,这就是“雪夜访戴”成为后代文人艳羡话题的原因。
王子猷,豪门出身,高官子弟,本人也是黄门侍郎,骑兵参军,至少也是正师级的干部,官、钱、位,应该是说得过去的了,不是所有文人都能达到的境界。比起那些十年寒窗,熬尽灯油,蹭蹬科场,拼命八股的人,不知快活多少倍?按常理而言,王子猷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去张罗,去铺垫,去造势,去促销自己了,还有什么不够心满意足的地方呢?
我也常常替这位古人纳闷,干吗呀,子猷先生,你累心不累心啊?
正如那些报纸上天天见名字,荧屏上晚晚见形象,书店里处处见作品,网络上时时被点击的红人,令我不解一样,怎么总是没完没了地,永无厌足地折腾呢?闹不闹?烦不烦?
后来,我明白了。当他们才思衰竭,想象匮乏,灵感顿失,江郎才尽,创作衰势不可挽回时,当他们预感到众星拱月的风光不再,热闹场面的难以为继,眼见拥趸者渐渐离去而前路堪忧时,其折腾的能量,反而成倍地增加。
因为你想罢,别人也不让你罢,靠你卖钱,靠你噉饭的人,恐怕轻易也不会让你罢。再说,你已经拿大顶,头朝下倒立在那里了,成了时人注目的中心,你也不能就此拉倒。至少,有人向你讨钱的帽子里扔钢镚,至少,还有人为你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喝彩,因此,你自己也不想罢。一罢,全完,不就白费劲了吗?于是,只好抱着生命不息、炒作不止的恒心,继续卵子朝上头朝下的竖立在那里。
“雪夜访戴”的主角,虽然高明,说穿了,也是很在意这种热闹效应的,这也是所有热衷于炒作者的共同心态。要是,听不到别人嘴里念叨自己的名字,看不到别人眼里关注自己的神色,觉不出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有环绕自己的一圈人,那一份寥落、寂寞、冷清、凄凄惨惨戚戚,真像是有无数的蠕虫,在咬啮着自己那颗已经受不了冷落的心。
于是,不制造一些新闻,不弄出一些响动,他是受不了的。于是,又看到了这位公子哥的表演:“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命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
如果放在今天,娱乐版肯定会有“王子猷大闹竹林”的报道。
可惜的是,在《世说新语》这部书里,还有一则情节类似的记载,未能让王徽之专美于前。偏偏与他抢风头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弟弟王子敬,即王献之。当然也有可能王羲之生了五个儿子,这个叫“之”,那个也叫“之”,很容易搅混,也许是同一件事,同一个人,也未可知。书中说:
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傍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坐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着门外,怡然不屑。
同样的剧情,不同样的结局,两相比较,倒能看得出来,一收一放之间,两兄弟的实力差距。他弟弟所以比他更有恃无恐些,更浑不在乎些,因为王献之的谱,能摆得更大些。而他,一个骑兵参军,是无法与驸马爷相比;现在还查不出王献之逛顾辟疆花园赏竹的时候,是否已任吴兴太守,若如此,这狂,就更没说的了。这样一比,顶多是个肩扛四个豆的王子猷,能不黯然失色吗?
其实,王谢子弟,谁不标榜清高,这种权位上的差别,会对王子猷产生影响而情绪低落吗?似乎应该不,然而却不能不。中国的文人,除极个别者,在乎权位,甚于在乎金钱,为之朝思暮想,为之夙夜匪懈,要甚于一般的追名逐利。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兴文字狱,不知多少文人掉了脑袋,但无数举子,仍旧本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地做那金榜题名的梦,冀图从皇帝手里接过那件黄马褂。官之大小,权之轻重,是十分在乎的,连死了以后的谥名,都全力以赴去争的。别看他们口口声声不为五斗米折腰,不稀罕那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但在有可能得到的权位面前,没有一个人会掉头不顾而去的。
就看当今那些上了台面的文人,那么在意官位之大小,那么关心级别之高低,那么看重座驾之好坏,那么计较利益之多少,便可想知古人的演潇洒,装潇洒,都不会离这物质的原动力太远。
因之,对于敏感的王子猷而言,虽然他和他的弟兄们都拥有与生俱来的风流,和根本推不开的富贵,但客观存在着的高低之别,上下之分,这种心理上的隐痛,也会使王徽之活得不那么百分之百的开心。在王羲之的几个儿子中间,王子猷,一直处于这种觉不出来的压抑气氛之中,所以,他才有“雪夜访戴”、“竹园闹主”的表演,他不但需要人知道他的存在,更需要人为他的存在喝彩鼓掌叫好欢呼。
然而,他总是失落,有一次,他们弟兄三人“共诣谢安”。在王导以后,这位曾经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便是朝野众望所归的人物了。不过,在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隐居,时人有“谢安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舆论,把希望寄托于他。所以,这位头上有光圈的名流的人物品评,一句话,便举足轻重。“二兄(徽之、操之)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小者佳。’客问其故,安曰:‘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而且,谢安对王献之“其钦爱之,请为长史,安进号卫将军,复为长史”,如此重用,如此信任,在一向自视甚高的王子猷心灵里,能不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吗?
他为人放诞傲慢,不拘形迹。哀帝兴宁年间,曾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带,不理政事。后来,桓温将他安排到自己老弟,车骑将军桓冲手下,任骑兵参军,成了一个弼马温的角色。
这种与他家门光荣不相称,与他兄弟们职务不相称的安排,也不能让他心理平衡。有一次桓冲问他:“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晋书》)最后一句,是孔子答复子路的话,他竟然拿来调侃上司,这潇洒也相当够意思的了。
他是潇洒的文人,却要去做不潇洒的现役军官,有点滑稽,不过也不奇怪,这是拥有统治权力的几大家族间的平衡需要。所以,他在大军阀桓温手下做事,只是挂名而并不履职,吟风唱月,赏花问柳。别看这位手握重兵的帅爷,能够废掉皇帝,差点要自立为王,但拿这位吊儿郎当的部下,没法办。吃你的粮,拿你的饷,事情是绝不做的,所以,才有这等潇洒的闲心,半夜三更,心血来潮,顶风冒雪,去看一位相距遥远的朋友。
试想一下,琅琊王家,东晋政权中的第一豪门,皇帝都不得不让出龙椅的半边请姓王的坐,现在他却坐在冷板凳上,受命于行伍,那情绪会好起来吗?
更何况他的婚姻状态,显然属于太过平庸一类,在史书上找不见一笔记载,比之娶了金枝玉叶的弟弟王献之,比之讨了谢家才女的哥哥王凝之,王猷之也无法神采飞扬起来。尤其他弟弟在当驸马前,与爱妾桃叶浪漫的恋情,与前妻郝氏缱绻的挚爱,那首为心上人写的《桃叶复桃叶》的爱情歌曲,竟流行江南一带,所有这些风雅绮丽的韵事,都与王子猷无缘,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岂止是感到扫兴、窝囊、别扭呢?更多的倒怕是泛上的酸不溜丢的苦恼吧?
所以,他时不时地要潇洒一番,要制造一些足够上娱乐版的头条新闻,在当时的南京城里,他肯定是娱记紧紧追踪的明星。“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说新语》)
直到他弟弟垂危之际,出于手足之情,使他道出了心底的隐衷,“吾才位不如弟”,正因为才力的不逮,权位的差别,才不得不一个劲地装潇洒,演潇洒,填补心灵中的空虚。然而,王献之一死,他也未能活多久,至此,于是,这位公子,也就结束他不得不潇洒的一生。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懂得当今文坛,那些热衷于炒作的作家,干吗要死去活来地折腾了。估计这些先生们,女士们,与王子猷一样,大概都有他(她)们见不得人的精神上的隐痛,和不可告人的内心里的苦衷。
乍读《世说新语》,觉得古人要比今人潇洒,而且,越离得远的古人,越潇洒。其实,古人比今人,未必高明许多,他们和我们应该没有什么两样的。只是经过漫长历史的沉淀以后,那些欠潇洒和不潇洒的方面,为尊者讳,隐恶扬善,被中国人那好则极好,孬则极孬的极端思维抹煞掉了,剩下来就只有完美。
文人嘛,大部分具有表现欲,甚者,还具有强烈的表演欲。这两者,从本质上看,是一回事,只是低度酒和高度酒的区别而已。从语义上推敲,表演应该要比表现更外在,更夸张一些。表现,主要是突出自己,让别人知道他的什么,而这个什么,基本上还是属于真我。表演,当然也是突出自己,但突出的什么,很有可能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假我,或者压根儿的非我。然而,无论他怎么兴高采烈地表现或者表演,总是会有他内心里不快乐的一面。
偶读明代唐寅的诗作,题为《梦》:“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科,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调破邯郸景,依旧残灯照半床。”
小时候,随大人在书场听弹词《三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谁也比不上这位风流倜傥的吴中才子唐解元,更快活无比,更开心自在,更得心应手,更放浪不羁的了。他的潇洒,他的炒作,他的表现,他的表演,无不臻于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从这首诗,从这其实也是他伴其一生的梦里,我们不也体会出他内心深处的阵阵隐痛,聊作佯狂的背后苦衷,和那掩饰不住的怅惘嘛!
所以说,潇洒难得,难得潇洒,想到这里,对于时下喧嚣的市场化炒作,对于时下文化人的忙忙碌碌,轰轰烈烈,奇奇怪怪,热热闹闹,也仿佛多了一份理解,也就随之豁然了。于是,还有什么好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