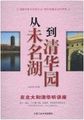系统化和结构化是民族国家的特征,也是国家型期社会和个人的典型技术方式,在国家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生活世界等等方面,使社会系统化和结构化的同一过程中,国家也以公民权、国民性、民族认同、福利化、角色化使个人与社会实现了整合。而且,国家的训诫和监控(通过行政、司法、法规、学校,以及监狱、劳教所等制度设置和职业化专家阶层)使型塑与整合成为不断持续的过程。这种双向过程使社会和个人成为了系统运作的载体,从而形成了社会与个人的体化同构关系。因而国家的变化也就意味着社会与个人之间的某些关系方式变化。首先,国家向市场、企业、生活世界、个人选择等的放权,在这些领域中确实出现了以国家型塑和整合为基础的社会与个人原有关系方式的大量削弱甚至瓦解。但同时,由于国家财政实力的提高、权力以及行政和司法体系的专家化,信息网络技术的运用等等,对社会和个人的管理控制能力也在提高。而且,由于当代社会的非预期后果频繁、反社会性行动的大量存在,使国家的责任成为了社会的需要,因而国家对社会和个人的总体监控实际上趋于强化。
在市场和经济、政治、文化、个人活动超越了地缘限制的同一过程中,资源转化系统也出现了全球一体化趋势,正在进一步摧毁血缘、地缘、业缘等社会与个人的传统关系纽带。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中,这类关系方式的存在越来越屈从于资源转换系统的运作需要,归根结蒂是屈从于利益原则和技术理性原则的需要。多元利益使个人的个性、目标选择、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地多样化和风格化,但技术理性则使互有差异的个人样式和风格留下了相似的社会标记,因而个人的多样化和风格化更具当代社会的性状和特征。此外,传统关系纽带的销蚀和资源转换系统的运转,使个人在情感上与社会愈加疏离,但在生存上对社会和他人却更加依赖。
生活世界在更大范围出现的国家权力的“盲区”,是青年、休闲、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群体的乐园,媒体信息、艺术创作的重要来源和试验场,大众文化和各种非主流文化的领地,也是后现代“文化精英”汲取灵感和宣泄失意愤懑的场所。但在实质上,生活世界(尤其是文化消费领域)被更深地卷入了资本周转和资源转换过程,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实现规模化、社会化消费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终端。因此,由生产过程预定、诱导和塑造消费的欲望、需求和满足方式,以及大众化、平民化趋势不仅是其突出的特征,也是使其继续保持运转的条件。如此一来,这一领域中的创造与模仿迅速转换,新颖与炒作频繁交替也就不可避免,结果是二者之间的基本界限一再发生模糊。所以,在个人间、群体问差异和多样化的虚假表象之下,总体上的一致性和重复性仍然是挥之不去的本质特征。
简要地说,现代性早期和扩展时期铸成的社会与个人的现代联结方式,迅速蜕变为了新的传统性,并受到动摇而趋于解体,这种不断的传统化与去传统化过程构成了现代性之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普遍性特质。当代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基本趋向:一种是与“新传统”关系方式的断裂,个人与社会越加疏离,社会在同过程中电史为多元化;另一种是建立“更现代性”的关系方式,实现社会与个人之间多样性的联结和组合,并形成不同的现代社会共同体。在我们看来,这两种基本趋势的共同作用,既可以造成一个充满歧见、不同观念相互背离、不同价值相互对立、不同行动相互排斥的社会世界,也会使个人及其社会共同体都真正懂得相互宽容、承认彼此的正当性的重要价值,从而避免一个被无数的独断主义者和个人霸权主义者充斥的世界。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对于社会学具有的元性质和基本性质,这一关系的变化必然将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探讨推向对元理论和元方法的深层追问。
对传统社会学的挑战。面对现代性的全球化,以民族国家的地缘社会情景为基础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局限降的显露,促使社会学对自身知识系统的建构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跨国社会过程和全球社会过程的出现所导致的后果,是民族国家架构下的地缘社会情景及其经验事实发生了变化,国家地缘社会与跨国社会、全球社会的共同作用改变了行为情景的单一性质,大量的当代社会重大经验事件出现在国家社会、跨国社会、全球社会的相互交错或相互交替的情景中,使社会事件的外在关联和内在结构都变得空前复杂化。这就要求社会学对于国家地缘社会与跨国社会、全球社会的关联,对于复杂情景结构中的经验事件过程,具有高度的想象力和包容性,以产生对当代社会的宏观整体过程的俯视性理论效果。如此一来,以往社会学中传统的、流于褊狭的思维模式、知识积累和建构方式明显地不再适用。而且,这一局面对实证传统的正统地位造成了动摇,为人文传统的崛起提供了新的机缘,形成了自然科学型社会学衰落与人文科学型社会学兴盛的总体格局。与此关联的另一个后果是,关于社会学知识的价值争论在当代社会学理论范域中也在日渐淡出。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社会学知识的价值争论上,是与实证社会学及其方法相联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正统立场”的淡出。如吉登斯认为:“社会学……并没有按照人们所说的自然科学那种方式来积累知识”(吉登斯.2000:14)。吉登斯的“激进主义政治”、“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理论,已经表明了他对于社会学知识的价值争论所持的立场。
福柯则断定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或许,我们也应该完全抛弃那种传统的想象,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小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对这些‘权力-知识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从识主体相对于权力体系是否自由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相反,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总之,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相反,权力-知识,贯穿于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福柯,1999:29-30)。福柯的论断无疑是偏激的,但它有助于揭示认为知识能够无涉于价值或意识形态的观点的迂腐。
塞缨尔·亨廷顿指出:“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一个普世的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塞缪尔·亨廷顿,2002:88)。塞缨尔·亨廷顿详尽地阐述了文明与全球政治之间的关系。
总之,不再讳言知识与价值、知识与权力甚至知识与主流政治的关系,不再热衷于作超越价值立场的各种设想--这类设想本身就是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激烈对抗时代的产物,是当代社会学区别于以往的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特点。
在当代中国,国家在现代性全球化过程遇到的挑战,使国内社会转型面对多重现实:一方面是继续推进的与本土前现代性的断裂,另一方面则是与20余年中形成的转型社会的新传统性的断裂--这类新传统变得越来越与时不宜,同时还要面对不断增强的跨国影响和汇入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这种多重现实构成的转变过程注定是迅速流变,充满风险,历尽沧桑。其间,持续传统化的个人和向全球开放的社会如何能继续整合于民族国家?国家如何有效地实现自我反省与监控?个人幸福、社会进步、人的解放与国家政治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结?国家的事业如何与个人、社群和社会的利益相互协调?国家何以使内部的各社会共同体继续保持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形式?国家何以降低或化解个人、社群和社会的风险?这涉及劳资、贫富、代际、妇女、家庭、环境、生态等等复杂关系和现实问题,中国社会学必须对之做出理论上的回应。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学对跨国和全球情景中的国家社会问题的回应力正在增强。
现代性遭遇全球化的时代是社会学理论重建和理论范域的再拓展时期。从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学经过民主社会与转型社会的社会学到全球化阶段的社会学,社会学又一次超越了自我,进入到自其有史以来的意涵最为深邃、前景最为广阔的时段和空区。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
[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I999.
[4]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M1].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5]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6]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8]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9]马尔利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0]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1]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13]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14]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5]于尔根·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6]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17]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8]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社会学本土化从世界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
[19]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0]Abram,Historical Sociology[M].London:Open Books,1982.
[21]Alexander,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22]Foucault,Madness and Civilization;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reason [M].Pantheon,1965.
[23]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M].Pantheon,1972.
[24]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J].In The National Interest,Number 16Summer,1989.
[25]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Last Man[M].The Free Press,New York,1992.
[26]Harbermas,Theory and Practice[M].Beacon Press,1973.
[27]Harbermas,Communication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M].Beacon Press,1979.
[28]Jean-Francois I,yotard,Just Coming[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da Press,1980.
[29]Jean-Francois I,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da Press,1981.
[30]Philip Abrams,1982.Historical Sociology[M].Ithaca N.Y. :Comell University Press.
[31]Rob Stones,1996,Sociological Reasoning ;Towards Past-Moderm Sociology[M].Macmillanpress LTD,London.
[32]Ruth A.Wallace Alison Wolf,1998,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Expanding The Classical Tradition,Prentice-Hall,Upper Saddle River[M].New Jersey.
[33]Steven Best and Doulas Keller.Postmodem Theory[M].Macmillan,1991.
[作者简介]郑杭生(1936-),男,浙江杭州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王任.社会学和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信箱:zhenghsh@95777.com;杨敏,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系200I级博士生、副教授、邮编:100872。
[原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