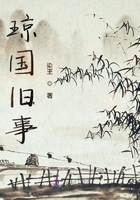“不,亲爱的你不会死的。使徒吩咐我要具有信心,他应允你祈祷,他认识基督,基督是爱他的,什么事都不会拒绝他……假如你会死掉,彼得就不会吩咐我要有信心,所以他对我说:‘具有信心吧!’——不会的,黎吉亚!基督会大发慈悲……他不想叫你死掉。他不许可的……我以救世主的名义对你发誓,彼得正在为你祈祷!”
接着是静默。挂在门口上的一盏长明灯已经熄灭了,但是满窗口射进了月光。在地下室对面的墙角里,一个孩子哭号了一阵,也静下来。外面传来了禁卫军的声音,他们在值班以后,正在墙脚下赌“十二点”。
“马库斯呀,”黎吉亚说,“基督本人曾经向天父呼号:‘把这苦杯从我嘴边拿开吧,’可是他仍然喝了下去,基督本人曾经死在十字架上,而现在有几千人正为他毁灭,那么他为什么要单单赦免我呢?马库斯,我是什么人呀?我曾经听见彼得说,他也将在虐杀中死掉,同他比较起来,我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禁卫军来捉我们的时候,我怕死、怕受苦,而现在我不再怕了。你看,这座监狱多么可怕,可是我就要到天国去了。你想想看,这里是皇帝,那里是温厚而又慈悲的救世主。而且那里没有死亡。你是爱我的,那么就想想看吧,我将是多么幸福。亲爱的马库斯呀,想想看,你也要到那里来找我的。”
说到这里,她吃力地喘着气,然后把他的手送到自己的唇边:
“马库斯r“什么事,亲爱的?”
“不要为我痛哭,要记住,你将到那里来找我的。我活得不长,可是上帝把你的灵魂给了我。因此我要对基督说,虽然我死了,虽然你眼看着我死掉,虽然你留在伤心苦恼里,你却不会冒犯他的意旨,而你会永远地爱着他。你一定会爱他并坚决地忍受着我的死亡。因为到那时他会再把我们结合,我爱你而且盼望同你在一起……”她又喘不过气来了,发出刚刚能够听得见的声音,她把话说完:
“这一点,你答应我吧,马库斯!”
维尼裘斯用颤抖的手抱住她,答道:
“凭你那神圣的头颅宣誓,我答应了!”
她那苍白的脸在黯淡的月光里显出了光彩,她又一次把他的手送到自己的唇边,悄悄说:
“我是你的妻!”墙外在赌“十二点”的禁卫军们,争吵得更响了。但是他们忘记了监狱、守卫和整个世界,他们从彼此的内心里感觉着那如天使般的灵魂,开始祈祷了。
约有三天,不如说约有三夜,没有任何事扰乱他们的平静。监狱的日常工作,就是把死人同活人、把病重的人同比较健康的人隔离,每逢那工作得困乏的狱卒在廊道里倒下来睡着了的时候,维尼裘斯便走进黎吉亚的土牢里,一直呆到曙光射进了栅栏的窗口。她把头靠在他的胸脯上,他们把话声放低谈着爱情和死亡。他们两个在思想和言谈中,甚至在心愿和希望中,不知不觉地脱离人生愈来愈远了,已经有失掉了人生的感觉。两个人像是从陆地登舟出航,再也看不见岸边,渐次沉入无限之中。两个人逐步变成彼此相爱而又爱着基督的忧郁的精灵,准备飞出去。在维尼裘斯的心里只偶尔像旋风一样猛然涌起一阵痛苦,有时他心里像闪电般掠过了一种希望,这是爱情和对于十字架上的上帝的信仰所生出的希望,可是他每天离开人世愈来愈远而倾心于死亡。每天早晨当他走出监狱的时候,像是在梦境里看着世界和城市,看着自己认识的人和与生活有关的事事物物。在他看来,一切似乎是奇怪、遥远、空虚和转瞬即逝的。就连苦刑的折磨都不再使他害怕了,因为他感到一个人在沉思默想中,用眼睛注视着别的东西就可以经历过来。两个人都觉得永恒已经开始在迎接他们。他们只是谈情说爱,谈他们将怎样相爱和怎样一起生活,不过那是在坟墓的彼方。如果说有时他们的思想又转回到现世上来,那也只像是正要走上长途旅行的人们在谈说着路上的准备罢了。的确有一片寂静在包围着他们,像是在沙漠里包围着两颗冷清清被人遗忘的柱石。他们惟一的愿望就是基督不要拆散他们,他们时刻在增强他们的信念,相信他会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爱着他,把他当作在无限的幸福与和平中结合他们的一条链条。仅管他们还活在世上,他们的身体却已摆脱世上的尘埃,两人的灵魂像泪珠那么纯净。在死亡的恐怖下,在悲惨和苦难中间,在监狱里,他们已经开始过着天国的生活,他彷如受到超度而变为圣徒,正牵着他的手引领他奔向无限生命的泉源。裴特洛纽斯从维尼裘斯脸上看出了日益增强的平静和一种相当奇妙的明朗,这是他以前所不能见到的,便不免大吃一惊。有时他甚至猜想维尼裘斯必定又找到了营救的办法,而由于维尼裘斯不肯把自己的希望向他吐露出来,很觉得别扭。他终于再也按捺不住,说道:
“现在你的样子与从前不同了。有什么秘密告诉我吧,因为我也希望能够帮助你。你有什么新计划呢?”
“已经布置好了,”维尼裘斯回答,“但这是你无能为力的。在她死后,我将供认我是个基督徒,追随她去。”
“那么说你已经绝望了吗?”
“不,我是抱着希望的。基督会把她交给我,我们将永远不再分离。”
裴特洛纽斯在前庭里踱来踱去,脸上分明看得出幻灭和不能忍耐的神情,接着他说:
“这种事用不着你们的基督,我们的‘死神’也同样能够办得到。”
可是维尼裘斯不开心地微笑着说道:
“不,亲爱的,你是不愿意理解这种事情的。”
“我不愿意也不能够裴特洛纽斯说,“眼前不是辩论的时候,可是还记得当我们要把她从老监狱里救出来而失败了的时候,我对你讲过的话吗?我丧失了一切希望。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你曾经说:‘我相信基督会把她交还给我。’那么就让他把她交还给你吧。如果我把一个无价之宝的酒杯抛进海里,我们的众神中任何一个,也不会把它送还给我,如果你们的神并不比他们更高明,我就不懂得为什么我要对他比对古老的众神更为尊敬呢?”“他会把她送还给我的。”维尼裘斯耸了耸肩膀。
“你可知道他问道,“明天在皇家花园里要拿基督徒当灯点吗?”
“明天吗?”维尼裘斯一再说。
眼见得那可怕的现实已经临近,他的心又怕又疼直在发抖。他想,这也许是他能陪黎吉亚同度的最后一夜了。于是他向裴特洛纽斯告别,匆忙跑去找“荒坟坑”的监工讨取出.但是失望正等着他,那监工不肯再把出入证交给他。
“大人,请你原谅。”他说。“我能办得到的事,都给你做过了,可是我不能不顾死活。今无晚上,要解走那些基督徒送进皇家花园里去。监狱里到处都有士兵和长官。要是他们认出了你,我和我的孩子们就完蛋啦。”
维尼裘斯晓得强求是没有用的。可是他仍然抱着一线希望,认为曾经见过他的那些士兵,甚至不要出入证都可以把他放进去,于是到了天黑,他像往常一样穿上拾尸人的紧身衣,头上包着布,动身到监狱去。
但是这一天,检査出入证要比平素更严格,此外,百人队长斯切维奴斯是一个古板的军人,从肉体到灵魂都忠于皇帝,他认出了维尼裘斯。
不过在他那一身钢铁的心胸里,分明对于不幸还闪现着一些同情的火星,他不但不用长枪敲打盾牌来报警,反而把维尼裘斯领到一旁,说道:
“大人,回你的公馆去B巴。我认得你,可是我不声张,我不愿意害你。但我不能放你进去,你走开吧,愿众神能安慰你。”
“你不能放我进去。”维尼裘斯说:“可是让我站在这儿看看解出去的是什么人吧。”“我接到的命令倒不禁止这个。”斯切维奴斯说。
维尼裘斯站在门前等着看被带出来的犯人。午夜时分,监狱的门才洞开,有好几排囚徒——男男女女和幼儿——走出来,由一小队武装的禁卫军护送着。这一夜非常晴朗明亮,所以不仅能看出那些不幸者的形影,也能辨别出他们的面貌。他们两个一排结成忧郁的长队伍,在寂静中行走,只有士兵们的武器的叮当声打破了寂静。解出来的人那么多,叫人觉得仿佛所有的土牢必定是空了。
在这长排的末尾,维尼裘斯清楚地看到医生戈劳库斯,可是没有黎吉亚和乌尔苏斯。
天还没黑,第一股人流就开始涌进皇家花园。群众身穿节日的服装,头戴花冠,高高兴兴唱着歌,大多数人喝得醉醺醺,正要走去参观这场堂皇的新表演。台克塔路上,埃米留斯桥上,台伯河对岸,凯旋路上,尼罗竞技场的四周,一直到梵蒂岗小山,全响彻着“火刑柱!异端嫌疑犯!”的喊声。在罗马曾经见过有人被烧死在柱子上,可是谁也没见过这么多的牺牲者。皇帝和蒂杰里奴斯为了遏止那从监狱里逐渐蔓延到全坡的传染病,打算马上了结那些基督徒,他们下令把所有监狱一扫而光,只留下供应广场演技的几十个人。所以当人群走入花园的大门,他们就吓得呆若木鸡了。在密密的丛林间以及傍依着草坪、灌木丛、池塘、田地和长满了花卉的广场,所有的大道和小路上,都挤满了涂着沥青的柱子,上面绑着基督教徒。从树木挡不住眼界的较高的地方,可以望见好多排柱子和装饰着花朵、桃金鑛、常春藤的人体,在高高低低的地面上一直伸延到远方,那么漫长,以致近在身前的柱子像是船杆,而在最远处的则像是插在土地里的彩色投枪或木杖。它们的数目多得超出群众的期望。这种情景真叫人以为有一个民族,全都被绑在柱子上供罗马和皇帝寻欢取乐。成群的观众,被某些牺牲者的形象或女性激起了好奇心的时候,便停立在个别的柱子前,看看那些人的面目、花冠和常春藤的花圈,然后向更远处继续走去诧异地问着自己:“会有这么多犯人吗?那刚能走路的小孩儿能够放火烧了罗马吗?”惊愕渐次变成了惴惴不安。
这时天黑下来,天空上闪烁着第一批繁星。靠近每一个犯人有一个奴隶站岗。他手中拿着火炬,当花园四处响起指示演技开场的喇叭声,奴隶就把火炬往柱脚一放。藏在花朵下浸了沥青的干草,立刻发出熠熠的光燃烧起来,火势上扬,把常春藤烤得枯干,抱住牺牲者的两脚向上飞腾。群众默不作声,花园里震响着漫无边际的一片呻吟声和痛苦的呼喊。不过,有一些牺牲者,面朝着星空,开始唱歌,赞美基督。人们静听着。较小的柱子上,有些幼儿发出尖锐的嗓门喊叫着“妈妈!妈妈!”这时就连那些铁石心肠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恐怖。有些喝醉酒的观众,当他们望见了小脑袋和纯洁的面貌痛苦得不成人样,或是孩子们在开始便在窒息的烟雾中晕过去的时候,他们心里也起了一阵寒栗。但是火焰向上飞扬,时刻捉取了新的玫瑰或常春藤的花冠。大道和小路照耀得彷如白昼,树丛、草坪、花卉的广场一片明亮,水槽里的水和池塘闪着光,在树上颤动着的树叶已经变成蔷薇色,一切都像在白天一样,清清楚楚。当燃烧的肉体的臭气在花园里弥漫起来时,奴隶们就在圆柱中间撒下特意准备好的没药和沉香。群众中随处可以听见喊叫声,是出于同情心呢,还是出于高兴和快乐,可就没人晓得了,喊叫随着火势时刻在增多。火焰拥抱着柱子,攀援到牺牲者的胸部,火热的气息把他们的头发烤得卷缩,为他们那幽暗的脸庞抛上一层黑纱,然后喷射得更高,像是为那下令发动这场火烧的强权,表扬他们的胜利和战功。
在这场表演的一开头,皇帝便乘着四匹白马拖着去竞技场的富丽双轮车,出现在人民中间。他装扮成战车手,穿着专供皇帝和宫廷人员穿戴的绿色骑士服。在他后面另有些战车随行,里面坐满锦衣华服的廷臣、元老院议员和僧侣,还有一些巴克斯的信徒,他们赤身裸体,戴着冠冕,手持酒壶,有一部分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发出疯狂的喊声。在他们的身边有一些扮成畜牧神和萨特尔的乐师,弹着琵琶和竖琴,吹着笛子和号角。在别的战车里,坐着罗马名门出身的贵妇和少女,也是喝得烂醉,半身赤裸。在驷马双轮车的四周,有些人挥舞着丝带结彩的酒神杖在奔跑着,另有些人在敲鼓,还有些人在撒花。这些五光十色的随从,在花园里最宽的大路上,在烟雾和人体火炬的行列中间,发出酒鬼的喊声,向前行进。皇帝让蒂杰里奴斯和基罗留在自己身边,他有意要拿基罗的害怕来寻开心,他亲自驾着马匹,眼观燃烧的肉体,耳听群众的喊声,放慢马步向前行。他站在高大的镶金战车上,四周有俯伏在他脚下的人山人海包围着,在灿烂的火光中,戴着竞技胜利者的金冠,他比廷臣和人群高出一个头,像是一个巨人。他那粗大的胳膊伸向前拉住缰绳,像是在给群众祝福。他的面孔上和半闭着的眼睛里,含着微笑,他像太阳又像神明在人群上照耀着——堂皇又有权势,可是样子也令人害怕。他不时停下来,仔细地看看某一个少女,看她的胸脯在火焰的燃烧下逐渐皱缩,或看看某一个幼儿,看他的面貌扭捩得不成人样。然后他又驾车向前走,身后随着一群疯狂骚动的跟班。有时他向人民哈腰鞠躬,然后又向后弯着身子,牵着金黄的缰绳,同蒂杰里奴斯交谈几句。最后他来到两条岔路当中的一座大喷水池边,从双轮车上迈步走下来,朝他的跟班点点头,混进人群中,人们乱喊并鼓掌来欢迎他。那些巴克斯信徒、山林女神、元老院议员、皇亲国戚、僧侣、畜牧神、萨特尔以及士兵们,立刻结成一个乱哄哄的圈子把他包围起来。而他呢,这一边有蒂杰里奴斯,那一边有基罗,绕着喷水池散步,池边正有几十个火炬在燃烧,他在每一个火炬前停一停,不是议论一下那些牺牲者,就是揶揄脸上现出极端恐惧之色的那个老希腊人。最后他在一个装潢着桃金M和常春藤编结起来的高杆前站住了。红火舌刚刚升到那个牺牲者的膝头,但是已经不能分辨他的面目了,因为燃烧的绿枝腾起了烟雾罩住他的脸。不过,过了一会儿,午夜的微风把烟吹散了,露出一个老人的头,斑白的长胡须飘在他的胸上。
一望见这个人,基罗立刻像一条受了伤的蛇扭成一团,从他嘴里发出一声喊叫,不像人声,倒更近似鸦噪。
“戈劳库斯!戈劳库斯!”
从燃烧的柱子上俯视着他的,正是医生戈劳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