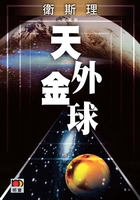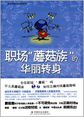“是的,”他发出低低的颤声说:“我几乎还没脱掉紫边白袍,就被送往亚细亚军团。那时我还不熟悉这个都市——不认识人生,不懂什么是爱情。我读过一点阿那克里翁和贺拉斯的诗,可是每逢我欣羡到不知所云又找不到适当言语来表达的时候,我不能像裴特洛纽斯那样信口念出诗歌。在童年,我进过穆索纽斯办的学校,他常常跟我说,以众神的愿望为愿望才能有幸福,因此幸福就在于我们的意志。不过,我想,还有另外一种幸福——种更伟大更可珍贵的幸福,并不全凭我们的意志,而只有爱情才能够给与。众神本身都在追求这种幸福,因此,黎吉亚呀,我至今还不曾有过爱情,因此我追随着他们的步迹,也在追求一个能给我幸福的人……”
他沉默了,好半天没有一点声响,只有激溅的水声,小奥鲁斯正向水里投石子吓唬鱼。停了一会儿,维尼裘斯又发出更温柔更低沉的声音说话了:
“你认识韦斯巴芗的儿子蒂屠斯吗?有人说,他还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深爱着贝莱尼姬,伤心到几乎要了他的命……黎吉亚呀,我也会那样爱的!财富、光荣、权势是缥渺的烟云!是空虚!阔人会到一个比他更阔的人,光荣的人会发现别人的光荣胜过他,强者会被另一个更强的人压服下去……可是,一个平凡的人,当他的怀抱里有另一个亲爱的胸怀在呼吸,或是当他在吻着爱人的嘴唇的时刻,就连皇帝本人,甚至是任何一种神,都不能比他体验到更大的快乐和更高的幸福……所以爱情可以使我们变成众神的平辈——黎吉亚呀!”
她心神不定惊惊惶惶地听着他讲话,同时又好像是谛听着希腊的笛子和竖琴的声音。她时时觉得维尼裘斯像是在唱着一种令人惊奋的歌曲,歌声慢慢地注入她的耳里,搅动着她的血液,使她的心陷于昏迷不醒,感到一种恐惧和难以形容的欢乐……她又像是觉得他所说的话都是她从前心里有过的,不过她不能对自己明白清楚地表达出来。她感觉到他把她心里至今沉睡着的东西激发起来了,而就在这时刻,那朦胧的梦变成了愈来愈明确、愈可喜、愈美丽的形象。
这时太阳早已越过了台伯河,在亚尼库鲁姆山上向下沉。一片红光落在静止的柏木棺上,空气里全都弥漫着红光。黎吉亚抬起她的蓝眼睛,仿佛从梦中醒来,望着维尼裘斯,而他俯着身子,眼里颤巍巍地流露出一种祈求的神情,于是在这夕阳西照之下,她突然觉得他像是比所有的人,比她在庙堂正殿里曾经见过的所有希腊和罗马的众神雕像,都更美丽了。他用手指轻轻握住她手腕的上部,问道:
“你可猜得出我对你说这些话的意思吗,黎吉亚?”
“不懂,”她悄悄地说,话声那么低,维尼裘斯几乎听不清。
可是他不相信她的话,更用力握住她的手往身前拖,要她靠近他的心脏——这颗心在这个美妙少女挑拨起来的热望的影响下,正像铁锤一般捶打着——而且要立刻对她倾吐出火热的语言。不料老奥鲁斯却从路边种着桃金孃的小路上朝他们走来,他边走边说:
“太阳快要下山啦;当心晚上着了凉,李比蒂娜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维尼裘斯答道:“我还没穿上大衣,并不觉得冷。”
“可是你瞧,太阳只剩下半个圆盘还照在山头上。”老军人接着说:“西西里气候温和,真是可爱,那里到黄昏时候,人们聚在广场上,合唱一曲欢送正在消逝的菲伯斯。”他忘记了刚才自己还警告他们要当心李比蒂娜,却并始谈起西西里,他在那里领有他心爱的产业和大片耕地。他还提起他多次想迁居西西里,安静地度过他的余生。一个人经过无数冬天,白了头,就会对于寒霜厌烦了。叶子还没从树上落下来,可爱的天空还在这个城市上空微笑着,可是当葡萄藤的叶子枯黄了,阿尔巴诺山上落了雪,众神在坎巴尼亚原野上吹起了刺骨的风,到那时——谁知道呢?——个人能不能把他的全家迁往安静的乡下住宅里去。
“普劳修斯,你是想离开罗马吗?”维尼裘斯猛然一惊,问道。
“我早就想这么做了,”奥鲁斯回答,“因为那里更安静也更安全。”
他又开始赞美他的果树园,他的牲畜,他那在绿荫下的房屋以及那长满麝香草和薄荷的山丘,花草中有成群嗡嗡的蜜蜂。维尼裘斯可不去注意这种牧歌的情调,只想着他或许会失掉了黎吉亚,便朝裴特洛纽斯那面观望,仿佛盼望他能够搭救自己。
这时裴特洛纽斯正坐在庞波尼雅身边,欣赏着日落的景色,欣赏着花园和站在鱼池旁的人们。他们的白色衣服,映在黑黝黝桃金德的背景上,从傍晚的余晖里闪出金色的光。天上,黄昏的光线开始染上紫色和堇色,像猫眼石那样变幻着色彩。苍穹变成了淡紫色,柏木的黑影比在白昼的光线里更加显目,傍晚的寂静笼罩着这些人、这些树和整个花园。
这种寂静叫裴特洛纽斯有所感触,尤其是处在这些人中使他感触更深。在庞波尼雅、老奥鲁斯、他们的儿子和黎吉亚的面容里,有一种东西,是他每天——或者宁可说是每夜——在包围着他的人们的面容里所不能见到的;生活在那里的全体人的生命里,流出了一种光明、一种安息、一种宁静。他有些惊讶地想到,他这个继续不断在追求着美与安逸的人,却还不曾知道这种美和安逸的存在。他无法把这种思想闷在心里,转过身来就对庞波尼雅说道:
“我心里这么想,你们的世界跟尼罗所统治的世界是有多么大的不同啊。”
她扬起细巧的面貌对着暮色,直截了当地说道:
“统治世界的不是尼罗,而是上帝。”
接着又是一阵静默。从饭厅近旁传来老将军、维尼裘斯、黎吉亚和小奥鲁斯走在小路上的脚步声,可是在他们来到之前,裴特洛纽斯又问了一句:
“那么你是信仰众神的吗,庞波尼雅?”
“我信仰上帝,他是惟一的、正义的,而且是全能的奥鲁斯·普劳修斯的妻子这样回答。
“她信仰那惟一的、全能的和正义的上帝。”当裴特洛纽斯又同维尼裘斯坐上了轿子时,他说:“如果说她的上帝是全能的,它就是掌管生与死的啦;如果说它是正义的,它叫人死是公正的。那么,为什么庞波尼雅要为尤丽雅戴孝呢?哀悼尤丽雅,也就是责备她的上帝了。我一定要把这番理论讲给我们的猴子、青铜胡子听一听,因为我相信讲到辩证法,我可以比得上苏格拉底。谈到女人,我承认,她们每一个都有三四个灵魂,可是没有一个具有推理的灵魂。让庞波尼雅找塞内加和河弩屠斯去思考他们的伟大的‘神’是什么的问题吧……让他们把色诺芬尼、巴门尼德、芝诺和柏拉图的亡魂一起都召来吧,那些亡魂住在其梅利的境界厌倦得像关在笼子里的梅花雀……我要找她和普劳修斯谈的可不是这件事。凭埃及的艾西斯的神圣肚子宣誓!如果我简单明了地对他们说明了我们的来意,我料想他们的道德论会像棒槌敲着铜盾牌那样喧嚷起来。所以我不敢讲!相信我的话,维尼裘斯,我不敢!孔雀是美丽的鸟,可是它们的叫声太刺耳。我怕怪声怪气的喊叫。不过我必须夸奖你的好眼力。一个真正‘玫瑰色手指的曙光女神’!你可知道,她还使我想起了什么吗?——春天!不是像我们意大利那样的春天,到处只有苹果树开着花,橄榄树是一片灰色,正像往常那么灰,而是像我在赫尔维霞曾经见过的春天,年轻,鲜艳,绿油油的……凭塞勒湼·维尼裘斯并不抬起头来,暂时沉默着,然后他激动得发出不连贯的声音开始说话了:“以前我渴望着她,现在我愈加渴望着她了。当我握着她手腕的时候,一团火把我包围住……我必须占有她。假如我是宙斯的话,我就要像他曾经变成了雨浇着达那厄?那样浇在她身上。我要吻她的唇直到她感到疼痛!我还要把她抱在怀里听她哀号。我要杀掉奥鲁斯和庞波尼雅,抱起她带她到我的家里。今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我要吩咐人用鞭子抽我的一个奴隶,听一听他的号哭。”
“安静些吧,”裴特洛纽斯说,“苏布拉区的木匠才会有你这样的欲望。”
“你讲什么,在我都不相干。我非占有她不可。我找你是想请你给我出个主意,如果你想不出办法来,我就得自己去打主意……奥鲁斯把黎吉亚当作女儿看待,那么我为什么要把她看做奴隶呢?既然再没有别的办法,就让她来装饰我的家门,让她给我的门涂上狼油,让她做我的老婆坐在我的炉边吧。”
“安静些吧,你这执政官的狂热的后代。我们捆绑蛮族拖在我们战车的后面,可不是为了讨他们的女儿当老婆的呀。可别太冒失。各种简单又正当的办法都仔细想想,让你自己和我用些时间考虑这件事。在我眼里,克丽索台米斯也像是朱庇特的女儿,但我仍然没有跟她结婚,这正像尼罗没有娶阿克台,尽管大家称她是阿塔鲁斯王的女儿。安静些吧……想想看,倘使她想离开奥鲁斯的家来找你,他是没有权力扣留她的,还要知道,冒出火焰的不是你一个人,爱神在她心里也点起火了……我看得出来,你必须相信我的话……忍耐吧。什么事情都会想出办法来的,可是今天我已经想得太多,我累了。我跟你讲定,明天我要把你恋爱的事考虑一下,除非说裴特洛纽斯不再是裴特洛纽斯,否则他就不会想不出办法来。”
他们又沉默了,过了好半天,维尼裘斯终于更安静地说:
“谢谢你,但愿命运女神多多保佑你。”
“沉住气。”
“你叫人把我们抬到哪里去?”
“去找克丽索台米斯……”
“你是幸福的,占有了你所爱的人。”
“我吗?你可知道,克丽索台米斯为什么还使我感到兴趣吗?没有别的,她和我的解放奴隶——那个弹琴的泰奥克雷斯——同欺骗我,而且以为我没有看出来。我曾经爱过她,而现在,她的撒谎和糊涂使我感到有趣。跟我一起到她那里去。倘使她开始跟你调情,用手指蘸葡萄酒在桌上写字,你要记住,我是不会吃醋的。”
于是他吩咐人把他们抬往克丽索台米斯那里去。
走在门道里,裴特洛纽斯把一只手搭在维尼裘斯肩膀上。
“等一下,我好像想出一个计划来啦。”
“但愿所有的神报答你?”
“是的!我相信,这个办法万无一失。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马库斯?”
“我留心听你讲……我的智慧女神……”
“几天以后,神圣的黎吉亚会到你的家里来享受婚姻女神的五谷啦。”
“你比皇帝更伟大!”维尼裘斯热烈地嚷起来。
裴特洛纽斯的确很信守他的诺言。
在找过克丽索台米斯之后的第二天,他整整睡了一天,可是到了傍晚,他吩咐人抬他到帕拉修姆宫,同尼罗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第三天,一个百人队长就率领十多个禁卫军的士兵出现在普劳修斯的家门前了。
这是一个不安定和恐怖的时代。这一类的使者常常就是死亡的通报人。所以当百人队长用锤子敲着奥鲁斯的家门而前庭总管通报士兵们已经进了门道的时候,全家顿时惊慌恐惧起来。一家人立刻把老将军团团围住,因为谁都不怀疑这场危险是与他特别有关的。庞波尼雅张开两臂抱住他的脖子,用尽气力抱住他,她那没有血色的嘴唇急速地动着,悄悄说着含混不清的话;黎吉亚,面色像麻布一样惨白,吻着他的手;小奥鲁斯牵着他的外衣;从走廊,从女仆和跟班住的下层小屋,从浴室,从矮房的拱门,都有成群的男女奴隶跑出来,到处可以听见叹气声:“天哪,天哪,大难临头啦!”女人们放声大哭;其中有几个甚至抓着她们的脸,或是用头巾包住她们的头。
只有多年来一直把死亡看做常事的老将军,保持着平静,他那短短的鹰脸变得那么冷峻,像是用石头雕刻出来的。过了一会儿,当他把这场哭叫压下去,他吩咐仆人们走开。他说“让我去吧,庞波尼雅。如果我的末日来到了,我们总还有彼此告别的时间。”
他轻轻推开她,于是她说:
“奥鲁斯呀,求上帝恩准你的命运也就是我的命运!”
然后她跪下来,开始使出那么一股劲儿来祈祷,只有关切着自己的爱人才能使出这股劲儿。
奥鲁斯向前庭走去,百人队长正在那里等着他。来人是老凯尤斯·哈斯塔,将军从前的部下,是不列颠战役中的战友。
“将军,向你致敬。”他说。“我带来了皇帝给你的命令和尚候,这里就是书面和印鉴,证明我是以皇帝的名义前来的。”
“我谢谢皇帝的致意,我服从皇帝的命令。”奥鲁斯答道。“欢迎你,哈斯塔,你说吧,你带来了什么命令。”
“奥鲁斯·普劳修斯哈斯塔宣旨道:“皇帝听说府上住着黎吉亚国王的女儿,那位国王,在神圣的克劳鸠斯时期,把她当作人质交到罗马人的手里,保证黎吉亚人绝不侵犯帝国的边疆。将军呀,神圣的尼罗向你致谢,因为那么多年来把她收养在府上,可是皇帝不愿意再多给你添麻烦,也考虑到那位人质的姑娘应该由皇帝本人和元老院来监护,所以命令你把她交给我。”
奥鲁斯是一个十足的旧式军人,为人又过于刚强,接到这个命令绝不允许自己露出懊悔之色,或说些废话和发牢骚。不过,在他的额头上突然现出了愤怒和痛苦的皱纹,往时看到他这样地蹙眉,不列颠的军团都要发抖的,即使在目前,哈斯塔脸上的恐惧也一目了然。可是现在,奥鲁斯·普劳修斯接到了这个命令却感到无能为力。他注视书面和印鉴一会儿,便扬起眼睛望着老百人队长,冷静地说:
“哈斯塔,你在前庭里待一会儿,等我把人质交给你。”
说了这番话,他走向住宅的另一头(名为“厄库斯”的内厅去,庞波尼雅、黎吉亚和小奥鲁斯正在那里慌张惊恐地等着他。
“绝不是叫谁去送死或充军到偏远的岛上去他说:“不过皇帝派来的人仍旧是祸事的使者。这件事是和你有关的,黎吉亚。”
“黎吉亚的事情?”庞波尼雅惊讶地叫起来。
“是的。”奥鲁斯说。
他转过身来面向那个姑娘说道:
“黎吉亚,你在我们家里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长大的,我和庞波尼雅爱你像我们亲生的女儿。可是你要知道,你并不是我们的女儿。你是你们族人送到罗马来的人质,你的监护权属于皇帝。现在皇帝要从我们家里把你领出去。”
将军冷静地说着话,可是带有一种奇怪的不平静的声调。黎吉亚静听着他谈话,眨着眼睛,仿佛不明了这是怎么一同事,庞波尼雅的脸蛋显得面无人色;奴隶们恐怖的面孔又一次从走廊通向内厅的门口露出来。
“皇帝的意旨是必须执行的。”奥鲁斯说。
“奥鲁斯!”庞波尼雅喊了一声,把姑娘抱在怀里,像是要保卫她,“她宁可死掉倒好——”
黎吉亚紧依着她的胸怀,一再叫着“母亲呀!”哭哭啼啼说不出别的话来。
奥鲁斯的面孔上又现出了愤怒和痛苦的表情。
“假如我是一个人活在世上他黯然说:“我不会把她活活地交出去,而今天我的亲属便要给‘解放者朱庇特’上供了……可是我没有权力杀掉你和我们的孩子,他还能活到更幸福的时代……今天我就去见皇帝,求他收回成命。他肯不肯听我的话,我可不知道。暂时再见吧,黎吉亚——你要记住,我和庞波尼雅永远在祝福你坐到我们的火炉边来的那一天。”
这样说着,他把手放在她头上,尽管他竭力保持冷静,而当黎吉亚把含泪的眼睛转过来望着他并抓住他的手用唇来吻的时候,他的声音里便充满了深厚的慈父般的悲哀。
“再见把,我的欢乐,我眼中的光明!”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