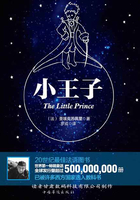狮子虽然饥饿,却不忙扑向那些牺牲者。竞技场上的红光使它们晕眩,它们像是昏迷了一般闭上眼睛,有几头懒散地伸屈身子,有几头张开了嘴巴打哈欠,真可以说它们是有意向观众展示它们可怕的牙齿。但是没多久,血腥气和成群躺在竞技场上的破烂的肉体,开始对它们起了作用。它们的举动立刻暴躁起来,鬃毛耸起,鼻孔发出闷重的声响在空中嗅着。有一头狮子猛然扑到一个面孔已经残缺的女人身上,用前掌踏着肉体,伸出粗糙的舌头舔着凝结的血;另一头逼近了一个基督徒,他怀里抱着缝上小鹿皮的孩子。
那幼儿抖动着身子哭喊,抽搐着抱紧父亲的脖子,而那个人呢,哪怕是片刻,也要延长孩子的生命,便想从脖子上把孩子拖开,好把他传递给那些跪在更远处的人们。但是哭声和这种动作惹恼了狮子。它突然发出短促而剌人肺腑的吼声,用脚掌一下子扑杀了那个幼儿,张开嘴咬住父亲的头,一眨眼的工夫就把头咬碎了。
一看见这种情形,所有其他的狮子也跟着朝基督徒们扑去。有些女人不禁怕得喊叫起来,但是观众发出来的喝彩把这些压下去,可是喝彩声不久也就停止了,因为想看下去的心愿占了优势,于是他们看到了胆战心惊的情景:许多头颅完全消失在张开的大嘴里,许多胸膛一下子就被扯开,许多心肺被扫光,许多骨骼在狮子的牙齿下粉碎了。有几头狮子抓住牺牲者的胯骨和肋条,疯狂地跳跃着跑过了竞技场,像是在找一个藏身的地方去吃掉它们;另有几头后腿立起,像角斗士一般彼此抓牢对打,圆剧场里充满了雷鸣般的吼声。人们从座位上站起来。有些人离开了位子,为了看得更清楚些从走道向下行,拼命地拥挤。那些激动的群众像是终于要把自己投入竞技场,跟狮子一起撕裂那些基督徒了。有时可以听到像是一阵鬼哭神号的闹声,有时是喝彩鼓掌,有时是摩罗西亚狗在咆哮怒吼,磨牙砺齿,狺狺狂吠,有时却只有一片呻吟声。
皇帝现在拿着绿水晶对着眼睛仔细观察。裴特洛纽斯脸上呈现出一种轻蔑和憎恶的表情。基罗已经被人从竞技场上抬出去了。可是从地道里又继续不断地赶出了新的牺牲者。
使徒彼得从圆剧场最高的一排在观望着他们。谁也没看到他,因为所有的人都把头朝着场子上,他站起身来,像从前他在柯奈留斯葡萄园里给那些想进监狱的人,祝福他们的杀身成仁和奔向永恒一样,现在他画着十字给那些正丧生在野兽牙齿下的人们,祝福他们的流血和悲痛,祝福他们那变成残缺不全的血块的死尸,和他们从血淋淋沙地上飞翔起来的灵魂。有些人扬起眼睛了望着他,他们的面上现出光彩,当他们望见头上的十字架,他们面露笑容。但是他的心裂开了。他说着:“主啊,照你的意愿去做吧,在真理的考验中,为了你的光荣,我的羔羊正在灭亡!你曾经命令我饲养他们,因此我把他们交给你,主啊,你引领他们,收留他们吧,治好他们的创伤,减轻他们的痛苦,把比他们在此地受到的苦恼更伟大的幸福赐给他们。”
他这样给他们祝福,一个接一个,一群接一群,仿佛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热爱着他们,如今正要直接把他们交到基督的手里。皇帝,也不知道是发了疯,还是有意要使这次表演成为罗马空前的一次,突然向市长悄悄说了几句话,市长离开悬楼,立刻走进地道。于是过了一会儿,当市民们看到铁栅门又开了,也不免吃了—惊。这一次放出了各种各类的野兽:有来自欧夫拉特的虎,努米底亚的豹、熊、狼,袋狼、胡狼等等。条纹的、黄色的、亚麻色的、深褐色的和花斑的毛皮,像一片动荡的海洋,布满了整个场子。场子里这时呈现混沌状态,除了野兽背脊的扭捩转动以外,人眼什么都不能分辨了。这场景观已经丧失了现实的形象,而仿佛是一次秘密的血祭,一场挣狞的噩梦,一个疯狂幻想的巨大万花筒。在咆哮、嗥叫、哀鸣声中,观众的席位上到处可以听到妇女们恐怖的和痉挛的笑声,她们的气力终于不能撑持了。人们害怕,面色变得黧黑,有许多人开始放声喊叫:“够啦!够啦!,’
然而把野兽放出来可比再把他们赶进去要容易得多。无论如何,皇帝总算想出一个扫清场子,并给人民一次新娱乐的办法。座席间所有的通道,出现努米底亚的黑人,插着羽毛,戴着耳环,手里持着弓箭。人们猜想到下文如何了,兴奋地喊叫着,欢迎那些弓弩手;努米底亚人走近栏杆,箭上弦,朝野兽群中射出去。这的确是一次新的壮举。他们柔韧的黑身体,向后仰,扯开有弹力的弓,一节按一箭朝外发。呼呼的弦音和飕飕的羽毛箭声,同野兽的咆哮和观众们发出的惊奇叫嚣搅成一团。狼、熊、豹以及还活着的人一个挨一个并排地倒下去。侧腹中箭的狮子,突地跳跃起来,忿怒中咧开嘴,想要咬那箭矢,露出可怕的形态,发狂般地旋转。有些野兽痛苦地呻吟着。一些小兽惊慌狼狈,胡乱地绕着场子奔跑,或是把头插进栏杆里,同时箭羽呼呼地呼呼地响下去,直到所有的生物在死亡的最后震颤中倒下。
几百个奴隶带着铲子、铁锹、笤帚、水推车、筐子,装置脏腑的筐子以及沙袋,成群地走到沙场去,圆剧场上现出了沸腾式的骚乱。不久,尸骸都收拾干净了,血迹也清除了,掘过的泥土填平了,新的沙土厚厚地撒在上面。然后,扮成丘比特的少年,把玫瑰、百合等各种花瓣撒在地上,香炉又添了新的香料。太阳已经西沉,天幕也撤除了。
人们惊讶,互相探听这一天还有什么新的奇观在等待着他们。
果然有那么一种谁也不会预想到的奇观在等待着他们。皇帝离开悬楼已经好半天了,他穿着紫袍,戴着金冠,突然出现在撒着花卉的场子上。十二个歌手拿着三角竖琴随在他身后;他拿着银琵琶,迈着庄严的步伐,向场中心前进。对观众鞠躬了好几次,眼睛朝天,像是在等待灵感。
然后他拨动琴弦开始歌唱了:
啊,光芒四射的莱托的儿子,
特奈多、吉真、克利梭的统治者,
这个神圣的伊里昂城,
一向都在你的手心里掌握。
你可忍心让它遭受希腊人的复仇,
并让那神圣不可侵犯的殿堂,
它不断焚香礼拜你的荣光,
竟被特洛伊人的污血弄脏!
啊,你威力无边的银弓射手,
老人把颤抖的手对你高举。
母亲从她们胸怀的深处,
含着泪大声向你呼吁,
乞求你对他们的子孙怜恤。
这些哀告可以把顽石感动,
而你对人民遭受的苦痛,
斯敏修斯呀,比顽石还更没感情!
这篇歌逐渐转变成充满悲伤和凄婉的哀歌。竞技场上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皇帝本人都受到了感染,继续唱道:
用你那七弦琴的天籁,
你能把悲泣和哀叹掩盖;
直到今天人们眼里含着泪,
像是一朵朵玫瑰的蓓蕾;
但是随着这篇歌曲的歌声,
谁能从尘埃和灰烬中复生,
谁曾度过大火的一天,避开灾难和灭亡……
——斯敏修斯呀,那时你在什么地方?
唱到这里,他的声音打颤,他的眼眶湿润了。贞女们的眼睑里显出了泪珠,人们默默地倾听着,然后他们发出继续不断好长的一阵如暴风雨般的喝彩。
同时从圆剧场的正门外面,传来了车辆的咯吱声,车上摆着基督徒、男男女女和幼儿的血淋淋的残骸,正要运往名为“荒坟”的土坑去。
这时使徒彼得双手抱住他那颤抖着的斑白头颅,在内心里喊道:
“主啊!主啊!你把世界的统治权交给什么人啦?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城市建立你的首都?”
太阳已经快要下山,像是溶化在傍晚的红光中。演技结束了,观众正离开圆剧场,通过名为“沃米托里亚”的走道向城里走去。只有皇亲国戚们不慌不忙地在等待人流向外涌。他们全体离开了座位,聚在悬楼旁边,皇帝为了听取喝彩声,重又出现在悬楼上。虽然在歌唱的收尾,观众并不吝啬地报以鼓掌喝彩,可是他还是不满意,他曾经期望有一阵近似疯狂的捧场。他耳里听着齐声赞美,也不认为满意,贞女们吻了他那“神圣的”手,而鲁布丽雅在吻手的时候,身子俯得那么低,以致她那淡红的头发都碰到了他的胸脯,而他还是不满意。尼罗心怀不满,倒并不隐藏这个事实。裴特洛纽斯闷声不响,这使他惊讶又感到不安。要是这人能说几句,并挑出歌里的词句恭维他一番,在这时将是他很大的一种安慰。最后他沉不住气了,向裴特洛纽斯招呼。当裴特洛纽斯一登上悬楼,他就说:炎谈吧。
可是裴特洛纽斯冷淡地答道:
“我不声不响,因为我找不到什么话说。这是陛下空前的成绩。”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可是人民又怎样呢?”
“陛下能够期望一些杂种贱民也会欣赏诗歌吗?”
“可是你也看见了吧,他们并没有如我所应得的对我表示感激。”
“因为陛下选定的时间不恰当z“这话怎么讲呢?”
“当人们脑子里充满了血腥气,他们就不能用心谛听了。”
尼罗紧握着拳头答道:
“啊,那些基督徒!他们烧了罗马,现在又伤了我。我将想出怎样的办法来惩治他们呢?”
裴特洛纽斯注意到自己走错了路,他的话产生了与他本意相反的效果,于是为了把皇帝的心神转移到别的方面,他俯下身来对他悄悄地说:
“陛卜的歌曲美得惊人,可是我只说一句评语:第四行的第三音阶,韵律上似乎还要修饰一下。”
尼罗羞得脸红了,仿佛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被人捉到一样,眼神发现出畏缩,也悄声地答道: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我晓得的!我要重写……但是再没有人注意到吧?真的吗?而你,凭众神宣誓,可别对任何人讲……如果……你珍惜你的生命的话……”
听了这话,裴特洛纽斯眉头一皱,仿佛不堪厌烦和疲劳而冒起火来,答道:
“圣上,倘使我欺骗了陛下,把我处死吧,可别拿死来吓唬我,因为众神知道得最清楚,我是否怕死呢?”
这么说着,他便直着眼睛瞧着皇帝的眼睛。停了一下,皇帝答道:
“别发火……你知道我多么喜爱你……”
“这个表示可不妙!”裴特洛纽斯暗中思忖。
“今天我本想请你参加一次宴会,”尼罗说,“可是我情愿关上房门,把那倒楣的一行第三音阶润饰一下。除了你,或许塞内加已经注意到了,大概塞恭杜斯·卡里那斯也看出了,但是我马上要把他们打发走。”
于是他召见了塞内加,表示要派他率领阿克拉层斯和塞恭杜斯·卡里那斯前往意大利和其他各省,从各城市、村镇以及著名教堂,简而言之,从凡是可以找到或榨取的地方,去搜罗金钱。可是塞内加明了派他去做的这件事,是掠夺、窃取圣物的强盗行为,立即拒绝了。
“圣上,我非到乡下去不可了,”他说,“到乡下去等死,因为我已年迈,神经上有了毛病。”
塞内加的伊贝里亚人的神经要比尼罗的神经更坚强,或许还没有什么毛病,但一般说来,他的健康情况不佳,因为新近他的头发发白,看起来像是一个人影子了。
因此尼罗瞧着他,心中暗想,这个人的寿终正寝无需等待多久了,然后答道:
“你既然不舒服,我不愿派你到路上去受苦,可是出于我对你的爱慕,我希望留你在我的近边,所以你用不着下乡,就关上门住在自己家里吧,无需出来走动。”
他又笑着说道:
“我要是只派阿克拉屠斯和卡里那斯两个人去,那等于把羊交给两头狼。我要派谁来领导他们呢?”
“圣上,派我去吧,”多米修斯·阿费尔说。
“不!我不希望惹得墨丘利对罗马发威,你会用你的下流行径玷污了这位神。我需要像塞内加那样的一个禁欲派,或是像我的那位新朋友——哲学家基罗。”
说着他向四面看了看,问道:
“基罗怎么样啦?”基罗在露天里已经清醒过来,为了听皇帝唱歌,又回到圆剧场,这时他钻出来说道:
“太阳和月亮大放光明的后代呀,我在这里。我刚才有点不舒服,可是陛下的歌曲又使我恢复过来。”
“我想派你去阿凯亚,”尼罗说。“那里的每一个庙堂有几文钱,你必定完全知道。”“宙斯呀,就这么办吧,众神会献出他们从来没有给过任何人那么多的贡品。”
“我这么想,可是我又不愿意,使你没机会参观这几次竞技。”
“巴尔呀!”基罗说。
皇亲国戚们见到皇帝脾气好转都高兴了,开始笑着大声说:
“圣上,别这么办!可别让这位勇敢的希腊人错过了参观这几场竞技的机会。”
“但是圣上呀,可别叫我再看见这些在卡皮托神殿乱卧乱吵的群鹅,他们的脑浆合在一起也装不满一个橡实果。”基罗争辩着。“阿波罗的长子呀,我正在写一篇希腊赞美歌献给陛下,我想到缪斯神殿里去住几天,求神赐给我一些灵感。”
“那可不行!”尼罗叫着。“你是想逃过下几次的竞技,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圣上,我向陛下宣誓,我确实正在写一篇赞美歌。”
“那么你在夜里写吧。向狄安娜去求灵感吧。她倒正好是阿波罗的姐妹。”
基罗的脑袋耷拉下来,火辣辣地朝着在场的人们看了一眼,人们又开始笑了。同时,皇帝转身向塞内乔和苏意留斯·涅鲁里奴斯说道:
“你们想象一下吧,指定在今天登场的基督徒,我们几乎还没弄掉一半。”
这时那个对于圆剧场的事情无所不知的老阿奎鲁斯·莱古卢斯想了一下,说道:
“人们‘不带武器又没本领’,就登场表演,时间一久就失去其趣味性了。”
“我要下令给他们武器。”尼罗答道。
可是那个迷信的维斯蒂奴斯从沉思默想中突然醒过来,发出神秘的声音问道:
“你们可曾注意到他们临死的时候像是看见了什么东西吗?他们面朝天,仿佛死得并不痛苦。我肯定他们是看见了什么……”
他说着举目观望圆剧场的上空,夜已经展开了它那点缀着繁星的天幕。可是别的人们哄笑着答话,并开玩笑地推测基督徒们在临死的时刻能够看见了什么。这时,皇帝朝那些持大把的奴隶做了一个手势,就离开了演技场,贞女、元老院议员、达官贵人、皇亲国戚,随后而行。
夜色清明又温暖。在演技场前面还聚集着好多人群,他们好奇地想一睹皇帝出发的情形。从某个角落不时响起喝彩声,但是马上就停止了。“停尸所”中发出吱吱呀呀声的板车正运走基督徒们血淋淋的残骸。
裴特洛纽斯和维尼裘斯一路上默不作声,快到他住宅的时候,裴特洛纽斯才问道:
“我同你讲的话,你考虑过吗?”
“考虑过维尼裘斯答说。
“你可相信这件事对我也成为最最重要的问题吗?不顾皇帝与蒂杰里奴斯,我一定要把她救出来。这像是一场我必须获胜的战斗,一种我希望赌赢的游戏,即使付出了我的脑袋……今天我更信心十足要进行我的计划。”
“愿基督报答你。”
“你瞧着吧。”
谈话之际,不知不觉到家了,他们走出轿子。这时有一个黑影朝他们走来,问道:
“这位可是维尼裘斯大人吗?”
“是的,”那保民官答道。“有什么事?”
“我是米丽阿姆的儿子拿扎留斯,我刚从监狱来,给你带来黎吉亚的消息。”
维尼裘斯把手搭在那年轻人的肩膀上,借着火把的光注视着他的眼睛,连说一句话的气力都没有了,可是拿扎留斯料到了他已到唇边又咽下去的问话,便答道:
“她还活着。乌尔苏斯派我来找你。大人,要告诉你,她害着热症始终在祈祷,一面叫着你的名字。”
维尼裘斯答道:
“赞美基督,他有力量把她送还给我。”
然后他领拿扎留斯走进书房。过了一会儿,裴特洛纽斯也走来听他们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