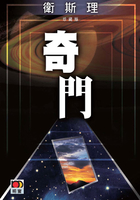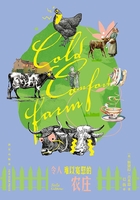事实上,在用过餐和照例的散步以后,他叫理发师为他梳妆,又叫奴隶们整理了他的长袍。一小时之后,他像神一样的美,吩咐人把他抬到帕拉修姆宫去。时间已经很迟了,
这一晚温暖又平静,月亮照得那么亮,轿子前领路的灯火手熄灭了他们的火把。大街上和废墟间,有些人群喝醉了酒,扎着常春藤和忍冬的花环,手里拿着从皇家花园折来的桃金孃和月桂的树枝,跌跌撞撞在路上走。大量的谷子和大场面的竞技的希望,使大家的心里全充满了快乐。有几处地方有人唱着颂扬“神圣的夜”和爱情的曲子;有几处地方,人们在月光下跳舞;有好几次奴隶们必须大声喊叫给“尊贵的裴特洛纽斯”的轿子让路,于是人群散开了,大声喊叫着,向他们所喜爱的人致敬。
这时他在想着维尼裘斯,奇怪为什么没有收到他的信息。他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自我主义者,不过由于他时而同塔尔苏斯的保罗,时而同维尼裘斯,厮混在一起,每天听他们谈论基督徒,尽管他自己是不知不觉的,但已经有些改变了。有一阵和风从他们身上向他吹来,在他的灵魂里撒下了新的种子。除了对个人以外,他开始对别人有了关切的心思,再则,他一向是爱着维尼裘斯的,因为在幼小的时候,他非常爱着自己的姊姊——维尼裘斯的母余,因此在目前当他参与了他的私事,他就那么有趣地注视着他们,仿佛在看一篇悲剧。
他确信维尼裘斯会赶在禁卫军的先头,已经同黎吉亚逃走了,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已经救了她。可是他愿意得到确实的消息,因为他预想他必须回答各种问题,而他顶好是先有个准备。
在蒂贝留斯宫前停下来,他下了轿子。过一会儿走进前庭,那里已经挤满了皇亲国戚。昨天的朋友们,虽然在惊奇他又受到邀请,却仍然避开他,而他从他们中间走过去,漂亮,潇洒,毫不在意又具有自信,仿佛他自己有权施惠予人的样子。有几个人看见他这样,暗自吃惊,怕他们对他表示冷淡为时太早了。
不过,皇帝装作没看见他,并没有对他的问候答礼,像是专心在同别人谈话。蒂杰里奴斯走向前来说道:
“晚安,‘风雅大师’。你仍然肯定不是基督徒放火烧了罗马吗?”
裴特洛纽斯耸耸肩膀,用手点着蒂杰里奴斯的肩胛,像是对待一个解放奴隶那样,答道:
“这事该怎么想,你跟我一样清楚。”
“我可不敢同你比聪明。”
“这在你还算有自知之明,因为当皇上从《特洛伊之歌》中给我们朗诵一篇新作的时候,你不但不像一只孔雀那么叫,反而要说出一些胡说八道的意见。”
蒂杰里奴斯咬着嘴唇。皇帝决定今晚读一篇新歌,他是不太高兴的,因为这样就开辟了一个他不能同裴特洛纽斯竞争的天地了。事实上,在朗诵的时候,尼罗照例不由自主地用眼瞧着裴特洛纽斯,仔细地观察,要从他的面孔上看出什么。而对方呢,有时扬着眉毛,有时表示赞同,有时探着头谛听,好像要肯定一下他听的是否正确。然后他或赞美,或批评,或提请修正或润饰某些诗句。尼罗自己感觉到,别人夸张地赞美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惟有裴特洛纽斯是为了诗歌而谈诗,所以如果他在赞美,便可以确认那些行诗是值得赞美的。于是一点一点地他开始同他讨论,同他争论,最后当裴特洛纽斯对于某一个辞语是否确切表示怀疑的时候,尼罗说道:
“到最后一篇,你可以懂得我为什么使用这个辞语。”
“啊!”裴特洛纽斯思忖。“那么我将活到等看最后的一篇啦。”
好多人听到他们的谈话,暗中就想:
“我要倒楣了!裴特洛纽斯尽有时间来得及争回宠幸,甚至会叫蒂杰里奴斯垮台。”这时人们又向他身边靠拢。但这一晚的收场可没有那么幸运,当裴特洛纽斯告别的时刻,皇帝眨着眼睛,面上露出既快乐又狠毒的神色,突然问道:
“为什么维尼裘斯没有来?”
倘使裴特洛纽斯能够肯定维尼裘斯和黎吉亚已经走出了城门,他便会答说:“他得到陛下的恩准结了婚到远方去了。”可是他看见尼罗一脸古怪的笑容,只得说:
“圣上,请帖送到时,他不在家。”
“告诉他,我很高兴见见他尼罗答道,“并且用我的名义跟他讲,不要错过基督徒们出场的那几次竞技会。”
这番话使裴特洛纽斯吃了一惊,在他看来,这番话直接指的是黎吉亚。坐上了轿子,他吩咐人要比早晨抬得还要快。不过,这件事可不容易。在蒂贝留斯宫门前,站立着密密麻麻喧闹不休的人群,像刚才一样喝得醉醺醺,虽然不唱歌和跳舞,但仿佛非常兴奋。从这方传来一片喊声,裴特洛纽斯不能马上听得清楚,而喊声沸腾不止,到最后简直变成狂野的怒吼:
“把基督徒交给獅子吃掉!”
宫廷大人们的轿子从吼叫的群众中间冲过去。从焚毁的街道深处,新的人群继续不断±也跑了来,他们听见了喊声就随着喊。人们交口传说,从午前已开始进行搜捕,捉到了无数纵火犯,不久,沿着新开辟的和旧有的街道,从帕拉修姆宫四周废墟中的小胡同里,从所有的小丘上和花园里,从罗马的四面八方,全响起了汹涌狂怒的吼声:
“把基督徒交给狮子吃掉!”
“这群畜生!”裴特洛纽斯不停轻蔑地说,“这种人民真配得上这种皇帝!”
于是他开始沉思,一个社会建立在强权之上,建立在连野蛮人都想象不出的残酷之上,建立在罪恶和疯狂的放荡之上,是不能够持久的。罗马是世界的主人,也是世界的一个脓疮。从它上边散发着尸身的恶臭气味。在它那腐朽的生命之上,死神的阴影正在下降。即使在皇亲国戚之间,也有人不只一次谈到这件事,可是裴特洛纽斯在以前从不曾把这个真理看得如现在这么清楚,罗马作为征服者而站立的这辆顶着月桂冠的战车,身后牵着一大群带锁链的各民族,正奔向悬崖。这个统治世界的城市生活,在他看来像是一种必须结束的疯狂舞会,一种秘密的狂欢节。现在他理解到只有基督徒才有一种新的人生基础,但是他相信,不久基督徒将不留丝毫痕迹了。那时又该怎样呢?
这一群愚蠢的人马将在尼罗的率领下继续前进,如果尼罗死掉了,便会找到同类的或许更坏的另一个人,因为这样的一种人民和这样的一种贵族断然不会找到一个更好的领导人。那时将有一场新的秘密狂欢节,而且更卑劣更猥亵。
但是这种狂欢是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的,狂欢过去之后,仅仅为了筋疲力尽,人们也得睡下来。
这么思索着,裴特洛纽斯感到疲惫不堪。只是为了旁观这种一成不变的世态,可值得生活下去吗?而且还是生活在不知明天如何的情况下!死神的化身并非不如睡仙的化身那么美,他的肩膀上也生着翅膀呀。
轿子到了家门口停下来,一个用心防守的看门人立刻把门打开了。
“维尼裘斯大人可曾回来?”裴特洛纽斯问道。
“刚刚回来,老爷奴隶回答。
“原来他没有救到她!”裴特洛纽斯暗自寻思。
接着他用掉了他的宽袍,跑进了前庭。维尼裘斯正坐在一张三脚凳上,双手抱着脑袋,俯下来几乎贴着膝头,听见脚步声,他扬起他那如木石一般的脸,只有眼睛里现出一股火热的亮光。
“你到得太迟了吗?”裴特洛纽斯问道。
“是的。他们在中午以前已经把她捉了去。”
接着是一阵沉默。
“你看见她了吗?”
“是的。”
“她在哪里?”
“在马梅蒂涅监狱里。”
裴特洛纽斯一惊,用一种审视的眼光注视着维尼裘斯。
对方是明了这个意思的。
“不!”他说,“没有把她投进屠里阿努,甚至没有投进中牢。我付钱给守卫,让她自己有一间屋子。乌尔苏斯站在门口保护她。”
“为什么乌尔苏斯不为她抵抗呢?”
“他们派了五十个禁卫军的十兵去。而黎努斯也不许他抵抗。”
“可是黎努斯呢?”
“黎努斯正病得要死,所以他们没有抓他。”
“你打算怎么办呢?”
“救她出来或者同她一起死掉。我也信仰基督。”
维尼裘斯谈话像是很平静,但声音里含有那样的一种绝望,裴特洛纽斯纯粹出于怜悯,心里直发抖。
“我了解你他说,“可是你想用什么办法来救她呢?”
“我给守卫很大一笔钱,第一别让她受到侮辱,第二别阻挡她逃跑。”
“什么时候才能逃走呢?”
“他们对我说,他们不能把她马上交给我,他们怕担责任。当监狱里装满了人众,当囚徒的番号弄乱了的时候,他们便把她交给我。然而那是最后一种手段了。首先要请你救她,也救我!你是皇帝的朋友。他亲自把她嫁给我的。你去找他谈谈,救救我吧!”
裴特洛纽斯并不答话,叫奴隶拿来两件黑色外衣和两把剑,然后转身面对着维尼裘斯。
“在路上我会告诉你的他说,“目前你穿上这件外衣,拿着这把剑,我们一同到监狱里去。到那里给守卫十万钱,只要他们肯立刻放出黎吉亚,便是给他们两倍多或五倍多也无妨。否则的话就要来不及了。”
“我们这就走。”维尼裘斯说。
片刻之后两个人已经走在街上。
“现在听我讲,”裴特洛纽斯说,“刚才我不愿意多耽误工夫。从今天起我已经失宠了。我自己的性命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因此我对皇帝再也不能发生什么影响。还不仅如此哩!我可以肯定,要是我请求什么,他一定会做出相反的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又为什么要劝你同黎吉亚逃走或抢救她呢?不管怎么说,你要是能够逃走了,皇帝的怒火会扑到我身上来。今天你要是有所请求,说不定他倒还肯做,我可不行。无论如何,你别再打这个算盘了。把她从监狱里救出来,逃走吧!你再没有别的出路。这个办法要是不成功,你还来得及采取别的手段。同时你要知道,把黎吉亚收监,不仅仅是为了她的信仰基督。波佩雅的愤怒在追踪着她和你。你还记得吗,你曾经得罪了皇娘,拒绝了她的爱情!她知道你所以拒绝她是为了黎吉亚,不过即使没有这回事,她在一见之下就已经恨上了她。从前她曾经打算害死黎吉亚,把她自己婴儿的死亡归罪于她的妖术。这件事情里是有波佩雅的魔掌!不然你怎么解说黎吉亚为什么第一个被送进监牢里呢?是谁指出了黎努斯的住家呢?我可以跟你讲,人们老早就追踪着她了!我知道我在绞痛你的心,打破了你最后的希望,可是我特意要这么说,是因为如果你不能在他们想到会出这个岔子以前就把她救出来,那么你们两个人都没命了。”
“是的!我懂得!”维尼裘斯呐呐地说。
时间已经很迟,街道空无人迹,可是有一个喝醉了酒的角斗士向他们走来,妨碍他们继续谈下去,那人摇摇摆摆撞到了裴特洛纽斯,伸出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一股酒气喷到他的脸上,扯着沙哑的嗓门大喊大叫:
“把基督徒交给狮子吃掉!”
“米尔米隆裴特洛纽斯安详地答道,“听从我的劝告,走你的路吧。”那醉汉又用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膀子:
“跟我一同喊,不然我就打断你的脖子;把基督徒交给狮子吃掉!”
但是裴特洛纽斯的神经已经受不了这些喊声了。自从他离开帕拉修姆宫,这些喊声像梦魇一样闷得喘不过气来,撕破了他的耳鼓,因此当他看见那个大汉的拳头在他头上挥起来的时候,他的耐性可就维持不住了。
“朋友他说,“你满嘴的酒臭,又挡住了我的去路。”
这么说着,他把从家里带来的那把短剑,朝那人的胸口戳进去,一直送到剑柄,然后,搭住维尼裘斯的胳膊,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他继续说道:
“皇帝今天说‘用我的名义跟维尼裘斯讲,不要错过了基督徒们出场的那几次竞技会。’你可懂得这话是什么意思吗?他们要拿你的痛苦做一次展览,这已经是决定的事情了。到现在还没把你我送进监牢里,大概就是为了这个。如果你不能立刻把她救出来,那可就……我不晓得了!也许阿克台会帮你的忙,可是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你在西西里的田产也许会引起蒂杰里奴斯的贪心。试试看吧!”
“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一切都送给他。”裴特洛纽斯答道。
从卡里内郊区到市公所并不远,因此没多久他们就到了。夜色开始发白,城堡的墙壁从阴影里清楚地现出来。
当他们转弯走向马梅蒂涅监狱的时候,裴特洛纽斯突然站住脚,说道:
“禁卫军!太迟了!”
事实上,监狱已被两列士兵包围了。清晨的曙光照在他们的头盔和枪尖上,发出一片银自的光泽。
维尼裘斯的脸色变得像大理石那么煞白。
“我们走过去。”他说。
过一会儿,他们就站在队伍前面了。裴特洛纽斯天生就有超人的记忆力,不仅认识军官们,也几乎认识所有的禁卫军士兵,他马上看见了一个熟识的步兵队队长,就向他打招呼。
“这是怎么回事,尼盖尔?”他问道。“你们接到命令来看守监狱吗?”
“是的,裴特洛纽斯大人。长官担心有人会来营救这些纵火犯。”
“有命令不许任何人进去吗?”维尼裘斯问道。
“没有,大人。有些相识的人可以进去看看囚徒,那样我们就可以捉到更多的基督徒了“那么放我进去吧维尼裘斯说。
于是他握着裴特洛纽斯的手,说道:
“你去见见阿克台,我要来探听她有怎样的回话……”
“来吧。”裴特洛纽斯回答。
正在这个时刻,地底下和厚墙里响起了歌声。赞美诗起初唱得很低又含混不清,后来却愈来愈响亮了。男女老幼的声音组成一片谐和的合唱。在黎明的静寂中,整个监牢开始发出竖琴似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并不带有忧伤和绝望。反之,从其中可以听见欢喜和胜利的声响。
士兵们惊讶地互望着。天空里现出了金黄和淡红的第一道曙光。
“把基督徒交给狮子吃掉”的喊声,在城市的每一区里不停地喧腾着。起初不仅谁都不怀疑他们是这场灾难的祸首,而且谁也不愿意怀疑,因为惩罚他们乃是市民们的一场精彩的娱乐。不过有一种看法传得很广,大家认为倘非众神庙愤怒了,这场灾难就不会酿成这样可怕的局面,因此官方下令在庙堂里供上“皮亚库拉”——即赎罪的牺牲。按照《希腊神谕集》的指示,元老院给伏尔甘、色列斯和普西芬尼布置了祭祀典礼和公众祷告。家庭主妇们给朱诺上供,她们成群结队到海边去取水,洒在这个女神的雕像上。已婚的妇女们给众神摆上宴席而且守夜。整个罗马清洗着罪恶,上供,乞求众神的宽恕。同时从废墟中开辟出宽大的新街道。各处又打起地基,要建造辉煌的家屋、宫殿和庙堂。但第一个要紧的事,便是以前所未闻的速度造起一个木制的巨大圆剧场,要基督徒到里边去送死。在蒂贝留斯宫的议事之后,立刻下令给各位执政官,要他们供应野兽。蒂杰里奴斯把意大利各城市的兽苑一扫而光,连较小的也不例外。在非洲,人们遵命组成庞大的猎人队伍,全体居民都被迫参加。从亚细亚运来象和虎,从尼罗河运来狼和熊,从爱尔兰运来凶猛的猎犬,从伊庇鲁斯运来摩罗西亚狗,从日耳曼运来巨大的野牛。由于囚徒人数的众多,这次竞技在场面的伟大上,将超过至今曾经见过的任何一次。皇帝希望在血海中淹没了大火的记忆,叫罗马痛快地喝个烂醉,谁也不曾作过比这次流血更伟大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