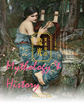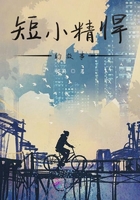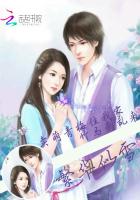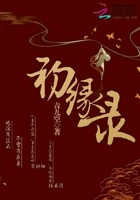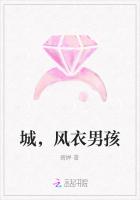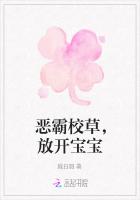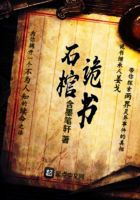全球:城市光影浮掠
料想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先从电影开始认识一座城市的吧。毕竟能够身体力行到达的机会,跟看一部电影比起来,还是要渺茫许多。也因此,我们总对那些影像化的城市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事实上,那些印象恰是从电影而来,或者更准确来说,是从那些导演而来。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得以走进城市,熟悉它,爱上它,记住它。
所以,我们看纽约,总先想起马丁·斯科塞斯或者伍迪·艾伦。前者的纽约越热闹越寂寞,充满遗世独立的绝望气息;后者的纽约却是浪漫琐碎的俗世生活,扯不开的情爱纠葛,讲不完的男女之事。两个纽约,哪一个才是真实?或许都是,亦或许哪个也不是。
斯科塞斯早期作品中所关注的大多是边缘小人物,而故事的舞台则是喧嚣的纽约。
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承载着多少遥不可及的“美国梦”,《出租车司机》中的特拉维斯便是怀揣梦想的其中之一。可惜,作为20世纪70年代浮华纽约城中最寂寞无助的小人物,这座偌大的城市竟容不下他卑微的灵魂。当他最后举起枪,对着镜子低吼时,镜头里所散发出的,是难以言状的孤独。
好在我们还能从伍迪·艾伦身上找电影《出租车司机》剧照到些许安慰。《怎样都行》是他离开纽约4年后的回归之作,尽管还是那么絮絮叨叨神经质,可是他们看到了一个自由宽容的纽约。爱上小女孩的老教授,放弃优越的上层生活,跑到廉价小旅馆里,开始另类的打工生涯。为了结婚,拜见小女友的父母,还闹出了一系列笑话。纽约的开放多元,从伍迪·艾伦的镜头里一览无余。这样精彩有趣的城市,想必是人见人爱的吧。
好莱坞的强大,让美国的许多城市得以“声名远播”。比如《疤面煞星》里的迈阿密,是一座罪与魅交织的涅盘之城;《逃离赌城》里的拉斯维加斯,传奇每天都在上演;《西雅图不眠夜》里的西雅图,含情脉脉,令人流连;还有《天使之城》里的洛杉矶,空气中洒满爱的光芒。
欧洲的城市,同样各有特色。有的温情,有的风尘,有的性感,有的冷峻。城市和人一样,有着不一样的特质,在镜头里也呈现出迥异的气息。
我们因为《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爱上了那个风情万种的地中海小岛。
梦想在那里见到妖娆的玛莲娜,就好像北京城的马小军迷恋米兰一样,每个男孩心里都有一个女神。
当然,关于巴黎的影像就更多了,其中最难忘的当属《天使爱美丽》。后来每次去巴黎,看到街头的快拍机都会想起艾米丽和她的小男友传奇的邂逅。就像到伦敦一定会去诺丁山的小书店一样,看看裘德·洛是否还在店里,等待他的灰姑娘。
马德里则因为阿莫多瓦,而变得活色生香。从《对她说》到《关于我的母亲》,再到《回归》,表面上阿莫多瓦的作品总看起来色彩艳丽、醒目璀璨;仔细看,却有着最深沉的黑暗底色。那些或不羁或罪恶的边缘人物,恰是阿莫多瓦对于马德里的独特见解。或许,在他眼里,马德里就是一座充满诱惑与挣扎的欲望之城。
或许很多人和我一样并不清楚马其顿在哪里,更不知道马其顿的首都名叫斯科普里。但是因为一部《暴雨将至》,我们认识了这个国家和这座城。知道这里的人们放牧而生,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安宁祥和。
《柏林苍穹下》让柏林变成一座连天使都甘愿坠落的爱之城;《布拉格之恋》则让布拉格的空气里注满激情与感伤。《罗马假日》的浪漫童话,让罗马成为多少灰姑娘的朝圣之地;《夏日时光》的威尼斯是属于凯瑟琳·赫本的难忘记忆。哦,差点儿忘了爱玩的伍迪·艾伦,还带来了一部巴塞罗那行走指南《午夜巴塞罗那》,让我们认识了一个热情奔放、充满冒险的魅力之城。
亚洲的城市,也在光影中浮现。小津安二郎的东京,有着久远的静默与孤寂;岩井俊二的小樽,则寄托着思念与回忆;《青木瓜之味》拍出了西贡的味道;《初恋红豆冰》吹来的是吉隆坡的清新海风;还有《外出》的首尔,让人陷入迷茫的纠结……不知道是城市成全了电影,还是电影成就了城市。我们只知道,时代在变,城市在变,好在还有电影,留住刹那芳华,让城市永存。
上海:光阴的玫瑰
上海,在近代中国被称为“十里洋场”。自鸦片战争以来,租界、外国人、股票、高楼这些新事物造就了它的繁华,也造就了它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声名。一百多年来,无论是外滩璀璨的灯火,还是南京路熙攘的人群,无不在电影中被凝固成永恒的画面。
无数影像记录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迁。
很奇怪,电影里的上海,总是有两个模样:一个是记忆搭建的旧日幻梦,一个则是现实构筑的摩登都市。前者是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是侯孝贤的《海上花》、是关锦鹏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徐克的《上海之夜》,也是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李安的《色·戒》。弥漫着似是而非的暧昧,归根到底却是记忆中的光影交错。
后者尽管真实,却很寂寞。比如许鞍华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彭小莲的《美丽上海》、娄烨的《苏州河》、叶伟信的《大城小事》、张一白的《夜·上海》,以及施润玖的《美丽新世界》。这城市摩登时尚,光鲜体面,只是生活其间的每个人却是冷暖自知,各有悲喜。
这两个上海,同生共栖,交织缠绕,共同分享着这座城市的感性与秘密。也因此,幻化为镜头里的摇曳多姿、气象万千,孕育出一朵光阴的玫瑰。
A面上海:海上旧梦
代表作品:《花样年华》、《红玫瑰与白玫瑰》等
华语影坛有两位导演,公认是拍上海最对味的人。一个王家卫,一个关锦鹏。尽管两人都是香港人,骨子里却都留存着难以磨灭的上海印迹。这印迹如酒般沉淀发酵,不是文字的书写,亦不是语言的告白,而是在镜头里弥漫着上海的气息:那种老派的精致,和只属于上海的骄傲与落寞,全都浸润在他们的影像中。《花样年华》与《红玫瑰与白玫瑰》算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部作品。
其实说到底,《花样年华》不过是王家卫制造的一场上海梦。他拍的是他想象中的上海,抑或更准确来说,是他记忆中的上海。也因此,他的故事里,上海总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暧昧与距离。仿佛是上海,可仔细一想,却又不尽然。
夜色中,张曼玉在弄堂口的馄饨摊留下的一抹抹婀娜身姿,介于梦幻与现实间,看得人如痴如醉。想起儿时,外婆说,正经人家的女子一天要换好几身衣裳:有居家的,有见客的,有出门的,有晚宴的。什么场合,什么服饰,向来是分得清清楚楚。
哪像现在,顶多出门一套,回家一套,活得够潦草。
如此,苏丽珍的曼妙,既可以说是她为了见周慕云的精心装扮,又可理解为是彼时上海女子的完美展现。这种对于自身容貌的关注,以及日积月累之下所散发出的强大气场,在潘迪华身上则体现得愈加到位。即便只是门缝中的一个侧影,或者走道中的匆忙一瞥,上海女人的妩媚与凌厉,也足以令人过目难忘。
不过到了关锦鹏的镜头里,上海不再是瑰丽暧昧的春梦一场,而变成了五味杂陈的世俗生活。《红玫瑰与白玫瑰》,在张爱玲笔下是两败俱伤的爱情悲剧;到了关锦鹏手里,倒消解掉不少的你死我活,且留下苟延残喘的生活本相。
赵文暄演的振保,坐在电车里心事重重。电车叮叮当当,好似生命的警钟,敲打着振保的灵魂。电影《花样年华》剧照到底是要娇艳的红玫瑰,还是要皎洁的白玫瑰?不知这红玫瑰何时会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那白玫瑰又几时会变成衣服上的一粒饭黏子?谁人能预料?开过电车的清冷街道,有着旋转阶梯的欧式公寓,还有穿风衣戴帽子的寻常男子,和他们的女人,让这上海弥漫着冷峻凄美的气质,到头来,还是一场醒不来的梦。
是怀旧也好,感伤也罢,王家卫与关锦鹏们所眷恋的上海,终究是他们记忆中的旧日时光。暧昧阴柔、知性优雅,这样的电影带给我们诗一般的观影体验,同时也赋予了上海这座城市梦境般的奇幻色彩。
B面上海:摩登都市
代表作品:《夜·上海》、《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等
上海的时尚摩登,向来走在全国前列。这摩登不单是指城市里的高楼林立,更在于高楼间分布着的石库门、老洋房、梧桐树和数不清的咖啡馆、服装店、电影院和小书店。有个词总用来形容上海和上海式的生活方式-小资,对比中国其他地方而言,愈加凸显出上海的独特气质与别样韵味。
于是,电影里的上海,便有了自成一派的现实境遇。比如张一白的《夜·上海》,让赵薇演一个出租车司机,在工作中遇到本木雅宏所演的日本设计师。这样的跨国奇缘,并没有受到太多的现实干扰。我们看到的是夜色中一座座如彩虹般光影交织的高架桥,和窗外灯火璀璨的不夜城。
外滩的异国风情,与老洋房里的寻常日子,被和谐统一在一起。最洋派的西方建筑里,生活着最东方的家长里短。有爱情,有亲情,有迷茫感伤,亦有贴心温暖。
张一白不愧是拍城市题材的高手,他把上海的夜色拍得璀璨明亮,却也百转千回。
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剧照同样深谙上海精髓的,还有一个香港导演许鞍华。尽管《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单就故事来说,留有不少遗憾。
但在细节上,看得出来是花了心思,费了工夫的。尤其是让斯琴高娃和周润发来演两个生活在上海的普通人,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个挑战。
姨妈生活在老式公寓里,每天去菜场买菜,去公园唱戏。穿得干净整洁,待人礼貌客气。身上有一种老派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却偏偏活得卑微落寞。这种精神层面的唯我独尊,与物质世界的巨大落差,恰恰是一代上海人的真实写照。也因此,这座看起来体面光鲜的城市,成了他们最进退不得的现实牢笼。
或许《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结局太过悲观,姨妈最终离开了上海,也意味着她的绝望与放弃。而事实上更多人则选择留下,继续在这座城市打拼。比如《美丽上海》
里的王祖贤一家,他们又聚集在一起,重温失落的亲情;《大城小事》里的黎明和王菲,在金茂顶楼相拥,共看城市夜空的烟花绽放;还有《美丽新世界》里的姜武和陶虹,找到真爱,重启人生。
上海的城市变迁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总伴随着对于契约精神的尊重与公共秩序的遵从。这也使生活在此的人,某种程度上活得更公平、更独立。于是影像中的上海,也得以呈现出复杂多元、开放自由的景象。所谓海纳百川,包容万象,从容优雅,是也。
北京:皇城乐与怒
相比上海的阴柔妩媚,北京则显得大气许多,像一个家底丰厚的阳光少年,尽管老辈的皇族气息犹盛,他自己倒活得够轻松洒脱。就是有一种前尘往事俱往矣,且看今朝谁风流的气度。也因此,在电影里,老北京总是带着传奇色彩,好像每个人都藏了很多秘密,在四合院的空间中,看似开放,却又封闭地自顾自活着。比如《城南旧事》,比如《蓝风筝》,比如《洗澡》。时代的烙印镌刻在最卑微的个体身上,即便有一颗想要挣脱的心,却也无能为力。
不过电影里的北京,最鲜活的模样,还是属于马小军们的青春记忆。《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代人的独立宣言;《十七岁的单车》承载了无数年轻人在北京的漂泊与渴望;还有《独自等待》式的新旧碰撞,在最中国的胡同里,开一家最中国的古玩店,生活着最全球化的年轻人;而《开往春天的地铁》里则装满了“杜拉拉”的人生梦想,哪里还找得到四合院和皇城根?
北京,就是这么一座具有摇滚气质的中国古城。有着悠电影《城南旧事》海报久的历史,开放的胸怀,多元的选择,和刚烈的气质。北京没什么似是而非,爱就是爱,恨就是恨,落落大方,铿锵有力。
皇城记忆
代表作:《城南旧事》、《蓝风筝》、《洗澡》等
不知道为什么,关于老北京的影像,总带着淡淡的忧伤和强烈的宿命感。不管每个人的境遇如何不同,到头来,却都抵不过时代的洪流,灰飞烟灭。《城南旧事》里的小姑娘,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借着她童真的双眼,看到20世纪20年代老北京胡同的社会风貌。胡同里的大人们总是心事重重:秀贞好不容易与女儿相认,却还是死在了寻夫的路上;供弟弟上学的年轻人,行窃被捕;奶妈的儿子淹死了,女儿被卖掉了,她离开丈夫偷跑出来做工。胡同不长,人生很长;幸福不多,苦难却很多。
到了《蓝风筝》,这种宿命感更甚。铁头的三个“父亲”都在同一个四合院里出现,却又相继离开。剩下逐渐长大的铁头和他日益老去的母亲。这四合院里的一砖一瓦都不曾改变,只是物是人非,徒留一声叹息。
好在《洗澡》,让我们看到了些许欢笑。父亲和两个儿子,构成了院子里的某种平衡。
父亲坚守着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也坚守着一份老派的传统。大儿子急急要抛弃一切,飞速狂奔。憨厚耿直的小儿子,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他只在熟悉的环境中过着习惯的每一天。老北京、四合院、澡堂子与街头熙攘的人群、拔地而起的高楼和日新月异的新城格格不入。新旧文化的冲击,带来的阵痛,是如此清晰。
少年凶猛
代表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十七岁的单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