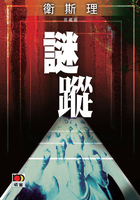我们往回走到那条通往公路的小道,我指给两个女孩子看,“到那边去吧,”我说,“会碰到人的。”她们望着我。我掏出皮夹子,给了她们每人十里拉。“到那边去吧,”我指着说,“朋友!亲戚!”她们完全听不懂,只是紧紧地捏着钞票,开始往路的另一头走去。她们不时地回过头来,像是怕我把钱要回去似的。我看着她们走在了那条小道上,把大围巾裹得紧紧的,胆怯地扭过头来望望我们。三位司机放声大笑起来。
“如果我也朝那方向走,你给我多少钱,中尉?”博内罗问。
“要是遇上了敌人,她们还是混在人群里好一点。”我说。
“你给我两百里拉,我就朝着奥地利一直走回去。”博内罗说。
“他们会把你的钱抢走的。”皮安尼说。
“说不定战争巳经结束了。”艾莫说。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路。太阳想冲出云层来。路旁边有桑树,从桑树间还能看见陷在田野里的那两部车。皮安尼也转过头去望望。
“看来只能修出条路才能够把车子拖出来了。”他说。
“基督啊,要是我们能有辆自行车就好了。”博内罗说。
“在美国有人骑自行车吗?”艾莫问。
“以前有过。”
“要是在这儿,能有辆自行车可真是了不起,”艾莫说,“这东西太好了。”
“基督啊,但愿我们有自行车,”博尼罗说,“就不用走路了。”
“那是枪声吗?”我问。我隐约地听见远处的射击声。
“这不好说。”艾莫说。他听着。
“大概是吧。”我说。
“我们也许会先看到骑兵吧。”皮安尼说。
“他们不见得有骑兵队吧。”
“基督保佑,但愿没有,”博内罗说,“千万别让天杀的骑兵把我一枪刺死。”
“你倒是打死了那名上士,中尉。”皮安尼说。我们走得很快。
“是我打死他的,”博内罗说,“这次战争中我还没杀过人,我一辈子就想杀个上士。”
“你是趁他动弹不了的时候,打死他的,”皮安尼说,“你杀他的时候,人家可并不是在飞快地跑。”
“那无所谓,这是件我永远都忘不了的快事。我杀了一个狗上士。”“你将来忏悔时要怎么说呢?”艾莫问。
“我会说:‘祝福我,神父,我杀了一个上士。”’他们都笑起来。“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皮安尼说,“从来不去教堂的。”
“皮安尼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博内罗说。
“你们真是无政府主义者吗?”我问。
“不是,中尉。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是伊摩拉人。”
“你没去过那地方吗?”
“没有。”
“基督可以证明,那才是个好地方哪,中尉。战争结束以后你来吧,我给你看一些好东西。”
“你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吗?”
“人人都是。”
“那座城不错吧?”
“好极了,我相信你从来没见过那么美丽的城市。”
“你们怎么会成为社会主义者的?”
“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人人都是,而且永远都是。”
“你来吧,中尉。我们也使你成为社会主义者。”
道路在前头向左转弯,那儿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个苹果园,外面围着一堵石墙。随着道路爬向山,他们就不再说话了。大家一起加快了步伐赶路。
后来,我们走上一条沿着河的小路,一直延伸到桥边,有一长列被遗弃的卡车和运货马车,一个人影也没有。河水高涨,桥巳经被拦腰炸断;桥上的石拱掉在河里,上面就流淌着褐色的河水。我们沿着河岸走,想找个可以渡河的地点。我知道前头有座铁路桥,可以渡到河对岸。河边小径潮湿而且泥泞。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军队,只有遗弃下来的卡车和军用品。河岸上除了淋湿的树枝和泥泞的土地外,既没有其他东西也没有人。我们走到河岸边,终于看到了那座铁路桥。
“一座多么美丽的桥啊。”艾莫说。那是一座普通的长铁桥,横跨在一道往往是干涸的河床上。
“趁着还没被炸断,我们赶紧过去吧。”我说。
“不会有人来炸它的,”皮安尼说,“他们都走光了。”
“说不定桥上还有地雷呢,”博内罗说,“你先走,中尉。”
“你听这无政府主义者讲出这种话来,”艾莫说,“叫他自己先走过去。”
“还是我先走吧,”我说,“他们埋的地雷不会就只为炸一个人的。”
“你瞧,”皮安尼说,“这才叫头脑,你怎么就没脑子呢,无政府主义者?”
“我要是有脑子就不会在这儿了。”博内罗说。
“这话很有道理,中尉。”艾莫说。
“有道理。”我跟着说。我们现在离桥巳经很近了。天上又堆满了乌云,下着小雨。那桥看起来又长又坚固,我们爬了上去。
“你们每个人都分开走。”我说着,开始走上桥去。我细心察看枕木和铁轨,看是否有拉发线或者埋有炸药的痕迹,但并没发现。透过枕木的空隙,我看到下面流淌着又混浊又湍急的河水。前面,望向那一片被淋湿的乡野,我看见了在雨中的乌迪内。过了桥,我回头望望,河上游还有一道桥。正当我望着那桥的时候,有一辆黄泥色的小汽车从上面开了过去。那座桥的两边很高,车一上桥,车身就被遮住了。但我还能看见司机和旁边坐着的那人,还有后座上的两个人,能看见四个人的头,他们全戴着德军钢盔。随后车子下了桥,又被路两边的树和遗弃的车辆遮住了。我向正在过桥的艾莫和其他人挥挥手,叫他们过来。我趴下去,蹲在铁路的路堤边。艾莫也下来了和我躲在一起。
“你看见那辆车了吗?”我问。
“没有,我们一直都在看着你。”
“有一辆德国军官坐着的车从上游那座桥开了过去。”
“军官的汽车?”
“是的。”
“圣母玛利亚啊。”
大家都巳经过来了,我们一起蹲在了路堤后边的烂泥里,望着铁轨那一边的桥、那一排树、明沟和那条路。
“照你看,我们是不是被切断了,中尉?”
“我不知道,我只是看见了一部德国军官的车子从那条路上开过。”
“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中尉?你脑子里不会有什么奇异的感觉吧?”
“别瞎说了,博内罗。”
“喝点酒吧?”皮安尼说,“要是真的被切断了,那就索性喝口酒吧。”他解下水壶来,打开壶盖。
“看!看!”艾莫说,指着路上。我们看见石桥顶上晃动着德国兵的钢盔。那些钢盔朝前倾斜着,平稳地向前移,就像是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操纵着。他们下了桥,我们才看见他们原来是自行车部队。我看见走在最前面那两个人的脸,又红润又健康。他们把钢盔遮得低低的,挡住前额和脸庞的两边。他们把卡宾枪挂在自行车车架上。每个人的束身皮带上倒挂着手榴弹,弹柄朝下。他们的帽盔和灰色制服都被雨水打湿了,仍旧从容地骑着车子,张望着前头和两边。起先两人一排一一接着四人一排,然后又变成两人一排,接着差不多十二个人;接着又是十二个人一一最后是单独一人。他们不说话,但就是说话我们也听不见,因为河水流动的声音太大了,他们消失在路上了。
“圣母玛利亚啊”艾莫说。
“是德国兵,”皮安尼说,“不是奥国佬。”
“该死,这整个局面都荒唐可笑。他们把下边那座小桥炸掉了,大路上这座桥却保留了下来。人都躲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们完全不想拦阻敌人吗?”
“你倒来对我们说说看,中尉,”博内罗说。于是我不再说话了。这本不干我的事,我的职责只是把三部救护车送到波达诺涅,但显然巳经无法完成,现在我只要人到达波达诺涅就行了,也许我连乌迪内都走不到。到不了了,真见鬼!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可别中了枪子儿或者被虏了过去。
“你不是打开了一个水壶吗?”我问皮安尼。他递给我,我喝了一大口酒。“我们还是动身吧,”我说,“不过也不用太着急,大家想吃点东西吗?”
“这不是可以多待的地方。”博内罗说。
“你说的对,我们走吧。”
“我们就在这地下走吧,免得被人家发现了。”
我们沿着铁路轨道走。两边伸展着湿漉漉的平原。平原的前头就是乌迪内的那座小山。山上有座城堡,人家的屋顶就在城堡下面,一户挨着一户。我们从这里能看见钟楼和钟塔。田野上还有许多桑树。我看见前头有个地方,路轨被拆掉了,连枕木都被挖了出来,丢在路堤下。
“趴下!趴下!”艾莫说。我们扑倒在路堤边。路上又有一队自行车走过。我偷偷地从堤顶朝他们望过去。
“他们看见了我们,但是却没有停下来。”艾莫说。
“如果是在上面走,就一定会被打死的,中尉。”博内罗说。
“他们要的不是我们,”我说,“他们另有目标,倘若我们被突然撞见就更危险了。”
“我情愿在这人家看不见的地方走。”博内罗说。
“好吧,我们就继续在轨道上走。”
“你觉得我们能逃出去吗?”艾莫问。
“当然啦,敌军还并不算多,我们可以趁着天黑溜过去。”
“坐车的那些军官是干嘛的?”
“天晓得。”我说。我们顺着铁轨继续走着。博内罗走在路堤的烂泥里,实在是走累了,也爬上来跟我们一起走。铁道延伸到南边,巳与公路岔开,我们再也看不到公路上的情况了。有一条运河,上边残留着被炸毁的断桥,我们凭着桥墩的残留部分爬了过去。我们听见了前面不远处的枪声。
过了运河,我们又走在了铁轨上。铁道穿过低洼的田野,一直通向城里。我们看见前面有另外一段火车线。北面是那条我们看见开过自行车队的公路;南面是一条小支路,横亘在田野上,两边有密密的树木。我认为还是应该抄近路朝南走,绕过城,再横过乡野朝坎波福米奥走,走上通塔利亚门托河的大路。我们走乌迪内城后面的那些岔道小路,可以避开撤退的总队伍。我知道有许多小路横贯平原。于是我开始爬下路堤。
“来吧。”我说。我们要走那条支路,绕到城的南边去。这时大家都爬下了路堤。突然有人从支路那边嗖的朝我们开了一枪,子弹打进路堤的泥壁。
“退回去。”我喊道。我们奋力地向路堤上爬,我的脚在泥土里打滑,司机们在我的前头,我尽快爬上路堤。又有两枪从密密的矮树丛中射了出来,艾莫正在跨过铁轨,身子一晃,绊了一下,脸朝下倒了下去。我们把他拖到另外一边路堤上,“他应该把头抬起来。”我说。皮安尼把他转过来。他躺在一片泥泞里,双脚朝下,断断续续地吐出鲜血。在雨中,我们三人蹲在他身边。他的后脖颈下面中了一枪,子弹从他的左眼窜了出来。我正设法堵住这两个窟窿时,他死了。皮安尼放下他的头,拿块急救纱布擦擦他的脸,也只能这样了。
“那帮狗崽子。”他说。
“他们不是德国兵,”我说,“那边不可能有德国兵。”
“意大利人。”皮安尼说。他把这个名词当作一种表性形容词。博内罗一声不响。他就坐在艾莫身旁,可是并不望着他。艾莫的军帽巳滚到路堤下面去了,皮安尼现在把它捡来遮住艾莫的脸。他拿出他的水壶来。
“喝口酒吧?”皮安尼把水壶递给博内罗。
“不。”博内罗说。他转身对我说:“如果我们一直在铁轨上走,随时都有这个危险。”
“不,”我说,“人家开枪,是看到我们想要穿过田野。”
博内罗摇摇头。“艾莫死了,”他说,“下一个会是谁呢,中尉?我们现在要往哪里走?”
“是意大利人开的枪,”我说,“不是德国人。”
“照我看,如果是德国人,一定会把我们都打死的。”博内罗说。“现在意军给我们带来的危险比德国人还要大,”我说,“掩护部队对什么东西都害怕。德国部队自有其目的,不会多管我们。”
“你说得头头是道,中尉。”博内罗说。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皮安尼问。
“最好先找个地方躲躲,挨到天黑再说。只要我们走得到南边就没事了。”
“他们为了要证明第一次并没有打错,一定会再向我们开枪的,”博内罗说,“我们都会被打死的,我才不要冒险呢!”
“我们找个离乌迪内最近的地方躲躲,等天黑再摸过去。”
“那就赶紧走吧。”博内罗说。我们从泥堤的北边下去。我回头望望,艾莫躺在泥土里,显得身子很小,两条胳臂贴在两侧,裹着绑腿布的双腿和泥污的靴子连在一起,军帽盖在脸上。这样子真像是尸首了。天在下雨。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他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了。我的口袋里装着他的证件,我得写信通知他家属。
田野的前头有一幢农舍,周围栽着树,屋子边上还搭着一些农家小建筑物。二楼用圆柱子支出一个阳台。
“我们还是一个个分开些走吧,”我说,“我先走。”我朝农舍走去。田野里有一条小径。从田野走过去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从农舍附近的树木间,或者就从农舍里开枪打我们。农舍离我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清晰。二楼的阳台和仓房连在一起,有些干草从柱子间突出来。院子是用石块铺砌的,所有的树木都在滴着雨水。有一辆空的双轮大车停在院子里,车把在雨中高高地翘起。我从院子里穿过去,停在了阳台下面。屋门开着,我便走了进去。博内罗和皮安尼也跟着我进去。屋里很暗。我绕到了后面的厨房,一个敞开的炉子里还燃有余火,虽然上面吊着几个锅子,可都是空的。我找遍了,也没发现一点儿吃的。
“我们得去仓房里躲躲,”我说,你再去找找看有没有能吃的东西,皮安尼,找到就拿上来。”
“我也一起去吧。”博内罗说。
“好吧,”我说,“我上去看看仓房。”我在底层的牛栏里找到了一道通向上面的石梯。因为下雨的缘故,马厩里散发着一股干燥而且愉悦的味道。这里巳经没有牲口了,大概被主人一起带走了。仓房里还有满满的半屋干草。屋顶上有两个窗子,其中一个钉着木板,另一个是狭窄的老虎窗,朝北面开的。仓房里有一道斜槽,是用来叉起干草从这儿滑下去喂牲口的。地板上通楼下的方孔上架有横梁,运草车开进楼下,就可以把干草叉起送到楼上。我听见屋顶上的雨声,闻到干草的味道,当我下楼时,还闻到牛栏里纯净的干牛粪味。我们撬开了南面窗户的一条木板,窥视着院落里的情况,从另外一道窗,能看见北面的田野。如果需要逃跑的话,两个窗子都通屋顶,倘若楼梯被封锁的话,还可以利用那喂牲口的斜槽滑下去。这个仓房很宽大,要是有动静,还可以躲在干草堆里。这似乎是个隐蔽的好地方。我相信,如果我们刚才没有遇到那子弹的话,一定早就平安到达南边了。南边是不可能有德国军队的,他们从北边赶来,从西维特尔赶公路而来。他们不可能从南边绕过来。相比之下,意军对我们更有危险性。他们惊慌失措了,看见任何东西都胡乱开枪。昨天夜里我们撤退时,还听说有许多德国兵穿上了意军军装,混在了从北方撤退的队伍中。我不相信,战争中尽是这种谣言,但也说不定真的有这种事情,也许我们的人也有穿上德国制服给他们捣乱的,不过似乎有点儿难度。我不相信德国人会这么做,他们也没必要这么做,我们的撤退根本用不着人家来捣乱。军队这么庞大,路又这么少,必然会产生混乱的局面。根本没人下令指挥,更不要说什么德国人。不过,他们还是把我们当做德军开了枪,打死了艾莫。干草味很香,我躺在仓房里的干草堆上,就像是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那时我们就躺在干草堆里聊天,用气枪打停歇在仓房高墙上的麻雀。那座仓房现在巳拆掉了,有一年他们把铁杉树林砍了,从前是树林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些残粧、干巴巴的树梢、枝条和火后的杂草。巳经回不去了,要是你不往前走,又怎么样呢?你再也不能回到米兰,即使回去了,又怎么样呢?我听到从北面乌迪内方向传来的枪声。我只听见机枪声,没有炮声。这说明,公路边一定还布置着一些军队。我朝下望去,借着这干草仓房内昏暗的光线,看见皮安尼站在下边卸草的地板上。他拿着一根长香肠,一壶什么东西。我昏昏沉沉地躺在干草上,几乎快要睡着了。“上来吧,”我说,“梯子就在那儿。”说完我才意识到,应该下去帮他拿上来。“博内罗呢?”我问。
“我就告诉你。”皮安尼说。我们走上梯子。把食物放在楼上的干草堆上。皮安尼拿出他的刀子,上边带有拔瓶塞的钻子,他用那钻子去开酒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