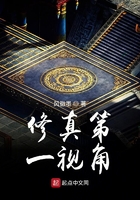一连几天,唐翱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门心思琢磨穆厚坤给他的书。
通篇细致看过后,他便急不可耐地跑去了穆厚坤家里。
此时穆厚坤正与孙小帅在厅内聊天。见到唐翱,穆厚坤向孙小帅介绍说:
“这个唐翱是工商总局督办唐端的二公子。”
孙小帅礼貌地点了点头。
唐翱兴致勃勃地说:“穆先生,你送我的书,我都看了,不过还是觉得不过瘾,特来聆听你的教诲,这位是?”
“这位孙小帅,是我的一个小兄弟。”
孙小帅刚要问好,“唐少爷”三个字刚一出口,便被唐翱抢话说:“不要再叫什么少爷不少爷了,我算什么少爷……你们刚刚在聊什么?”
穆厚坤如实道:“说到皇上推行的新政举步维艰,我们正在想是否有办法可助康梁两位先生一臂之力,以助皇上真正驭权。”
一听这话题,唐翱便兴致大起:“新政我也略有所闻,好像我父亲督办的工商局就跟这个有关。”
穆厚坤叹口气,不禁大发感慨:如今以西宫太后为首的那群老顽固还在醉生梦死,对外不知抵抗只知一味割地赔款以保荣华富贵,对内却施行越来越苛刻的专制统治。百姓生活日益困苦,甚至卖儿卖女只求一顿温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如他这般感慨者,在眼下的中国又何止一人。
在穆厚坤看来,目前只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变通引进西政、西艺来开风气,改造弊端。只有学习西方,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才能发展中国,这也就是所谓的新政。
对于新鲜的言论、新鲜的事物,唐翱向来是充满了向往与热情。再听穆厚坤一番讲述,唐翱大有一股恍然大悟之感。
唐翱的表现让穆厚坤甚是满意,他拉着唐翱讲道:“康先生所谓的变法有三个主张,即‘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政治上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经济上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除此之外,还要‘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
唐翱不无担忧地说:“时政已然如此,现在变是否晚了点?”
“西方人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呢?施行变法三十年而强大。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口之多,变法三年,就可自立。此后蒸蒸日上,富强之势,可以凌驾于万国!如若还不及时翻然变计,图生存、图自强,那么,我们就只有等着受外夷马蹄的蹂躏了!”穆厚坤越说越激动,“唐翱,我们不仅仅要做这个奇迹的见证者,还要做他的缔造者!用我们的双手、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勇气来支持康、梁两位先生的维新。”
唐翱被他说得激动万分,三个人又各自一番讲述后,穆厚坤把唐翱带到了院子里,指导他拳脚上的功夫,三人练习得不亦乐乎。就在这当口,小旺子突然匆匆跑来:“二少爷,二少爷……老爷四处找你呢,已经发火了。”
赶回家后,唐翱惴惴不安地向书房走去,唐允走在前面,唐五在后面跟着。
唐翱小声问道:“你知道爹找我什么事吗?”
唐允也是低声说:“我怎么知道。你这天天闯祸的性子,爹肯定又是哪里被你气着了。你等一会儿仔细着回话。”
“要不你去跟爹说,就说我身子不舒服,今天就不去见他了,明天、明天再去向他老人家请安。”唐翱这话刚一出口,便被唐允瞪了一眼。唐翱哼了一声,报以白眼,“行,我知道了,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就知道你见死不救。”
唐允则催促说:“瞎嘀咕什么呢?快点,别让爹等急了。”
唐翱叹了口气,不得已加快了脚步。等二人进了书房,唐翱立即躲在大哥身后,低着头不敢多说话,唐允拉了下唐翱的衣角,示意弟弟开口。
唐翱怯怯地喊了一声“爹”,惹来唐端低低地哼了一声。他自觉没趣,寻了个椅子坐了下来。
唐允一眼就看见后窗户开了一条缝,狐疑道:“后窗户怎么开了?”
唐五快步走向后窗,窗外随着搬米面劳工混进来的马祥祺急忙猫着腰跑开了。
关好窗户后,唐五便退了出去,轻轻地带上了房门。
唐端看看唐翱开口便问:“你最近是不是常跟那个穆厚坤混在一起?”
对老爹脾性了解得甚是透彻的唐翱自然知道不能如实回答,于是嘴硬说:
“没有混在一起。”
“还敢顶嘴,这是什么!”唐端说着,把《民约论》摔在了唐翱面前。
唐翱忙解释道:“这就是一本普通的西方书。”
“你以为我不懂,这上面讲的是君主立宪,正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所倡导的,你看这些东西,迟早要给唐家带来祸患。今天起,不准出家门半步,在家好好给我待着。这个穆厚坤背景复杂,弄不好会惹祸上身,连累唐家的。”
唐端的语气远远超乎了寻常的严厉。
唐翱倒是歪头道:“我不怕,大不了所有的祸事我一人承担。我可不像您这么怕死。”
唐端被他这话气得不断咳嗽,唐允忙起身拍着父亲的背,嘴里指责道:“父亲说的都是为你好,你怎可这么不知好歹?”
颇有些不服的唐翱刚想辩驳,眼珠一转,敷衍说:“孩儿鲁莽说错话,请父亲原谅,孩儿以后听爹话就是。”
唐端稍微平息了下,说道:“朝廷已经下旨命我署理四川,明日即将启程。
我不在家,你可千万不要胡乱跑,要听你大哥的话。现在朝廷里好几派,争得不可开交,说不定哪天就要出大事,我们唐家千万不能卷进去。穆厚坤就是和康梁一党的,现在得意的很,说不定哪天就要人头落地!你不要跟着做冤死鬼!”
唐翱不以为然,但还是嗫嚅着:“孩儿听见了。”一听老爹要离家去署理四川,唐翱心里已经说不出有多美了。
唐端不耐烦地吩咐唐翱出去,并且让唐允留了下来。
“为父赴四川后,家里就要你多照顾。你母亲身体不好,切不可让她再多操心;对于翱儿你要多加督促,不可再纵容他。最重要的是,那个铁匣子你要好好保管,日后出事,这个也可用来救命。切记。”
唐翱刚一出书房便向穆厚坤家溜了去。穆厚坤关心地问唐端是不是为难他了,唐翱竟然嘿嘿一笑:“没有。他就找我说了点老生常谈的事情。我听着烦,就趁着他跟我大哥聊天的空当溜了出来。我爹说他要去四川了。我自由了。”
一听这话,穆厚坤也高兴地道:“那好啊!以后你来这边就不用偷偷摸摸了。可趁机多学习点新思想、新知识。”
唐翱有些犹疑:“可是我爹说你现在得意的很,说不定哪天就要人头落地的!”
穆厚坤爽朗地笑了,慷慨道:“贪安稳就没有进步,要进步就要历些危险。”
此时,《南京条约》、《马关条约》已经签订,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已然成为日本时刻威胁中国的跳板。政府每年还要付出巨额赔款,英美俄等国又是虎视眈眈,时刻准备来这儿分一杯羹。如果现在不维新,不自保,那么没有多久,怕是所有人都会成为亡国奴,成为奴隶种。而大清国却人人有愚昧之病,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着,从来不知道平等为何物,明明是奴才却觉得自己是主子……见唐翱也算得上是开明之人,穆厚坤便放心地说道:“你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不思变通。我敢断言,如果继续这样,不出一年,他只能守旧而亡,带着他所谓的忠心,为他已经病入膏肓的主子殉葬。”
听到这里,唐翱倒是没有反驳,只是不禁发问:“先生你不怕死吗?”
“死,怕什么,我出对得起天地浩然正气,入则经受得了良心拷问。何谓大丈夫,那就是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人必有一死,但求死得其所。我奋斗过、努力过、坚持过,那么就不枉这人世走一遭。”
穆厚坤稍停了片刻,随即情绪又不受控制般激荡了起来,“如果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国将灭亡而无动于衷,为了这一身皮囊而畏畏缩缩,我告诉你,我做不到。
我要为所有志同道合的人、所有为了救国而牺牲的同胞呐喊、奋斗。你想做什么样的人呢?是自己荣华富贵但是看着四万万同胞生活于水生火热之中呢?还是为国为民奔走呐喊放弃荣华富贵?为国为民者,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带来幸福。”
唐翱看着穆厚坤不知说什么好,任凭他继续说了下去。
“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行义仁之强。所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是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二是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三是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朝廷已经病入膏肓,新时代已然来临,发了霉的三坟五典里面根本找不出救这个国家的药方。我们要救国,就要寻找新的途径,那就是维新,那就是变革。我们要实现保国保民,天下大同的世界,让其他各国不敢再看不起我们,不敢欺负我们,恢复我们泱泱大国的气魄……”
唐翱听着听着脸上已慢慢露出了笑容。一口气说了半晌的穆厚坤奇怪地看着唐翱,问他这是怎么了。唐翱兴奋道:“原来我只是游移不定,所以故意来激发先生,让先生给我讲得更透彻、更明了一些,坚定我的信心。”
穆厚坤忽然抚掌而笑:“你真是机灵古怪。”
被母亲骂了一通的秋蓉失魂落魄地跑出家门,她跑向河边,向河当中走去,越走越深,河水慢慢地没过她的肩部……河岸上,一个身穿粗布衣裳、背着个包袱的中年汉子骑马走过来。此人叫陈省之,是个教书先生。他一看眼前这般光景,顿时着了急,急忙下马,解开包袱扔在地上,奋力向河水中的秋蓉冲过去。
陈省之一边跑一边喊:“姑娘,使不得,使不得啊……”
水已经没过了秋蓉的头顶,陈省之一个猛子扎下去,将秋蓉救了起来。
秋蓉在水里还兀自挣扎着要寻短见。陈省之也不理会,直接将秋蓉抱到岸上。
这时秋蓉已经浑身湿透,坐在地上大骂陈省之。
“你干吗要救我,谁要你管我的闲事?”
陈省之一揖到地:“小可姓陈,名省之。姑娘,有什么想不开的,要寻短见啊?”
秋蓉大哭起来,搞得陈省之一时手足无措:“你别哭啊,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你这么哭,过路的人要是看见,还以为我……”
秋蓉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怒道:“谁让你救我了?”使得陈省之一时语塞。
两人坐了一会儿后,陈省之便带着秋蓉到了路边的一个小摊吃饭。
秋蓉还是一副了无生趣的样子,嘴里念叨着:“唐家看我被土匪抢了,就当我死了,还把我写进了什么烈女簿……”
陈省之气愤道:“这个唐家简直是迂腐之至,可笑之至,禽兽不如,我带你去找他们理论,看他们有什么话说!”
秋蓉叹口气,幽怨地说:“你去找他们?唐家老爷现在进京当了大官,只怕你还没摸着人家的门呢,就得丢了性命……别说唐家了,就是亲爹亲娘还不是一样嫌我丢人,容不得我。”
陈省之叹着气问道:“那你打算怎么办?”
秋蓉黯然摇头,一副无所相依的样子。
陈省之试探着说:“要不,你跟我去龙头坝?”随即他补充说,“你放心,你我以兄妹相称,我在龙头坝教私塾,乡邻对我还算恭敬。不管怎么说,能过个安生日子。”
秋蓉犹豫后,点了点头。陈省之便带着秋蓉、牵着马向龙头坝村口走去。
当地财主林公溥已经领着几个人等候在那里了,他上前笑道:“省之兄,你想得我好苦啊,你回家数月,龙头坝的孩子没人管,我都快愁死了。”
此时陈省之的每次外出,在林公溥和众多乡亲眼里还只是简单的回家探亲。
陈省之微笑说:“公溥兄,你就是偷懒,你怎么就不能帮着管管。”
“我哪有你那两下子,管不了,管不了。”林公溥说着,眼睛却不住地往秋蓉身上瞟。
陈省之指着林公溥对秋蓉道:“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我的好友林公溥,龙头坝的大财主。”随后又指着秋蓉,“这是我表妹秋蓉,家里出了些变故,我就把她带出来了。”
林公溥显出一副很同情的模样:“姑娘不用担心,到了龙头坝就像是到了自己家。”秋蓉点头谢过后便随着大家一起去了林家客厅。
林公溥一路面露怀疑之色,望着陈省之低声问:“省之,你跟我说实话,她真是你表妹?”
陈省之当即回答:“当然,这还有假?”
林公溥似乎仍有些不信:“如果真是你表妹,那我就有句话要跟你说说了。”
陈省之摆出一副愿闻其详的态度。
林公溥再次压低了声音,先是埋怨老婆至今也没给他生出个一男半女,自己又家大业大,随即又嫌弃龙头坝的女子性情野得很。陈省之一听便想到他定是打起了秋蓉的主意,推脱说回去问问秋蓉再给他回话。
在龙头坝已住下一段时日的秋蓉提着菜篮子在街上走着,她的肚子微微隆起,街上的百姓对此议论纷纷:
“这不是陈先生的表妹吗?大姑娘家,怎么肚子大起来了?”
“看来这陈先生也不是什么好人,这不是把人家给毁了啊!”
秋蓉只好面露羞怯地匆匆走过去。
耐不住的不仅是秋蓉,还有林公溥的老婆金凤,她正揪着林公溥的耳朵发威:“说,秋蓉的肚子是不是你弄大的?”
林公溥赶忙辩解说:“真的不是我,你听听街上的人都怎么说的……都说是陈省之干的。”
金凤则尖声喊着:“陈先生才不是那号人,我看就是你。”说着她又揪住林公溥的耳朵,把林公溥疼得大叫起来。
被金凤收拾了一顿的林公溥心里憋了一肚子火,随即直奔林家私塾,正赶上陈先生刚刚下课。林公溥也顾不得寒暄,上前就问道:“省之兄啊,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陈省之疑惑地问:“什么事?”
“你还问我,你去外面听听,别人都怎么说,说你把秋蓉的肚子搞大了!”
陈省之听后只是低头不语。
林公溥又说:“我说秋蓉怎么老是不搭理我呢?原来你们……唉,现在我老婆还以为是我干的,你瞅瞅,今天把我抓的。”
陈省之想了想,低声说了句:“我只能娶了秋蓉。”
这话听得林公溥目瞪口呆:“你……真有你的……我算是看走眼了……”
碰巧这会儿林舒拿着点心走进来,林公溥问道:“妹妹,你怎么来了?”
林舒把点心藏在身后:“就许你来,我怎么就不能来了。”说着把点心递给陈省之,“陈先生,这是我做的点心,你尝尝。”
陈省之有些意外:“有劳林姑娘了。”
一旁的林公溥则惊讶地对林舒说:“你什么时候学会做点心了?我当了你几十年的兄长,从来没吃过你做的点心。”
林舒有些不好意思,一个劲儿将林公溥往外推:“以后做给你吃,快走吧!”
林公溥恍然地看着林舒和陈省之,林舒则愈发羞怯。
“我还有事,改日登门拜访。”有些尴尬的陈省之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林舒却拿着点心追了出去,被林公溥一把抓住,问道:“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看上他了?”说得林舒更加羞怯了。
“什么呀,胡说……陈先生,等等我!”
就在林公溥去私塾的空当,金凤冲到了秋蓉住处,一把薅住秋蓉的头发把秋蓉拖倒在地,一连扇了几个耳光。
“你个臭不要脸的,骚货烂东西,勾三搭四……”
秋蓉奋力而起,推开金凤:“你疯了!”
“我就疯了,谁家男人不好勾搭,凭什么就勾搭我男人。还有廉耻吗?我告诉你,在我们林家你就是个臭要饭的,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你以为勾搭上我家林公溥你就能进到了这个家门了吗?门都没有!”金凤说着又要撕扯秋蓉的头发。
秋蓉忽然爆发,清脆地扇了金凤一个耳光:“滚!”
一时间,金凤被打得愣在了那里。
“我告诉你,如果你再这么胡搅蛮缠诋毁我的声誉,我绝不罢休。”秋蓉说着从针线筐里抓起一把剪刀。
金凤被她吓得灰溜溜跑了。
出乎秋蓉的意料,陈省之竟然向她提了亲。
就在几天后,秋蓉的院子里便摆了几桌酒席,气氛既不热闹也不冷清,林公溥也在座,低着头大口喝酒,抬起头,皮笑肉不笑地看着陈省之。
陈省之坦然地带着秋蓉给乡亲们敬酒:“今天是我和秋蓉大喜的日子,各位能赏光,陈某感激不尽。在龙头坝这些年承蒙各位照顾,今天终于娶妻成家了,我敬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