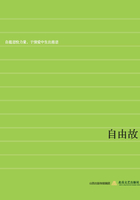因为我和阿道夫在维也纳所学的专业不同,所以很快我们这段友谊就显现出了它的脆弱之处。每天早上,当我准备去音乐学院上课的时候,我的朋友还在床上酣睡;而到了下午,当他想工作的时候,我的乐器练习又打扰了他。这种情况经常引发我们之间的冲突。
“什么音乐学院,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有什么可教的东西?”他想要向我证明,即便是像他这种没有上过音乐学院的人,也同样能够达到我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他说这依靠的并不是那些教授的智慧,而是个人的天赋。
抱着这份野心他开始了一项令人惊奇的实验。我至今也说不清,他这项实验到底价值何在。阿道夫回想起了他以前接触过的一些基本乐理知识。语言似乎很难达到他的目的,于是他摸索着看能否将单独的声音与音符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他想让这种音乐语言被赋予情感。对于一部最终将要呈现在舞台上的歌剧来说,声音与感情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然而我,一直对自己在音乐学院所了解到的真谛表示深信不疑,并且还或多或少地带着些藐视情绪在看待他的实验,因此这让阿道夫感到非常的生气。他独自在这些抽象的实验上忙活了好长一段时间,或许是因为他想从根本上颠覆我的学院派知识吧。当几年过后,一名俄国作曲家在维也纳以相似的实验引起了一阵轰动之时,我才回想起我朋友的那次创作尝试。
那段时间,阿道夫搞了大量的创作,其中有一些原创故事,但主要的还是戏剧。他在屋子里通宵达旦地伏案工作,至于具体做了些什么,他却对我言之甚少。他只是偶尔朝我床上扔来几张他的近作,或者自鸣得意地从他风格古怪的作品中挑选几页读给我听。
我知道,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植根于理查德·瓦格纳的世界,也就是说,故事背景通常都是古代德国。有一天我无意间对他说道,据我在音乐历史课上学到的知识,世人在瓦格纳死后出版的作品中发现了一部名为《铁匠维兰德》的音乐戏剧的创作提纲。事实上,这只是篇简短而仓促的文字,连一个上演本的草稿都算不上,并且也没有对任何素材进行过音乐处理。
阿道夫听罢便立马从他那本《众神与英雄》中翻到了维兰德传奇。说来也奇怪,虽然在维兰德传奇中,尼杜尔国王的行为动机完全是出于自身的野心和贪婪,但我的朋友对此却并不是特别反感。对黄金的渴求,是德国神话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而这既没有给阿道夫带来一点消极影响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积极影响。尽管故事中还描述说,维兰德为了复仇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强暴了自己的女儿,并用他儿子的颅骨做成了饮酒用的高脚杯,但这些似乎都未能让阿道夫有所触动。当晚他便开始了创作。我确信他在第二天早上就会得意地向我展示出他的戏剧新作——《铁匠维兰德》。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早上什么也没发生。但是当我中午回来吃午饭的时候,我十分惊讶地发现阿道夫正端坐在钢琴前。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没有过多的解释,他直接对我招呼道:“听好了,库斯特尔!我将要把维兰德写进一出歌剧。”
我当时被震惊得哑口无言。
阿道夫一边享受着我的惊诧反应给他带来的快感,一边继续弹奏着钢琴,或者对他而言,应该叫作继续“玩”着钢琴。老普鲁拉斯基在世的时候,曾经教过他几手,但毫无疑问,他这样的水平离我所理解的“弹奏钢琴”尚有一段距离。
当我回过神之后,我便问阿道夫,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又是如何下手的。
“很简单——我来创作音乐,你,把它记下来。”
阿道夫的计划或构思几乎总是超出常人的理解范围,而我对此也早已习以为常。但如今就连论及音乐——这片我的特殊领域——我都实在无法跟上他的步伐。对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我毫不质疑,但恕我直言,他毕竟不是个音乐家;他甚至连一样乐器都不会。他一点儿音乐方面的理论知识都不具备。他怎么能够凭空想象出一部歌剧?
我只记得当时我作为一个音乐人的自尊被伤害了。于是我一言不发地出了门,走到附近的一个小咖啡馆坐下写作业。
然而,我的朋友对我的行为一点儿也不感到生气,当我晚上回到家里以后,他却显得越发的平静,“好了,序幕完成了,听着!”
于是他便凭着记忆为我弹奏了他自己创作的歌剧序幕。
当然,对于这段音乐,我一个音符都想不起来了。但有一样东西还保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段由自然音乐元素构成的咏叹调,他打算用传统的乐器来进行表演,可是由于这种演奏听上去还不是很优美,所以我的朋友决定采用一种现代交响乐器,那便是瓦格纳大号。至少这样的音乐能够让人们接受。他的每一个独立的音乐主题都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说整段序幕让人们感觉水平低下的话,那可能只是因为阿道夫还演奏得不够好,也就是说,他无法更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当然,他的作品完全是受到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影响。整个序幕由一系列单个的主题构成,尽管他选择的每个主题路线都有着很好的发展空间,但不得不承认这已经超出了阿道夫的能力范围。毕竟,他也没有接受过相关的专业培训,他又能够从哪儿获取这些必要的专业知识呢?
在他演奏结束后,阿道夫想听听我对他作品的评价。我知道他对自己这份作品的期望很高,而且我也知道,在音乐这方面,我的赞赏对他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但是,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
我对他讲道,基本主题还是不错的,但他必须得知道,单靠这些主题是不可能构成一部歌剧的,并且我还声称自己十分乐意教给他一些必要的理论知识。
此话一出,便立马激起了他的愤怒。
“你以为我疯啦?”他冲我吼道,“你有什么资格教我?废话少说,把我刚才在钢琴上弹的东西丝毫不差地记下来。”
当我的朋友用这种方式跟我讲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我是非常了解的,并且我也意识到,与他针锋相对是落不到好下场的。所以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把他弹奏的东西记录了下来。但没过一会儿,查克雷斯夫人就敲响了门,示意我们时间已晚,于是阿道夫只好打住。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去了学校,当我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阿道夫就责备我居然“在他歌剧创作的关键时刻”一走了之。他已经为我备好了乐谱纸,准备马上开工。由于阿道夫的演奏总是随心所欲,不同我保持一致,并且也没有统一的音调,所以我很难跟上他的节奏。我试图让他明白,为了更有效地配合,他在弹奏钢琴的时候必须得保持一种统一的音调。
他大言不惭道:“谁是作曲人,是你还是我?”
我所能够做的就是记录下他的音乐思想和理念。
我只好叫他重弹一次,以便能让我记下,他也照做了,这么一来我们才有了点进展;然而对于阿道夫来说,这种进度实在太慢。我告诉他我想亲自把刚才记下的通弹一遍。他表示同意,于是我便坐上了钢琴,而他则变成了我的听众。
说来也奇怪,我倒是更喜欢我自己弹奏出来的效果,也许是因为这部作品本身在他的头脑中就有着一个精确的构思,所以无论是他的拙劣技艺还是我的记谱法和演奏,都无法与之相符。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歌剧的序幕上耗费了几天,或者更准确地说,几夜的心血。阿道夫要求我将整个作品用一种合适的公制形式表达出来,但不管我怎么做,阿道夫都觉得不满意。因此很多时间我们就耗在了这件事情上面。最后我成功地使他相信,这么做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可一旦我试图一次性演奏完整个章节的时候,他又开始极力反对。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在那些费心劳神的夜晚,是什么让我朋友陷入到了绝望的边缘,又是什么让我们的友谊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这段歌剧序幕就像是一部已经完成好的作品一样储存在他的大脑中,正如他从前那样,在还未动笔之前,心里就已经有了一座大桥或者是一座音乐厅的设计方案。然而,虽说他是铅笔素描方面的专家,并且他能够通过绘画,勾勒出他的想法,但是这样的手法运用到音乐领域可就不那么灵验了。而他想利用我来助他完成歌剧的企图,却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因为我的理论知识只会对他的直觉构成阻碍。他脑海中这个大胆而重要的构想,在还未付诸行动之时,就已经将他带到了彻底绝望的边缘。尽管他看上去依然显得不可一世,但有那么一瞬间,他却对自己的使命感产生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