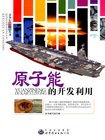我向华盛顿大学递交了入学申请并被正式录取。除了我同母异父的哥哥约翰外,我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就像其他所有经历过大萧条洗礼的家庭一样,我们家也负担不起我的大学学费,但是父亲母亲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我入了学,我终生都不会忘记这份深厚的亲情。
对于我的梦想,他们总是全力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意外身亡,没过几年,母亲由于思念过度,在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也撒手而去。如今想来,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能活到波音747飞机诞生的那一天啊!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放任我日复一日埋头于画飞机的草图,他们也常被挂在天花板上的那些飞机模型碰到脑门儿。如果他们的在天之灵知道我儿时的梦想已经实现,肯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1939年秋季,我进入华盛顿大学学习。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同时也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时期。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首先爆发,这让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顿时感到乌云密布。每当我和其他人拼车往返于学校的时候,时局总是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
华盛顿大学航空工程学院的师资队伍颇具实力,其中就有伊斯门教授、马丁教授和柯尔斯顿博士等人。我的老师当中有一个名叫罗伯特·哈齐的年轻助教,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退伍后进入波音公司工作。在他于1958年跳槽到麦克唐纳公司之前,我和他一起参加了波音707飞机项目。之后,罗伯特主持了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DC-10飞机项目的开发,这可是波音747的竞争飞机中最为成功的一个。
我尤其喜欢数学和物理这两门功课,所以华盛顿大学的课业对我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在学习上,同学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不过我总能拿到最优异的成绩,仅有一次是例外。在先进航空技术这门课上,我的成绩排在了好友戴利·迈尔斯之后。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后来他官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副局长。
总而言之,华盛顿大学为我提供了极好的教育环境,我享受在那里度过的分分秒秒。在那段时间里,我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知识并且明白这才是正确的途径,而我希望在一生中都能坚持如此。
在大学的最后两年中,每逢暑假我就到波音公司打工,在工厂的部件区从事技工的工作。我在波音公司的时薪高达62.5美分,我的学费也就有了着落。
在我结束克里夫兰中学的学业之前,陆军和海军曾分别向我们这些毕业班的男生推荐了自己的预备役军官训练项目。陆军的这一项目仅持续两年而且没有多少吸引人之处;相反,海军的预备役军官训练项目为期四年且安排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科目。权衡之后,我最终选择了加入美国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海军的训练生活与我的大学生活同时展开。
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相当大方,每天支付给我25美分,这在当时对我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更重要的是,我在这个训练营里学到了许多有关天体导航的知识,这对于提高航空飞行能力大有裨益。这样一来,我终日奔忙于大学学业和预备役军官训练项目,再加上暑期要在波音公司打工,直到毕业前我的生活一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幸运的是,尽管忙得昏天黑地的,我还是逮着机会认识了一位名叫南茜·法兰西的年轻姑娘。南茜比我早一年进入华盛顿大学学习,主修经济。大三那年,我在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举办的一场舞会上结识了南茜,之后开始频频约会并很快坠入爱河。南茜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孩,言谈举止都显得那么与众不同,且十分讲礼貌,用当年的话来形容南茜就是“很有教养”。
与此同时,欧洲的情形日益糟糕。1940年,希特勒的大军相继入侵一些低地国家和法国,而不列颠之战也拉开了序幕。得益于美国《租借法案》的实施,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最终勉强取得了胜利。而我们也更加清楚地知道,在法西斯主义日益扩张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维持中立都是极不现实的。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当时我正念大三。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迫使美国宣布参战,这对我们来说是始料未及的。由于美国一向不赞同维持大量常备军,仓促宣战后,整个国家根本无法立刻组织一支大规模的战斗部队,同时也缺乏足够的装备。我们的工业界也尚未做好大量生产足以满足美国和其同盟国需求的飞机、船舶以及其他战争所需的武器。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罗斯福总统于12月8日向国会和全国人民宣布美国已参战时,那些压在我心头沉甸甸的难题。就像所有年轻的美国同胞一样,我随时准备为我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去。我暂时放弃了所有关于职业生涯的设想,并做好了应征入伍的准备。
大四那年,我的校园生活陷入了一种极度疯狂的状态。生活显得那样紧张忙碌,而我们也学会了苦中作乐。我知道同学们很快就要奔赴各地参加这场世界大战了。我的许多朋友也早已做好了准备或已经放弃了学业,他们热切期待着入伍那一天的到来。此时的校园生活已经变得十分不同寻常了。
1943年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里,一架B-29“超级空中堡垒”原型机从校园上空呼啸而过,冲着南面的波音机场而去。飞机上的一个发动机燃着熊熊大火,只见一股黑烟拖在飞机之后。后来,当我们开车回家的时候,一片烟幕让我第一次有了不祥的预感。我们的视线被那些在度瓦米许一带聚集的抢险车闪耀的车灯吸引了过去。
因一台发动机起火,波音的这架B-29轰炸机原型机坠毁在紧邻波音机场跑道的一家肉联厂内。著名试飞员爱德蒙·艾伦和其他几人均在这起事故中不幸丧生,艾伦的去世无疑使波音公司蒙受了巨大损失。除了参与B-29飞机的试飞工作外,这位麻省理工学院出身的工程师还参与了波音307“同温层飞机”和314型“飞剪”号的首飞工作。每一个人都非常钦佩艾伦的勇气,并深深地怀念他,我也不例外。
学校提前为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以便我们能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在1943年那个多事之春,仅仅两天的时间内,我取得了航空工程专业的学士学位,与南茜在西雅图西城举行了婚礼,并收到了美国海军的入伍通知书,成为了一名海军少尉。
南茜和我在西西雅图的沙滩附近的阿尔基公理教会教堂举行了婚礼,伴郎是我的兄长卢和大学同学雷·奥利弗,婚宴是在南茜父母家的房子中举行的,那是一座能俯瞰整个普吉特湾殖民时期风格的大房子。当时的我可谓百般滋味在心头,战争的脚步声已越来越近,我的口袋里还揣着一份入伍通知书,我感到兴奋,心头也多多少少有几分紧张。
我被派往海军在迈阿密的猎潜艇训练中心,幸运的是,已婚的身份使我能携南茜一同前往。我们坐火车朝芝加哥而去,那段旅途中还有卧铺可供休息。到了芝加哥后天气十分寒冷,我们在那里换乘另一列火车后却只有硬座了,这段路程足足走了3天。
火车上到处都是各军种征召入伍的人,许多人喝得醉醺醺的。一路上,我为了避免南茜受到骚扰,不断跟他们发生冲突。每次登车的时候,驻扎在那里的宪兵会搜查每一个穿着军装的人,但是这对防止车上的人喝酒根本起不到作用。
习惯了西雅图的生活,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迈阿密,潮湿闷热,到处都是当地人称之为“棕榈甲虫”的蟑螂。到那里几天后,我和南茜找到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住所,这才开始安定下来。我的军旅生活很快就开始了,训练生活一直持续到当年年底才结束,这时我成为了一名战时的海军现役军人。
遗憾的是,那里无法为我提供海军航空兵的职务,我非常渴望加入这支队伍,但环境却不允许我这么做。尽管我曾学过天体导航学,但是在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接受了航海术的训练后,我似乎也只有在海上服役的份儿了。尽管遭到了拒绝,我确实是早在大学时期便已递交了参加飞行员训练的申请。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指挥官把我叫去狠狠训了一通:“我们培养你是要你当一名舰上人员,该死的,那才是你要做的!”他还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你将在驱逐舰上为你的国家服务。”
结果是,我被派到了“爱德华·艾伦”号护航驱逐舰(DE-531)上,这是一艘刚从波士顿海军造船厂出厂的护航驱逐舰,隶属于大西洋舰队。之所以命名为“爱德华·艾伦”号,是为了纪念于1942年5月在珊瑚海战役中牺牲的一名海军功勋飞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