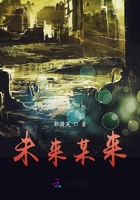楚当当的艺考成绩公布了,分数相当不错,只要文化课过关,她肯定能上中国美院。于是大家决定要在周末庆祝一番。到了聚会当天,楚当当早早地来到断桥。可是,陆续有人请假,左等右等,最后只有杨略一人参加。
楚当当嘟着嘴说:“就咱俩大眼瞪小眼的,还是算了吧。”
她原先的安排是,平时忙碌,好不容易出来放风,肯定得好好玩。趁着春光明媚,看看桃花,划划小船,玩三国杀、狼人游戏,再摆出各种古怪的姿势来合影。可现在呢,就俩人,玩什么都不行啊。
杨略看出了楚当当的失落。
“当当,其实,就我们两个人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租辆自行车,沿着白堤,一直骑到西泠桥,然后再去苏堤。说不定,我还可以给你讲讲西湖的典故呢。”
“好,我就接受你这文豪的熏陶。”
楚当当性情率真,执着于艺术,身上有股子洒脱劲儿。与她交流,杨略总是觉得很放松,很自如,当她是好兄弟。与之相比,他对葛怡的情感,则是爱中有敬,心里是紧张的。一想到葛怡,他心里难免酸楚。幸好楚当当已经跨上了单车。
“走吧!”
楚当当照例穿得随便,不过是一条背带牛仔裤,一件白色衬衣,此刻轻快地踩着踏板,两条小辫活泼地甩来荡去。虽说朋友来得不全,但她毕竟春风得意,所以脸上一扫往日的阴沉,变得明媚而娇艳。
杨略也追了上去,并驾齐驱,与当当开开玩笑,谈笑风生,不觉心里开朗了许多。
阳光很好,白堤苏堤都在春晓。一树树的桃花,正开得红艳艳的。柳树的黑枝桠上,显出一片青绿,像水彩在宣纸上层层洇开,近看却只有点点叶芽,娇嫩剔透,让二人赞叹不已。
渐渐地就到了西泠桥,杨略详细地说了苏小小与阮郁的故事,说这二人才貌相当,情投意合,却不能白首终老,乃是千古憾事。又念了那首著名的苏小小诗:
“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楚当当长于绘画,但对历史掌故却知之甚少,她以前一直以为苏小小就是苏东坡的妹妹,今天听杨略一说,才知道她是这样凄婉的才女,不由感慨一番。
再往前骑了一段,路边出现了一个老人的雕像,穿黑布大褂,戴瓜皮帽,留一部山羊须,一边观看湖光山色,一边在画册上写生。
“这是黄宾虹。”
这可是楚当当的强项了,她看过不少黄宾虹的画作,多少了临摹过几幅,对他的风格也了如指掌。可是那种微妙的审美感觉,她口拙嘴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而对于黄宾虹的生平事迹,她因为没兴趣,所以不甚了然,所以最后只好说:
“是画山水画的。”
幸好她灵机一动,取出手机,上面刚好有几幅她在参观黄宾虹纪念室拍的照片,就给杨略看,是几幅云雾湖山图,笔墨纵横,气象万千。
正在看时,楚当当忽然指着远处,说:“看,鸟——”
一只鸟从林中飞出来,黑白相间的翅膀扇动,一下,又一下,像慢镜头,他看得很分明,很安静,每一下都反射着阳光。背景是蓝空、山影、湖光。黄宾虹的画,似乎在眼前出现了。杨略觉得,这画面,真可以写首甜美的诗。
最后,他们一起坐在桥栏上,双脚悬空,荡来荡去,自由自在。农谚云,二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可就变了。乌云远远赶来,一下遮住了太阳。空气猎猎地涌动,撞击着树枝。湖水汹汹地涌动,撞击着岸石。几枝去年的芦花在摇摆,像洁白的拂尘。
“冷吗?”
“还好。”
“真不冷吗?”
“嗯。”
杨略在包里取出一件外套,给楚当当披上,袖子在脖子前面上打了个结,垂在胸前。然后左看右瞄,轻轻一番拉扯,收拾整齐。
“听歌吧。”楚当当取出耳塞。“这边是左,这边是右。右边给你,左边给我。”
许巍的歌就这样塞进了耳朵,是《旅行》:
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
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
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
有一群向西归鸟
歌词很美,歌声自在,轻盈,每句末尾又出乎意料地一落,如同乘车疾行,忽然跃然下坡,人的心魂一时悬了空,麻酥酥的,晃悠悠的,然而无处不妥帖,无处不润泽。
楚当当喜欢旅行,应该也有这般潇洒吧。杨略的眼前,已浮现出楚当当云游的形象:双肩包,画板,轻盈的身姿。
风恰到好处地扑面而来,和乐曲走得很合拍,又细致地将头发吹起,她的,他的。风鼓荡着一种豪气,逸气,灵气,他想唱歌,清越的歌,明亮的歌,却怕忘记歌词,于是改为念诗:
像一只燕子淡入春天
像一尾鱼淡入江南
像一滴水淡入柳烟
一扇门豁然敞开,又大提琴一般
委婉而坚决地关闭
一扇门就这样淡淡地远去
像一瓣羽毛淡入日光
涣然冰释。一无所余
楚当当微笑着,看看他,又看看湖水,然后闭上眼睛,轻轻地说:
“虽然听不懂,但意境很美,很像一幅画,可惜我没带画箱。”
杨略也笑笑,忽然觉得,诗画相和,是多么美的事情。而他在诗里随机写出的“一扇门”敞开又关闭,然后淡淡远去,似乎也是有所指。具体指什么,他却不愿出,就这样含蓄着,朦胧着,也是好的。
“我们合个影吧。”
楚当当也同意了。他们请了一个路人,就把坐在桥栏上自由的样子拍了下来。
然后,他们坐公交车回去了。
车子空敞,一晃一颠,窗外的梧桐、楼房、行人也跟着轻松地摇晃。车内人的脸孔,都有一种美意,说话声也琳琅动听。他觉得心里亮堂堂的,又满满的,盛了一泓清水,要溢出来了,要痒痒地笑了,嘴裂开了,眼角皱了,但很安恬,依旧是一道静水,浅浅地流,美美地流,自给自足地流。
“笑什么呢?”楚当当在一旁问。
“没什么。”杨略把头甩了甩,由于离心力,几朵笑声飞了出去,像转动的雨伞上飞出的水珠。
“没什么是什么?”
“就没什么。我经常这样的,一个人偷笑。”
“我也是。”
他看看她,又看向窗外,心里憧憧地跳动。一道活水,喧喧地流,美美地流,畏首畏尾地流。
可是,该流到哪里去呢?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把照片发到了微信朋友圈里,本来想加上一句:“祝贺楚当当小朋友艺考成功,撒花!”又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把这句话删了,就剩下两个少年,坐在青春的桥头,坐在浩荡的春风里。
不明就里的朋友评论:“般配啊。”
知根知底的同学语带双关:“这个坐姿,很危险哦。”
于是就有了种种传闻,毕竟是在高三,烦躁的生活里需要调剂。大家并不想追究真相。真相总是无趣的,好玩的就是这种模糊劲儿,适合窃窃私语,适合刨根问底,聊以解忧。
对这些传闻,杨略有几分得意,又有几分不安。他偷眼去看葛怡,她依然故我,只是更沉默了些,偶尔也烦躁了些。陶坷坷向她问功课,她说了一遍,陶坷坷没听明白,她居然高声说:
“你好笨啊。”
她以前时常这样笑吟吟地骂杨略,几乎成了他幸福的专利了。而这次居然说给陶坷坷听,杨略不由心里一酸。但随即发现,葛怡丝毫没有打情骂俏的意思,她皱着眉头,一脸烦躁,真是生气了。这在她是不常有的,几乎算是失态了。
杨略有几分得意,又有几分心疼。
而作为当事人中的另一人,楚当当却似乎浑然不觉,只是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接连不断转发一些画作。而那些画作的作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她的指导老师端木宇。
最近,端木宇画出了一组戏曲人物油画,诸如昆曲《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和柳梦梅,面容是整齐清晰的,而戏服却用了金黄、殷红的色块,斑斓,璀璨,极丰富,又有种梦幻感,与《游园惊梦》的意境十分相符。而楚当当对作品的评价很简单,就是几个表情:一颗爱心,或是抛出飞吻。
杨略从中看到了端木宇的才气,也看出了楚当当的用意。楚当当这一手,真是无声胜有声,声明了立场,又不伤颜面。但杨略毕竟感觉出一丝尴尬。
“唉,我这是在做什么呀?”
当然,很快,传闻就消失了。毕竟是在高三,再大的新闻、绯闻,也抵不过高考的重要性。谁愿意在那些无聊事上耗时间?
自从一开学,老师们如同商量好了一般,都如上紧的发条,一节课紧似一节课。历史老师一脸严肃,告诫着大家:“文科学生,就指着历史争分呢!这历史啊,又考记忆,又考理解,现在要抓紧了,抓紧每一分,每一秒,不要空度一天。”数学老师也大肆宣扬:“文科的其它科目考的都是主观题,给你10分也行,给你8分你也没话说。只有数学,很严肃,也很客观,1是1,2是2,绝不含糊。只要认真学,数学就能拿高分,高考时就能往上拉名次……”
杨略自然也深知其中利害,他是一门课都不愿放弃。只是,前段时间心情抑郁,一些学习任务没完成,就让他有些恐慌,于是要加倍努力了。在每天的任务安排表上,他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尤其是数学,他立志要做完三本习题集。
于是,他马不停蹄地看书,做题。做完一项,就在安排表的相应位置打钩,然后也不休息,立即转入下一项。
然而,有时候明明在做数学试卷,心里却想着语文的一些知识点没掌握,于是去看语文,但刚看了一点,却牵挂着数学,于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天下来,学习任务没能都完成,心里就越发浮躁。
有时候,他好不容易把本日的任务全部完成了,却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成了移山的愚公,挖完了今天的几筐土,本来要休息了,可是一看大山依然巍峨,就着了慌,恨不能再多挖几筐,于是半点成就感也没有了。他的脑子里有个声音,对他抽着响鞭,大声呐喊:你该更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
他恨不能一天当两天用。
像是要响应这个愿望,他开始失眠了。前一次失眠,他是因为苦恋,只是个暂时现象。而这次呢,却是出于发自内心的恐慌。躺在床上,满脑子跑火车,什么杂乱的念头都在心里浮现。床头的闹钟噌噌噌地走着,声音清晰入耳,让他越来越着急,翻来覆去,难以成眠。
他默念了几首唐诗,心情稍微宁静,曾泉又不识时务地打起了呼噜,“咯啊啊——呼呜呜——”,不绝如缕,忽然翻了个身,鼾声停息了一会儿。杨略正觉清静,“咯啊啊——呼呜呜”,这次曾泉是侧躺,声音就直接穿入杨略耳朵了。
杨略用棉被捂住了耳朵,却也毫不济事。
他开始想葛怡,一如往日,他轻轻念着她的名字,心里涌动着柔情,眼前又盛开了洁白的栀子花,香气馥郁醉人。但不知怎的,楚当当的身影忽然闯进来。那天下午,他们坐公交车回家,当当先下了车,往前走了几步,忽然想到了什么,轻盈盈一个转身,双手握着背带,笑眯眯地看他,使劲地挥手,两条辫子一荡一荡。这个美好的场景,深深印刻在他脑海里,一想起来,心里就有几分甜蜜。但是他警觉了。
“我这是怎么了?难道真的移情了?”
他几乎看到了后果。葛怡将觉得他用情不专,从此一刀两断。而楚当当呢,也不可能接受,只会正色告诉他:“我不愿成为感情的替代品。因为心灵太柔弱,容易受伤,我要好好保护。”
不过,唉,感情的替代品,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一旦倾心过一个人,就成了犯罪前科,再也无法洗净?感情经过转移就会变质?当然,他想的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谴责。他希望自己的情感干干净净,就为了一个人而盛开。
唉,浮躁啊,浮躁,已经让他难以专情了。
他这样自相矛盾地想着,不知过了多久,在半睡半醒之间,他做了个梦。在梦里,他飞快地奔跑,几乎足不点地。头顶上有什么阴沉沉地压下,怎么跑也躲不开。然后,他似乎坐上一辆火车。火车极快地奔驰,窗外是平整的原野。天空是蓝色的,云朵也是醒目的。然而他很不安。果然,车顶一声巨响,一只长着黑色鳞甲的手穿透铁皮,撕开车顶,露出一个黑甲的怪物,一脸狞笑,就要跳进来……
他猛地惊醒来。一看时间,三点多了,曾泉的鼾声已停,单昀正在咯咯咯磨牙,只有陈子轩的床上一点动静也没有。再一看,陈子轩的床上没有人。莫非,陈子轩刚才趁着大家睡觉,又溜去教室用功了?
他心里一阵发急,更是难以入眠,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东方既白,然后一身疲惫地开始新的一天。
周末回到家,爸爸没有催他读书,倒是让他放松一下,去打个球,看个电影。
“读书也不在这一会儿。”
杨略却舍不得浪费时间,绕着小区跑了一圈,身上出了微汗,就回来了。坐在客厅里,打开电视,点播了一部电影。他是希望科幻乃至魔幻题材的,就点开了《永无止境》,而且一看就入了迷。
片子说的是一位作家,长期没有灵感,看着截稿日期越来越近,却毫无办法,脑子像一锅浆糊一样,打开电脑,却憋不出一个字,于是只好顶着油腻的乱发在街上乱走。谁想,一个机缘巧合,他得到一种神药,NZT,忽然心智大开,极度专注,灵感如滔滔流水,连绵不绝,转瞬之间,就写好了文章,而且还有余暇,将连狗窝一般的房间清理干净。此后,他就依赖上了NZT,有了它,他的大脑潜能全部被激发,随便听听广播就能学会各种外语,看看股市数据表顿时掌握了未来走向,更不用说天文地理无所不通。最后,他成为参议员,目标直指美国总统。可是,一旦没了药,他却无法集中注意力,精力涣散,头脑混沌一片。
爸爸从书房里走出来,坐在他身边。
“这电影讲什么的?”
杨略大概描述了电影情节,就开始感叹脑子不好用,专注力不够,记忆力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