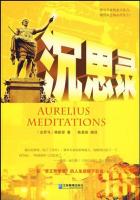弗洛兰和她的四个伙伴,在黑暗的丛林里急急地奔跑着,在他们身后,则是率领着两百个武士的陆美尼在紧追不舍。逃跑的五个人东冲西撞,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他们每个人都在想,希望离开阿拉伯人的村寨越远越好,因为即使不被后面的追兵抓住,被阿拉伯人抓住,也同样不能活命。他们往前跑了约有半个小时的光景,正想要歇一口气,忽然听得身后又有了脚步声,只好又爬起来,不辨方向地继续往前逃走。
跑了一段路之后,他们忽然看见前面,有闪闪的火光,心里不觉一惊,在这荒野里,这火光是从哪儿来的?难道自己跑了这么久,又兜回到老地方了吗?虽然这样狐疑着,脚下却不敢停住,还得继续往前跑。跑近了,终于看清楚了,前面有一圈用荆棘围着的地方,中间燃着一堆小小的篝火。圈子里面有五六十个黑武士,围坐在火堆边。他们走得更近些,才看清还有一个白人站在篝火的光亮能够照见的地方,那是一位白种女人。弗洛兰等人,听到背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那些黑人,也都脸朝着阿拉伯人营地的方向站着,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也在倾听不知从哪儿发出来的声音,从这个声音在推测将会发生什么事。接着那白女人做了一个手势,意思也是叫黑人们静听,这说明,她也听到弗洛兰等人的脚步声了。
弗洛兰对她的伙伴说:“我看到火堆旁有个白种妇女,我们虽然不认识她,但到底属于同一种族,说不定她能救助我们,目前看来也只有她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背后追咱们的人,已经快要到了,在这危急关头,也许她能保护咱们。来,我们就去找她吧。”她不等她的伙伴们回答,便直接向荆棘圈走去,克赖斯基等四人只好在后面跟着。
弗洛兰等人没往前走多远,那些目光锐利的瓦齐里武士已经看见他们了。于是他们拿起了长矛,在做着戒备。
有一个黑武士高声叫道:“站住!我们是泰山庄园上的瓦齐里人,你们是什么人?”
弗洛兰答道:“我是一个英国妇女。这些都是我的同伴,我们在丛林里迷了路,本来我们雇了一些守卫的人,没想到遭了他们的暗算。那些守卫,在他们头目的带领下,还在后面苦苦地追赶我们。我们这里,只有五个人,万望你们能给我们一些救助。”
琴恩对瓦齐里人说:“让他们进来吧!”
当弗洛兰等人走进琴恩和瓦齐里人的营地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察觉,在营地对面的一株大树上,正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们。那是一双灰色的大眼睛,猛一看,非常像泰山,在目送着弗洛兰和她的同伴,走进荆棘围着的营地里去。
等弗洛兰走近琴恩身边,琴恩大吃一惊,不觉失声叫道:“咦,你不是弗洛兰吗?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弗洛兰也同样吃了一惊,停住脚步,叫道:“我没认出来,原来是爵士夫人。”
琴恩继续说:“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到非洲来的?为什么不到我庄园上去呢?”
弗洛兰不觉愣了一愣,但马上接着说:“我和布鲁伯尔先生还有他的朋友们到非洲来,是为了搜集一些科学上的材料的。他们之所以叫我同行,是因为我曾经跟夫人和爵士到过非洲,比较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怎么也没想到,途中我们的奴隶会叛变,我们慌不择路,害得我们迷了路。如果不是遇到夫人,我们也许会死的。”
琴恩问:“后面追你们的人,是西海岸雇的脚夫吗?”
弗洛兰回答说:“是的。”
琴恩说:“他们一共有多少人?我想,我们的瓦齐里武士能够对付得了他们。”
此时克赖斯基插嘴说:“追我们的大约有两百人。”
夫人摇摇头说:“不怕,他们的力量差得远呢!”她转身吩咐瓦齐里武士的头目乌色拉,“有两百个西海岸的脚夫,在追赶这些白人,我们作好准备,必须用武力保护他们。”
乌色拉自豪地回答:“我们足以能胜过他们,因为我们是瓦齐里人。”
没过多大工夫,陆美尼带领的一帮人,已经到了篝火的光亮照得见的地方了。
陆美尼带领的人们,见前面荆棘圈里的人有所准备,不觉停住了脚步。陆美尼却没把瓦齐里人当回事,于是走上前来吵闹着,要他们把那些白人交出来。他的部下也跟着嚷着闹着,好像不打一架不过瘾似的。他们满以为自己这边二百人,足以敌得过圈子里的五十来人,他们却低估了瓦齐里人的厉害。
瓦齐里人在圈子里面静静地等待着,他们受过人猿泰山的训练,一点儿也不心浮气躁,非常沉稳,大有沉着应战,稳操胜券的架势。他们养精蓄锐地以静制动,等着敌人送上门来。
琴恩问弗洛兰等人:“他们手里有多少支来复枪?这种武器可是会给我们添麻烦的。”
这次又是克赖斯基抢着说:“别看他们人多,他们之中,会打来复枪的,不过五六个人。”
琴恩对这群白人说:“你们也都武装起来,加到瓦齐里人的队伍里来!你们不要单独离开,等他们攻过来,我们马上开火,要不停地放枪。我知道,西海岸的黑人,最怕白人的来复枪。我和弗洛兰就躲在营地附近的大树后面。”瓦齐里人听惯了琴恩的吩咐,爵士夫人的话在他们心里很有分量,他们都非常顺从她。那个肥肥胖胖的布鲁伯尔,虽然也站在了瓦齐里人的队伍当中,可是他的两条腿,却在不住地打战。
他们这些人的举动,陆美尼借着火光,看得清清楚楚,就连琴恩和弗洛兰躲在大树后面,他也看清楚了。陆美尼他们本来不是准备来打架的,他们是来捉弗洛兰的。他转身对他的部下说:“我看这圈子里只有五十来个人,要把他们都消灭掉,不是什么难事,不过我们的目的不是来打架的,我们是来捉那个白女人回去的。你们不妨就站在这里呐喊,时进时退,只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就行了。我悄悄带五十个人,绕到营地的背后去,去逮那个白女人,你们只管听我的暗号,到时候我会关照你们的。只要逮住了那个白女人,我们不做任何耽搁,马上回村去,我们的村落有坚固的木栅栏,到了自己的村落里,就十分安全了。即使他们追来,我们也容易抵御。”
陆美尼的这个安排,西海岸的黑人们都赞成,因为他们本来就没准备打架,如今既然可以不动武、不流血得到胜利,然后安然地回村子去,大家当然都十分高兴。因此他们就站在原地,叫喊得非常起劲。
陆美尼带着一小拨人,躲躲藏藏地爬到营地的后面,准备去捉弗洛兰。这时,突然从一株不太高的树上,笨拙地爬下一个白大汉来,正好站在两个白种妇女的中间。这人半裸着身体,只围着一张狮皮,闪闪烁烁的篝火光,正好照见他也算得上英俊的身姿。
只听琴恩惊喜地叫起来:“泰山,谢谢上帝!原来是你啊。”
那大汉把食指竖在嘴唇上,发出“嘘嘘”的声音,叫他们肃静,然后并不理睬琴恩,却转身对弗洛兰说:“我要找的是你!”只见他一把把弗洛兰扛在肩上。琴恩被弄得目瞪口呆,完全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她还没来得及过去拦阻,这个泰山早已跳出了荆棘圈,朝黑暗的丛林中奔去了。
琴恩简直被弄糊涂了,好像受了一个意外的打击,分明是泰山,泰山也不会没听见自己说的话,怎么会不理自己,反而扛上一个过去的女仆跑了呢?她呆愣愣地站在那里。接着她叹了一口气,软瘫瘫地坐在了地上,用双手捂住脸,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陆美尼和他的部下,偷偷钻进荆棘圈里,借着火光,在望着琴恩。由于琴恩捂着脸,看不清面目,所以把琴恩抱起就跑,朝丛林中他们的村落跑去了。
十几分钟之后,那四个白种男人和瓦齐里武士们,看着西海岸的黑人,呼啸着渐渐向丛林中退去,看他们那高声大叫,倒好似打了大胜仗凯旋一样。瓦齐里人被弄得莫名其妙,看这些黑人来势汹汹,原以为要打一仗的,没想到未动一枪一弹,就这样没头没脑地结束了。
克赖斯基抓了抓头皮说:“这群人忽而来,忽而又跑了,真不明白他们是干什么。咱们快找找,看夫人和弗洛兰在哪里。”
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两个女人都不见了。
瓦齐里武士们都急得跳起来,他们到处高呼着:“夫人!夫人!”可一直听不到回答。乌色拉急了,高叫道:“我们瓦齐里武士集合到一块儿来,就是拼死也要把夫人找回来。”说着,他们就跳出荆棘圈,去追西海岸那些黑人去了。
瓦齐里武士比那些黑人跑得快,不大一会儿,就望见他们的踪迹了。陆美尼手下那些黑人十分害怕,只向村落的方向逃去。瓦齐里武士高声呼喊着在后面追逐,吓得那些西海岸的黑人把来复枪和长矛都丢了,以跑得快些。陆美尼和他带的一小队人,跑在最前面,已经进到木栅栏里面了。他们等自己的人进完了,把木栅栏牢牢地关上,无论如何也不让瓦齐里人冲进来。因为他们知道瓦齐里武士只要一进来,自己的队伍远不是他们的对手,整个村落会寸草不留的。他们不但关上了栅栏门,还上了锁,这木栅栏建得很高,很牢固,易守难攻,这给外面的瓦齐里武士,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乌色拉见这样闹下去不一定会成功,便吩咐武士们暂时退下来,站在离栅栏不远的地方,看看动静再说。大家望着栅栏门,乌色拉想引诱敌人出来,这样比强攻省人力。他对部下们说:“我们今天的目的,只是为找到夫人,没有必要把这群黑人杀光。”
有一个瓦齐里武士说:“我们只管攻,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女主人是不是在这个村落里呢!”
乌色拉说:“这群黑人跑了之后,女主人就不见了,你们说,她能在哪儿呢?她一定在这个村子里。”他想了想又说,“不错,你说的也有点道理,不如我先去探查一下。我有一个计划,你们看,风是从对面吹过来的,你们十个人跟我来,其余的人留在栅栏门外,高声喊叫,装出要进攻的样子。说不定过一会儿他们会开门出来,到那时候,我会从里面出来,如果我没出来,你们就分开,排在栅栏门的两边,让他们逃走,不要拦阻他们。只须注意队伍中有没有夫人,如果见了夫人,必须马上把她夺过来。你们听明白了吗?”
他的同伴都点点头说:“好,就按你说的做吧!”乌色拉带了十几个人,向村落的后面走去了。
且说陆美尼,拖了琴恩走到离栅栏不远的一间茅屋里,然后牢牢地把她捆在一根柱子上。在黑暗中他也没看清楚,他满以为这个女人是弗洛兰呢。后来,他急急忙忙地离开了这里,朝村栅栏跑去,以便指挥他的部下,坚守这个村子。
这时屋里只剩下琴恩一个人了,她渐渐整理思路,思索一些问题了。刚才这一切都来得太突兀,变化太快,她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但唯独有一件事,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的丈夫泰山,从来没有这样反常过,当面临围攻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救自己,反而扛上一个另外的女人,往丛林中跑去了?她忽而想起乌色拉的话,泰山头部又受过伤,是否由于他记忆力尚未恢复所致?但即使想到这一层,她心里还是十分痛苦的,她低下头来,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带着极端痛苦的心情,被绑在一间污浊的茅草屋里伤心地哭,她好久都没尝到这种滋味了。
正当琴恩独自愁苦的时候,乌色拉正带着他十几个伙伴,沿着村栅栏,找到一个不太结实处,打开了一个缺口,从缺口外爬进了村子后面。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几堆枯柴,便把枯柴聚敛到一起,准备放火。
再回来说陆美尼,他跑到村庄栅栏边看了看,似乎没有多大危险,不愿恋战,想溜开自己去享乐一下。于是就命令黑人们守好村门,但要注意一点,如果瓦齐里人改变了战略,赶快来报告他。陆美尼吩咐完了,就匆匆朝囚禁琴恩的茅屋跑去了。
陆美尼是一个黑大汉,由于有一个疤痕,鬓角是歪的,下巴又非常突出,面容是那种又凶恶又丑陋的。他拐进屋来,点着一个火把,凝视着他面前低头哭泣的白种妇人。当他走到她身边,伸手要抚摸她的时候,琴恩抬起头来,他一看竟不是弗洛兰,而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白人妇女,他吓了一跳,立刻向后退了一步。
陆美尼仔细看看这白种妇人的脸,惊叫起来:“你是谁?”他用西海岸常用的那种半通不通的英语问。
琴恩说:“我是格雷斯托克爵士夫人,也就是人猿泰山的妻子。假如你明白道理的话,应该赶快放了我。”
陆美尼开始时露出非常惊疑的样子,但他还是没有打算放琴恩。他端详着她的脸,觉得她比弗洛兰更美,渐渐地,一股兽性,从他心里升腾起来。
陆美尼用他粗大的手,解开了琴恩身上的绑绳,琴恩见这个黑人贼头贼脑的,明显地不怀好意。等他把绳索完全解开时,用最快的速度跳到门口,可是没容她跑出去,一只粗大的手,又把她拦腰抱了回来。她使出平生力气,像一头雌兽一样拼命挣扎,陆美尼把她打倒在地上,把她拖到自己身边,这时候,陆美尼似乎已不顾一切了。村门外瓦齐里人的叫喊,村中也突然起了乱跑声和叫声,他都不顾了。可是琴恩虽然柔弱,但始终让他觉得很不顺手,她又抓又咬,使他感到很难办。
这时,在木栅栏背后,乌色拉已经把火把插入枯柴中,渐渐地,大约已经有六处在起火了。霎那之间,火光熊熊,烈焰腾腾,风借火势,火借风威,不大会儿工夫,村中好几处已经着火了,噼噼啪啪的响声越来越大。到后来,木栅栏也被烧倒了。果然不出乌色拉所料,村里一着火,木栅一倒塌,村里西海岸的黑人乱成一团,纷纷拼命地往外逃,并没有人指挥,不约而同地都往丛林里逃去了。瓦齐里人站在门外两边,留心着人群中有没有他们的女主人,可是,等到村子里的人都走完了,村子里也烧成了一片火海,他们瞪大了眼睛看,但自始至终,连琴恩的影子也没看见。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这些忠心耿耿的瓦齐里武士,还不死心,还在默默地等着,虽然他们知道,村里已经没有活着的人了。乌色拉最后才说:“看来夫人确实不在这里了。现在我们只有去追赶那些黑人,逮住几个人,从他们的嘴里,盘问出夫人的下落。”
他们追了一夜,到天色大亮时,他们才追到走得慢的一群黑人,这些人似乎走不动了,在那里歇脚。瓦齐里人把他们抓住了,告诉他们,乌色拉问他们什么,只要实话实说,就决不难为他们。
乌色拉问他们:“陆美尼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个西海岸黑人头目的名字,他还是在前天晚上,从那几个欧洲白人那儿打听来的。
黑人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离开村子时就没看见他,在你们围村子时,他指挥过我们一阵,后来就不知他去哪儿了。我们从前原是阿拉伯人的奴隶,后来才被这几个欧洲人雇了,陆美尼对我们很苛刻,甚至比阿拉伯人还狠,我们也不喜欢跟他在一块儿。”
乌色拉又问:“你们可曾看见,村子里有没有一个白种妇女?”
有的黑人说:“我们看见陆美尼拖着一个白种妇女。”
乌色拉问:“他拖走那个白种妇女干什么?你们可知道现在那个白种妇女在哪里?”
黑人说:“不知道。那妇女被带到村里来,被捆绑在一间靠栅栏门不远的茅屋里。此后,我们再没见过她。”
乌色拉看了一下自己的同伴,大家都露出担心恐慌的样子。
乌色拉对那些黑人说:“走,我们都回村子里去,你们也跟我们一块儿走,要是发现你们说谎骗了我们……”说到这里,他用手指在咽喉上按了一下,做了一个用刀子割的动作。
那些黑人导口同声地说:“我们发誓,真的没有说谎。”
他们急急忙忙地往昨晚逃出的村落里赶,可是等他们赶到的时候,一切都被烧光了,什么也没留下。
乌色拉走近冒烟的余烬问:“那个白种妇女可是被绑在这儿的?”
那个黑人说:“是,就在这儿。”说着,他大步走到栅栏门附近的地方,看那里躺着一个烧得焦头烂额的死尸,由于烧得太厉害,已经辨不出面目了。那黑人说:“你们要找的白种妇女,陆美尼就把她绑在这儿的。”
乌色拉和那些瓦齐里武士,都挤上前去看那具尸体,有人说,看尸体的身高,不像是夫人。乌色拉说:“尸体都烧得蜷缩起来了,怎么看得出来?夫人当时是被绑在柱子上的,她怎么跑得了呢?我看这多半是夫人了。”说着,背转身去,不禁掉下泪来。其他的瓦齐里武士,也都非常难过,平时,夫人一向对他们很好,他们也是素来敬爱夫人的。
有一个黑武士说:“我总觉得这不像夫人,说不定是另外的什么人。”
另外一个黑武士说:“这一点很容易弄明白,如果在残灰里,能找到夫人的指环,那就能确认是夫人了。”说着,他就蹲下身去,从灰烬中寻找夫人常戴的指环。
乌色拉失望地摇摇头说:“恐怕这多半是夫人,你们看,这不是捆绑她的柱子吗?”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即使找不到指环,也不能证明夫人没有遇难,因为陆美尼会把戒指抢走呀!夫人被绑在柱子上,想来,她万难有逃走的可能。”
瓦齐里武士们都肃穆地默立了一会儿,大家挖了一个坑,恭恭敬敬地把残灰捧起,埋了起来。并且在墓前立了一块石头,作为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