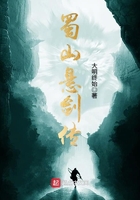当得·阿诺恢复知觉醒来时,他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柔软的草铺上。这张草铺的上面是一座A字形的小草棚。在他的脚下,是小屋的开口,可以看到前面绿草如茵的空地,而更远处却是由浓密的灌木和丛林构成的一道绿色的屏障。他现在行走既不方便,伤口又痛,身体也很虚弱。尤其是当他的知觉完全恢复以后,他浑身被拷打过的地方,现在也越发地疼痛起来。那些伤口、骨头和肌肉都有一种火辣辣的刺痛感,就是转一下头也会引起强烈的疼痛,所以他只好闭上眼静静地躺着。他尽量想拼凑出在他失去知觉以前的冒险经历,看自己是否能搞清现在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朋友手中还是在敌人手中。最后,他想起了他在那根火刑柱上的可怕情景,也最终记起了那个奇怪的白人,而自己就是在他强有力的臂弯中昏过去的。
现在得·阿诺不知道有什么命运等待着他。在周围,他既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丛林里不停的呜呜的风声、成千上万片树叶的哗哗声以及小虫的叽叽声、鸟声、猴子声似乎都融汇成一片安慰他的细语轻言,就像他躺在远处的某个地方,远离生命的世界,而这些声音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阵阵模糊的回音。最后,他又沉入了香甜的梦乡,一直睡到太阳偏西。他又一次醒来,再一次感觉到他早上醒时经历的一切。只是他很快地想到他现在是躺在一座小草棚里,就不由得向脚下的门口看去。这时他却看到在那里有一个蹲着的男人的身影。那个人宽阔的肌肉、丰满的脊背正对着他。尽管它是褐色的亮晶晶的,但那是一个白种男人的脊背是绝对不会错的。啊!感谢上帝,得·阿诺终于放下心来。
法国人轻轻地叫了一声。那个男人听到了,他站起来向小屋里走来。他的脸长得很英俊,得·阿诺觉得他甚至从来没见过这样英俊的人物。他弯下身子,爬进小草棚,来到受伤的军官身旁,把一只凉凉的手放在他的前额上。得·阿诺对他用法语说话。但他只是摇头,这对于法国人未免觉得有点悲哀。然后,得·阿诺又试着用英语跟他说话,但他仍然只是摇头。用了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都得到同样令人沮丧的结果。就连得·阿诺仅仅知道一两句的挪威语、俄语、希腊语以及他只是一知半解说不清楚的非洲海岸黑人部落的土语都拿了出来,但这位男子一概不懂。
在查看了得·阿诺的伤口以后,他转身离开了小棚,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一会儿,他从外面回来,带来一些果子,还有一个空的像葫芦状的植物,里面盛着清水。得·阿诺吃喝了一点。令他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发烧。接下来他又试着和他的这位护理交谈,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一切的努力都毫无结果。
突然,这个男子好像明白了什么,他又转身离开了小棚,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他手里拿着几片树皮回来了。可是令法国人觉得奇而又奇的是他手里还拿着一截铅笔。我的老天!竟然是一截铅笔!
他就蹲在得·阿诺的身旁,在树皮光滑的里面写了一阵,然后,把它递给了法国人。得·阿诺一看竟然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在树皮上竟然清楚地用相当规整的印刷体字母写着一段英文信息:“我是人猿泰山。你是谁?你能明白这种字吗?”
得·阿诺兴奋得立刻抓起了铅笔。但就在这时他又放下了。他想这个奇怪的男子既然能写英文,那他显然是一个英国人了。
“是的,”得·阿诺高兴地说,“我懂英语。我也能说英语。现在就让我们用英语交谈吧!首先我得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可是这个男子仍然摇着头,只是一个劲地指着树皮和铅笔。
“我的老天爷!”得·阿诺不由得惊叫起来,“如果你是一个英国人,怎么你现在还不会说英语?”
可怜的受过教育的文明人,他被语言学错误的基本原理欺骗了多少年,竟然不知道文字也是一种可以直接用来表达思想和交流信息的符号。所以,这时他忽然以为这个男人可能是个哑巴,或者是个聋哑人。所以,他只好也在树皮上写了几句英文。他写道:
“我是保罗·得·阿诺,法国的海军中尉。我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你救了我的命,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能写英文却不能说英语吗?”
泰山的回答却令得·阿诺越发地如坠云里雾中。泰山的答复是:
“我只说我部族的语言,我的部族是大猿喀却克的。也会一点吞特——大象的话,努玛——狮子以及丛林里其他动物居民的话。可是和人我却从来没说过。除了有一次和琴恩·波德打过手势。这是我头一次和我的同类,用文字来交往。”
看了这段文字,得·阿诺大为惊奇。这简直难以令人相信,居然世界上有一个发育完全的人,他却从来没有和他的同类说过话,而且更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却既能写又能认一种文字!
他又看了泰山写的那段文字。千真万确——“除了有一次和琴恩·波德……”,这就指的是那个被大猩猩掳走的那位美国的女士吧!得·阿诺突然好像明白起来,难道这就是那个“大猩猩”?于是他抓起了铅笔写道:
“琴恩在哪儿?”
泰山回答道:
“已经回到她的人那儿去了,在泰山的小屋里。”
法国人又写道:
“那么她并没有死?她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
泰山又写道:
“她没有死。她是被大猿脱克俘虏的。他想占有她。但是人猿泰山在脱克伤害她以前就把脱克杀死了。丛林里的任何动物都不敢面对泰山进行战斗。我就是人猿泰山——万能的斗士。”
得·阿诺继续写道:
“我很高兴她现在安全了。我现在身上疼痛,写不下去了。我要休息一会儿。”
然后泰山写道:
“好的!休息吧!等你好了,我再送你回你自己人那里去。”
有好多天,得·阿诺就躺在他柔软的草铺上。不过,从他们谈话的第二天起,得·阿诺就开始发起烧来。得·阿诺明白他是受了感染。他甚至想到他是不是要死了,所以他叫来了泰山,示意他要写字。泰山于是给他拿来树皮和铅笔。
得·阿诺写道:
“你能到我的人那里去,把他们领到这里来吗?我可以给你写一封信,你交给他们,他们就会跟你来的。”泰山摇了摇头,然后拿过树皮和铅笔写道:
“从你来的头一天,我就想过这事。但是我不敢这样做,因为这里是大猿们常来的地方。要是我离开很长时间去送信,他们发现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又动不了,他们会把你杀掉,当食物吃了。”
得·阿诺只好无可奈何地躺下去,闭上了他的眼睛。他不想死,可是他觉得他正走向死亡。因为,他发烧得似乎越来越严重。这天晚上他终于烧得昏了过去,一直有三天他就在神志昏迷之中。泰山一直蹲在他旁边,用冷水给他清洗伤口,给他擦头、洗手。到了第四天,法国人的烧来得突然,也去得突然。但是,这一场高烧使他虚弱不堪。这时泰山不得不离开他一会儿,去寻找食物,只好把一葫芦清水留在他身边。
其实,这一场高烧并不是像得·阿诺所想象的是某种传染疾病引起的。它只是非洲丛林里白人普遍会发生的一种水土不服。它要么会致人死命,要么就像在这个法国人身上那样突然消失。
两天以后,得·阿诺已经能在小棚外面的圆场上蹒跚走步了。泰山有力的臂膀时不时地要扶住他免得他跌倒。他们有时也坐在大树下,而泰山无意中也发现了几块光滑的树皮。于是他们就在上面对起话来。
得·阿诺首先写道:
“我怎样报答你对我所做的一切?”
于是泰山回答说:
“教给我说人的语言吧!”
得·阿诺立刻就同意了泰山的要求,开始了他的教学。他指着他们熟悉的东西反复地说着法语的名称。因为,他觉得他用自己的语言教这个丛林人更容易一些。当然,他对法语的了解比任何其他语言更完全。这对于泰山来说,当然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不可能再从另外的人那里学某种语言了。所以,当他指着画在树皮上人的样子时,他却学到了这个字的发音是HOMME (法语“人”)。同样地他也学会了人猿是SINGE,而树是ARBR E(均为法语)。
泰山是一个很好学的学生,只用两天多一点,他已经学会说一些短句子,像“这是一棵树”“这是草”“我饿啦!”等等。不过,得·阿诺发现在泰山原有的英文基础上教他法语有一定的困难。
法国人为泰山书写简单的英文课文,却让泰山用法语重复它。结果这种读音和书写分离的语文经常引起泰山应用它们时的混乱,所以现在得·阿诺才明白他已经铸成了一个错误。但是,如果再让泰山从头学起,就得抛弃他几天来所学的一切,特别是他们现在已经达到几乎可以较顺利交谈的地步,如果重新学习英语就太费事费力了。
到了他们开始学习以后的第三天,泰山写了一小段话,询问得·阿诺是否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壮,可以让泰山把他带回小屋那儿去。泰山和得·阿诺一样渴望到小屋那里去,因为他十分想再见到琴恩。仅仅为了这个理由,他觉得留在这里照看这个法国人已经是很不得已了。仅此一点已经足以表明他无私的性格了,照看得·阿诺恢复健康,甚至要比他到孟格村去搭救他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得·阿诺当然很愿意去尝试这样一次旅行了,不过他写道:
“但是,我怕你不能一直带着我穿过这样一片茂密的丛林吧?”
泰山大笑起来:“Mais%oui.”(“当然可以。”)泰山用法语答道。得·阿诺听了也大声笑起来。他自己的口头禅居然从泰山嘴里顺畅地讲了出来。
他们就这样出发了。得·阿诺也像克莱顿和琴恩一样,对这位人猿先生神奇的体力和敏捷感到惊讶不已。
下午四五点钟,他们已经来到丛林边缘的开阔地。而当泰山从丛林的最后一根树枝上跳到地上时,由于马上就会见到波德小姐,他的心不由得猛烈地怦怦跳了起来。但是,在小屋的外面什么人也看不到。而且,得·阿诺也迷惑不解地注意到,海港里不但看不见巡洋舰,“飞箭”号也没有锚泊在海湾里。
当这两位男士大步向小屋的方向走去时,一种死样的沉寂突然包围了他们。虽然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但是他们已经明白在他们打开那扇关着的屋门以后,他们会遇到什么。
泰山终于拔开了门闩,推开了那扇沉重的木门,屋子里正像他们暗自恐惧所预感到的一样,里面已经没有人了。这两位男士,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得·阿诺知道这一定是他的人以为他已经死了,所以才离开的。不过泰山想到的只是那位女士,她曾经吻过他,而正当泰山为救她的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她却不知去向了。
一种巨大的痛苦正在他心中升起,他真想远远地走到丛林的深处去,回到他的大猿部落里。他再也不想看到他同类的人了,甚至不想再见到这间给过他许多美好回忆的小屋,就连曾经使他殷切盼望过要见到自己同类并成为一个男子汉的心愿,也一并留在这里。
那么这个法国人呢?得·阿诺呢?他怎么办?尽管他能和泰山和睦相处,可是泰山也不想再看到他。因为,他想抛弃一切能引起他回忆起琴恩的人和物。
当泰山正在门前踌躇不决的时候,得·阿诺却一脚迈进了小屋。他看到这里留下了许多有用的生活用具。他认出了许多是巡洋舰上的东西,一只野营用的炉子、一些炊具、一支来复枪和许多发子弹、不少罐头食品、毯子、两把椅子、一张帆布床以及一些美国书和期刊。
“他们一定还会回来。”得·阿诺看了这些东西以后,这样想着。他走到约翰·克莱顿多少年以前作为书桌的木案子那里,在那里发现了两封写给人猿泰山先生的信,一封是一个男人的笔迹,没有封口;而另一封则是一个女人秀丽的笔迹,却封了口。
“这里有两封给你的信,人猿泰山!”得·阿诺大声说。可是当他走到门口时,才发现他的同伴已经不在那里了。他走出门口,东张西望了一阵也看不见泰山的影子。他大声地喊叫,也没有回应。
“我的老天!”得·阿诺叫了起来,“他把我撂在这儿了。一定是的。他又回到他的丛林里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然后他想起来,泰山看到小屋里空了时脸上的样子,就像一个猎人从他无意中弄到的麋鹿眼睛里看到的那种哀怨无望的神情一样。看起来泰山是受了一次沉重的精神打击,得·阿诺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可是究竟为什么?他还没法理解。
法国人现在看着他周围的一切,寂寞和对这块地方的恐惧,更加上刚刚过去的那一场痛苦和疾病的折磨使他疲弱不堪,都弄得他心烦意乱极了。
他独自一个人被丢在这座可怕的丛林里,永远听不到一个人的声音,也看不到一个人的影子。而且,他不断地处在对凶猛野兽和更可怕的野蛮人的恐惧之中,成为一个寂寞孤独和希望渺茫的牺牲品。
这时在西面的远处,人猿泰山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丛林的中部树枝间向前荡去。他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莽里莽撞地向他自己的部落跑去。他只觉得他好像要甩掉以前的那个自己一样,像一只受惊的松鼠似的在树枝间乱窜。他要甩开他自己的思想,可是无论他怎样飞跑,他的思想还是紧追着他不放。
当他正在一头慢慢向他的相反方向——小屋的方向——走去的狮子上面荡过的时候,他不由得想起,得·阿诺能抵抗一头母狮吗?或者要是遇上一头大猩猩呢?或者一头公狮,一只残忍的猎豹呢?
泰山突然停下了他的飞行。
“你到底是怎么了,泰山?”他大声地问着自己,“你到底是一头大猿,还是一个男子汉?”
“你要是一头大猿那你就像一头大猿那样,丢下你的同类在丛林里,任他是死是活,而随着你的狂想爱到哪儿就到哪儿去!你要是个男子汉,那你就该回去保护你的同类。你不能因为他们中的某个人的离去使你难过而丢下他不管。”
得·阿诺关上了小屋的房门,他的神经变得很紧张起来。即使是一个勇敢的人,得·阿诺当然是一个勇敢的人,有时也会对沉寂产生恐惧的。
他把一支来复枪装上了子弹,把它放到了易于拿到的地方。然后走到桌子边,拿起了那封给泰山的没有封口的信。他认为信里也许会说到他的人暂时留在海岸的什么地方,而且他认为这并不违背道德。所以,他从信封里抽出了信纸,读了起来:
致人猿泰山先生:
我们为使用您的小屋,特向您表示感谢。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没能见到您,并亲自向您致谢。
您小屋里的东西我们一点也没有损坏,相反却给您这孤寂的家中留下了可以使您生活得更舒适、更安全的一些用品。
如果您认识那位多次救过我们命、给我们送食物的奇怪的白人,并且能和他交谈的话,也请代我们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的好意。
我们一小时之内就要起航了,不准备再回到这里来。但是,我们希望您和其他的丛林朋友知道,我们将永远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为来到这片海岸的我们,这一群陌生人所做的一切。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会加倍地报答你们的恩惠。
谨致最大的敬意!
威廉·西塞尔·克莱顿
“再也不回来了。”得·阿诺嘟嘟哝哝地说。一面转身极端懊丧地扑倒在帆布床上。
一个小时以后,他忽然为一种声音所惊起。有什么人或东西在门边像是要进来的样子。得·阿诺一把抓过来那支子弹上了膛的来复枪,把枪托顶在肩上。
这时外面已经暮色苍茫,小屋里一片黑暗。但是,得·阿诺还能看到那门闩动了一下,他不由得感到头发都竖了起来似的。
门轻轻地被推开了一条窄缝,显出了有什么东西站在那里。得·阿诺顺着枪管瞄了过去,正对着门缝,然后抠响了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