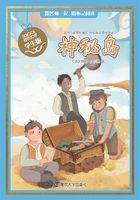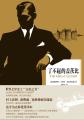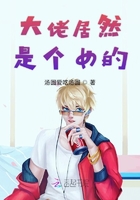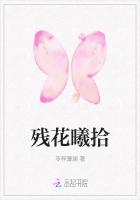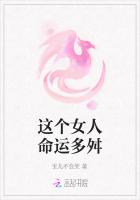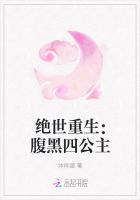某县教育局局长,应邀参加在西安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只有5天的会期却整整“研讨”了2个月,名为“学术研讨”,实为游山玩水。郑州、洛阳、西安是当然的必“游”之地,接着又南下成都,攀“蜀道”,游“三峡”,然后飞抵桂林,泛舟山水甲天下的漓江,又绕道广州、深圳,感受沿海城市的开放气息,最后在西子湖畔、沧浪亭边“研讨”结束。一次研讨会,行程几万里,游览大半个中国。一趟下来,数万元花销理所当然地全部报销。其行为不仅法律无奈,就是财政、审计部门也都全部认可。
这种消费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会议接待消费。除了大型会议在规定场所开以外,一般的中小型会议或出席层次较高的会议,大都选址在宾馆酒楼。某市主办了一次“经济发展恳谈会”,选择了当地惟一一家五星级宾馆。与会者住高级房间,吃高标准伙食,往来经费由会议悉数报销。会议所发的高级纪念品全打在会务费中,一个只有40多人参加的为期3天会议,花费了20多万元。二是交通通讯消费。有了小车还要配豪华轿车,有了电话还要配3G手机,公车私用,私客公请,个人消费,单位报销等种种行为渗透到领导层的生活方方面面。如某区1995年开支电话费30万元,2000年开支增加到100多万元。有一个单位规定:领导配车一辆,手机一部,室内装空调一台,真皮沙发一套。一家不足3000人的公司,领导拥有轿车12辆,3G手机32部,18部电话,每年养车费和通讯费支出高达20多万元。三是公款吃喝消费。某电厂厂长,吃喝玩乐,出餐厅、进舞厅,一天一个醉,一年挥霍公款100多万元,把一个好端端的盈利电厂搞成亏损上百万元的困难企业。有一个单位,一年中仅出国考察费开支高达1000余万元。某市财政局局长去世,财政拨款10万多元,动用轿车、面包100多辆为他办丧。其中为死者购买高档寿衣花去3.2万元,一顶帽子1.5万元,手表3860元,西装领带2600元,皮夹克2528元,腰带1588元,一副眼镜903元,派克金笔613元,文件夹366元。令人闻之瞠目结舌。
权力消费客观地讲有其必要和合理的一面,但失控的、过分的权力消费必然产生种种弊端。一位县级领导干部实事求是地算了一笔账:国家每月付给我的工资不算,还专门给我配备了轿车、司机、手机、电话和优越的办公条件。这样算起来,我个人消费的水平并不比西方国家公务员的消费水平低,应该很知足了。而那些许许多多被曝光官员的腐败劣迹,无一不和贪婪的权力消费相关,它向人们昭示了滥用职权挥霍公款的腐败悲剧。
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权力消费,既是对社会财富的流失,又是对社会成本的叠增,还会带来社会意识的蜕变。对于权力消费所产生的腐败现象,已经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领导同志在中纪委会议上指出:“讲排场、比阔气、挥霍浪费的现象,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盛行起来,一些人沉迷于物质享受,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令人触目惊心。”
向权力消费腐败宣战的警钟已经敲响。
第四节 买官卖官——人事腐败
“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使用。”这是人们对现代官场上不正之风的讽刺与抨击。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这是封建社会留下的一个“买官鬻爵”的腐朽“传统”。
两个时代不同,但买官卖官的目的是一致的——为一已之私利,追求一本之万利;性质是一样的——丑恶、贪婪、腐败。对此,老百姓深恶痛绝。
组织人事方面的腐败之风,不可小视。
从一首老民谣看买官卖官
“三千雪花银,一个红顶子”,这是满清政府的腐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丧权辱国的巨大灾难。如今跑、要、买、卖、骗风行官场,情谊无价,官衔有价,存在着明显的人治色彩。
1934年在修《临清县志》中,在其“谣谚”部分载有几首民谣,这些民谣“感怀时事,发为心声,词虽鄙俗,意在讽劝”,其中一首如下:
咸丰坐了十年半,顶翎赏了一大片。说他是文科,未曾把书念;说他是武科,不识弓和箭;说他是军功,与贼未见面。回家去祭扫,把他祖宗吓了一头汗:我的儿,咱家没有文武学,哪里来的凤凰蛋!
据史书记载,清朝中叶,特别是咸丰年间,面临内忧(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与外患(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军费不足,国库亏空,吏治日趋腐败,公开推行捐官(捐款授官,实际是用钱买官)制度。当时规定,除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优伶等不得捐官外,其他人只要有钱,都可以买到官职。出钱少的买小官,买虚衔;出钱多的买大官,买富官。由于捐官靠的是钱,所以,大量有钱而无能的人当了官,财主少爷、纨绔子弟,即使是酒囊饭袋,只要有钱,就可捐个官做。这首老民谣所讥讽的正是当时这种情况。
品味着这首老民谣,不由得看到当下的买官卖官的现象。本世纪之初,有媒体披露,中纪委查处了一些地方的极少数人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上买官卖官的案件,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反响。但事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震慑作用,买官卖官现象逐渐呈蔓延扩大之势。极有意思的是,如今的“官市”还非常繁荣。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导干部在“领导即服务,当官即公仆”的幌子下,干着同封建官僚一样的卖官鬻爵的营生,送大钱的当大官,送小钱的当小官,不送钱的当不了官,以“肥不肥”为标准,按质论价,一点都不含糊。
广西合浦县原副县长甘维仁,送给成克杰23万元,当上了广西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安徽阜阳市市长肖作新在卖官上有严格的“官价”,一般科局级5万元,要害部门的“一把手”10万元,乡镇党政“一把手”灵活掌握,视该地的经济发达情况而定,经济好的,官价高一点,经济差的,官价低一点。有一个个体户,想过过“官瘾”,多捞一点钱,送给肖作新20万元,结果跃身变成公安局的官。浙江省平阳县组织部长董根顺,官当4年,卖官收贿171万。而那个肖作新在任市长17个月里,通过卖官等方式,受贿人民币116.4万元,港币5万元,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钱,居然达到1223万元。
“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要四五万。”这是山东省泰安市群众给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卖官画的相。胡建学在任泰安市委书记5年间,利用干部职务晋升和调动之机,以钱封官,以钱定职,先后收贿人民币100多万元。
山西省汾西县委书记郑泽生,提拔使用干部,惟钱是用,从不顾及社会影响。他拿共产党的官位当商品卖。“五百挂个号,一千报个到,一万拿顶帽,要想得官位,再加5000元……”。贪污分子孟永明用巨款收买了郑,点名要当县反贪局局长,郑泽生力排众议竟让孟如愿如偿,把反贪局长的位子卖给一个大贪污犯,可算是天下一大奇闻。
在将贪官送上审判台的罪状中,总离不开卖官这一条。然而,在“东窗事发”后,这些家伙受到的惩罚都是极其严厉的,有的甚至送上了断头台。对这些受到惩罚的贪官,人民的态度是:活该,怎么惩罚都不解心头之恨。”
咸丰年间的买官卖官,是由当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自上而下公开进行的。而今天的买官卖官,为党纪国法所不容,是少数人偷偷摸摸所为,是见不得阳光的丑行。但两个时代的买官卖官者目的是一致的——为一已之私利,追求一本万利;性质是一样的——丑恶、贪婪、腐败。所以,老百姓对买官卖官现象深恶痛绝。
变了味的“集体推荐”
把跑官要官穿上“合法”外衣,冠以“集体推荐”的名义,这是新时期“官市”普遍推崇的一种作法。这种变了味的集体推荐,实际是集体跑官要官,其行为比起个人跑官要官有着更大“欺骗性”。
这种集体跑官要官的基本方式一般分三步走:第一步考察前集体推荐。他们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能够“严格”按照民主推荐的原则,确定共同相中的对象,认认真真走过程。第二步考察中集体夸功。表现为组织人事部门在分别谈话时,上下都能从德、能、勤、绩方面用共同的褒奖、共同的语调,甚至相同的语言为候选人贴金。第三步考察后集体说情。这是一段难以把握的过程,这段时间,单位集体中会选出至少两名擅长“攻关”的人物,上下活动,融通感情。
通常情况下,集体跑官要官可以分为3种类型:一是集体小团体利益的驱使。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有着一定权力的单位。在与同级单位的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过程中,他们希望多出几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关键时刻为他们遮风挡雨,于是上下齐心,合力共推。二是单位一把手亲自操纵,指挥全盘。主要领导先培养好候选人,然后在单位进行操纵,大多数干部及工作人员抱着不得罪人的态度,听由其变,认为谁上谁下与自己都关系不大。三是个人精心运作的结果。随着个人跑官要官遭到挫折和失去市场的境况下,开始变通形式,走“合法”的道路,通过各种渠道在单位内部上取悦领导,下融通同事,造成有利于自己的局面,形成一边倒的态势。
通过剖析集体跑官要官,不难看出3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具有安全性。从形式上说经过了“集体研究”,从制度上说“符合原则”,从过程上说“名正言顺”,他们心里都装着责任集体承担、个人不担风险的侥幸想法,心安理得,高枕无忧。第二具有隐蔽性。在整个过程中,大都以“群众路线”掩人耳目,拿“群众同意”为说词,不易出现漏洞与破绽。第三具有强制性。倘若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在以后工作中会以种种理由推托,不予配合,甚至设障,以此施压。
集体跑官要官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任其发展,必然败坏党风,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贻误事业的发展,必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予以制止。
集体跑官要官之所以萌发并蔓延,是因为少数领导认为这是公事公办,不会违纪违法。实际这种行为依然破坏了党的组织路线,是任人为亲,权钱交易的伪装形式,是谋小团体之“公”,损人民之“利”的腐败行为,本质上仍然是以权谋私,理所当然应予以禁止。
事实证明,集体跑官要官一般由一把手发起并组织,剪断这只黑手也必然从一把手抓起。对单位一把手的选配要重德才、强监督、立制度。做到强化思想教育,使其不想为;加强行政监督,使其不能为;建立健全制度,使其不敢为。大家不会忘记,在当年赖昌星的红楼里,众多的公共权力部门的首脑,陷入一种“冬眠状态”。赖昌星满足他们的欲望,也就牢牢控制了他们良知和责任的闸门。权钱在交换,欲望和责任也在交换。在集体犯罪中,个体的安全感存在于“大家都这样”的假设之中。可以想象,与这样安全感相伴,势必还有一种永远都挥之不去的恐惧感,就算你枕着价值千万元的枕头,恐惧都无法消失。所以,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向腐败。
好处是个人的,责任是集体的,是导致集体跑官要官的根本原因之一。某市一个体户,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梦想当大官。市领导为把他手中的40万元弄到手,既有人帮他入党,又有人帮他转干,还有人帮他虚报5年党龄,在拉他当上市经委主任以后,担心露馅,又有人帮他办调动。如此庞大的“集体腐败群”令人为之惊叹!对这样的腐败群体,必须分清主次、轻重,对症下药。严厉惩处,要把板子打到“出馊主意的人”、“把关定向的人”和“冲锋陷阵的人”的屁股上,使其不敢为所欲为。
变了味的“集体推荐”,说到家就是“集体腐败”。
买卖兴旺的“官场黑市”
买官卖官的现象在不少地方屡禁不止,且呈上升趋势。官职有大小,价格有高低,地区有差别,不同行业还有长线、短线之分。市场买卖的那一套几乎都搬进了官场。
由任人唯亲,跑官要官,发展到买官卖官乃至骗官,成为现代“官场”上的一个并非鲜见的怪象。有人戏言“官场黑市”。
“官场黑市”,这一见不得人的权钱交易,是不用商检、不用报税的黑生意,是没有机床、没有烟囱的黑工厂,是封建社会“卖官鬻爵”的沉渣泛起。
一般来说,做买卖需要成本,即使是小买卖,也须先投入一定的本金才能进货,然后,再以高于成本的价钱出售。生意不大,但也得报税,除去这些费用,你所赚的钱,才是你的利润。然而,有些人则把做生意这一套带到党内来了,他要做的生意就是拿钱买顶官帽子,并且有人凭此而达到目的,当上了手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即然官是买来的,就要投入本钱,那么,他是决不会做赔本的傻子。他不仅要捞回本钱,而且还要赚回一大笔利润。这是符合逻辑的推理,事实也正是如此。
买官卖官因为见不得人,通常情况下是极为隐蔽的,多为直销,很少有中介组织插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官卖官的投入产出比很高,比较效益极佳。市场上“一本二利”就算暴利了,而在官职的买卖中,却是“一本万利”。或许连本钱都不用,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无本万利”,买官者便轻易而举得到一顶官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