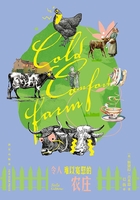胡卫东见甘薯花没喝,端着杯子等着,两眼端详着她说:“敬酒要干了。不干杯怎算敬呢。”
鲁反修夏瓜蒂齐劝道:“薯花,干了,干了。”
甘薯花心慌意乱,一张口,把酒倒进去。
甘薯花一盘酒下肚,脸成了红布,显得更加妩媚。夏八斤又给她添酒,她捂着酒杯说:“不喝了,我要回家。”
鲁反修说:“你还没敬我一杯酒呢,咱也是第一次喝酒。”
甘薯花泥:“鲁主任,我真的不敢喝了,用水表示吧。”甘薯花端起一茶碗水。
鲁反修不碰,说:“薄情薄意的,用水哪算敬呢。”
夏瓜蒂说:“敬了县领导,不敬公社领导哪能行呢。就一小杯,薯花,敬。
年轻可怜的姑娘,怎能经受住这群老狼的折腾,强忍着火烧火燎的难受滋味,又一口倒下去。她放下酒盅就往院子里跑。
洪薯仙示意夏八斤跟出去。
甘薯花捂着嘴,坚持着走到墙角吐起来。吐完了,抹抹了眼泪,转身欲走。夏八斤从背后抱住她,两手捂在甘薯花耸起的乳房上。
甘薯花用力踹了他一脚,厉声说:“放开!我喊人了。”
夏八斤怕街上有人听到,又拉住她的手,说:“屋里再坐会吗。”
甘薯花手一摔,捂着脸跑出门。
胡卫东:“八斤就看上了这姑娘?”
洪薯仙:“是啊,整天恋得神魂颠倒的。”
胡卫东:“八斤有眼力,不错。找人介绍过?”
洪薯仙:“介绍过。她爹还愿意,只是她本人恋着本村的那个仲地瓜。”
胡卫东:“凭我们这样的条件,啥样的姑娘还不接上八条腿往这跑。鲁反修夏瓜蒂,这事就包给你俩了口必要的时候,可用经济的,政治的,行政的手段做下作嘛。”胡卫东说完,义举起杯,“束,为八斤的婚事,我敬你们俩一杯酒。”
三人一饮而尽。
趁洪薯仙拿饭的空当,胡卫东跟了进去。
洪薯仙说:“八斤的婚事,委托给鲁主任和夏瓜蒂一定能成,人党提干的事,你也要费费心。”
胡卫东:“这事我考虑过了,若不是那件事,现在早就提拔成公社领导了。但,不能操之过急,须慢慢来。”
洪薯仙:“事情过去多年了,村里也没人知道,再不安排就晚了。”
胡卫东:“听鲁反修说,那女孩还没结婚,如果现在安排了八斤,她知道了,又会缠他。过段时间再说吧。”
洪薯仙像当年第一次亲吻胡卫东一样,两手把他揽进怀里,皱巴巴的双唇寻找着当年的感觉。
二十二
谷雨前后,种瓜埯豆。
过了谷雨,天就慢慢的转暖了。润物细无声的小雨,随风潜人夜过后,地里湿润润的。太阳一照,雾气升腾,形似奔岛。
杏花桃花相继凋谢。坡里的野花,这儿一片红,那里一片黄,柳树杨树抻开嫩绿的枝叶。欢快的鸟雀唧唧啾啾地在树林间田野里欢蹦乱跳。
地瓜庄处于胶东半岛东部,昼夜温差大,早中晚气候变化明显。
谷雨前后,是这里断霜的时间。有清明断雪不断雪,谷雨断霜不断霜之说。断了霜,芽瓜就可以栽了。
各家畦的地瓜种都长出了六到七片叶子。叶子由黄变绿,叶梗由绿变红,进入栽培的最佳时机。昨晚记工时,夏八斤就做了安排。要那些地瓜芽壮的户,第一次可以多拔点。苗弱的不要,长壮了再拔。早饭前送到仓库门前,由保管员田薯根和会计田薯豆查棵数。
天还不亮,仲地瓜就起了床。点上煤油灯,给瓜蛋掖了掖被子,让他再睡一觉。瓜蛋嘴里不知嘟囔着什么,咕咚翻个身,又睡过去。望着瓜蛋睡梦中那副调皮的样子,仲地瓜笑了。
仲地瓜将一张木板横端在窗台与砖围墙上,双腿在木板上蹲着,食指拇指中指并拢,挑那些叶大梗粗的拔。一边拔一边数着棵数,每五十棵用泡软的莛杆裤裤扎起来。
仲地瓜无论干什么活儿,仔细,认真。在地瓜芽竹理上费了木少心计。他买来了一支温度计挂在墙壁上,一天三时看温度。温度低了,堵窗,叫娘多烧火。温度高了,开窗,少烧火。由于温度适宜,湿度合适,地瓜芽发得多,长得壮。
仲地瓜心胸比较开阔,虽然他与夏八斤有矛盾,打心里鄙视夏八斤那种傲慢气,浪荡相。他却认为,活不是给队长千的,更不是给夏八斤个人干的。而是给集体干的,给社员们干的,也是给自己家干的。从来不拿农活使气,他干的活让夏八斤挑不出毛病来。这一点,他遗传了仲长蔓的基因。无论和别人闹矛盾或是吵架,过了火心头该说话的说话,该一起干活的一起干活。不像有的人,吵一次嘴半月二十日的不说话,打一次架记恨一辈子,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男子汉嘛,是是是,非是非,摆平就行了。他知道夏八斤在安排农活上有意挤兑他,他不在乎,也不吝啬力气,安排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是队长吗,安排的活你不****不干,总得有人干。
长蔓婆看到儿子那间亮了灯,知道他起来拔地瓜芽,就走过去。
仲地瓜:“娘,你再睡会吧,我自己拔就行。”
长蔓婆:“如果薯花家不够,能多拔点就多拔点,给她家顶顶帐。”
仲地瓜:“先拔够咱的再说,早完成任务,余下的自留地里还栽,再多了可以到集上卖。”
长蔓婆:“是这个理。不过薯花家完不成任务,咱也不能卖。”
长蔓婆站在炕旮旯里拣边上的拔。日光斜照在右边第一根窗棂上,收地瓜芽的钟声响了。仲地瓜把拔的地瓜芽数了数,凑齐了一千棵,放进篮子里提着,往仓库门前送。
仲地瓜送过去的时候,有几家已提前送过去了。不过,提前去的几家都拔得少,三百棵四百棵的。田薯根又叫了甘薯萍田薯叶块儿数。一边数,一边把发黄的弱苗病苗剔出来。
甘薯萍田薯叶把数好的地瓜芽一捆一捆地在水缸里淹一淹,空空水,放进偏篓里,用湿麻袋盖好。这样上午栽不完,下午可以继续栽,不至于因时间长发蔫。
仲地瓜拿来地瓜芽,田薯根让仲地瓜帮着数别人家的。
仲地瓜问:“你们相信我?数码了咋办?”
田薯根:“数多了归公,数少了你赔上。”
仲地瓜:“应该数少了归公,数多了赔上。”
田薯根寻思了一会,对,五十棵数成一百棵,队里吃亏,一百棵数成五十棵,队里沾光。到底是中专生,帐码头比我强。于是笑着说:“噢,摘了帽子尿尿,算倒把账了。”
在场的人都笑了。
仲地瓜专心地数着,甘薯花提着地瓜芽来了。
甘薯花看见仲地瓜在那里数地瓜芽,未等说话,脸先红了。甘薯花今天见到仲地瓜脸红的原因不是激动,而是心虚。在夏八斤家喝酒,被夏八斤摸了奶,心中的难言之苦压的她抬不起头来。她回家趴在铺上哭了很长时间。这种事既不便与娘说,又不能让仲地瓜知道。如果仲地瓜知道她在夏八斤家喝酒被夏八斤摸了,会做何联想。不与他实话实说,又觉得欠了他什么。她曾发誓把一个纯洁的身子给仲地瓜,被夏八斤摸了还算纯洁吗?她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见到了仲地瓜就心虚,就脸红。有时故意躲着他,懒的和他说话。仲地瓜也有些察觉,还以为老窝瓜对她俩的事从中打横的原因呢。
甘薯花把地瓜芽往地上一放,说:“薯根哥,我家的地瓜芽长得不旺,只拔了三百棵。”
田薯根:“仲地瓜拔得多,叫他给你家顶上二百棵。”仲地瓜:“田薯根,你真说对了。我拔了一千棵,给薯花家记上三百二百棵都行。”
甘薯花越发心虚脸红。说:“不用不用,俺下次多拔。”
田薯根:“客气什么,过几天连仲地瓜都是你的了,何差几根地瓜芽。”
说的大家笑起来。
数完了甘薯花的,仲地瓜让田薯根数他家的。田薯根说:“你家的不用数。”
仲地瓜:“为啥?”
田薯根:“我信得过你,看看这一偏篓地瓜芽,哪有你家这样壮实的。
听了对仲地瓜的夸奖,甘薯花心里既高兴,又生出一种无端的忧伤。
栽地瓜这种农活,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一项工序繁杂的营生。打起垅来后,栽时要经过捣埯、浇水、撒蔓、埋埯四道工序。加上运蔓的,挑水的,费工费事费力。因而每年春地瓜栽培季节,村里集中时间,集中劳力,集中工具,男女老少齐上阵,大人孩子都上坡。
捣埯也叫捣碗。将锄头倒过来,锄刃朝上,用锄钩子往地瓜垅顶上捣。捣出的穴,口大底小像个碗。捣埯是个技术活,选一些有经验的老庄家把式捣。两手一前一后握着锄杠,一副拿枪的架式。斜着身子呈45度角,走猫步。捣出的埯大小一样,深浅一样,距离一样。如果捣得不均,埯深了,浇水多。栽地瓜时水渗不下去,埋上地瓜芽容易泥僵。地瓜芽周围干成一块“碗轱辘底”圆,地瓜芽不扎根或锄地瓜时把“碗轱辘底”连同地瓜一起揭起来。埯浅了,浇水少,风一吹,干得快,成活率底。捣得密了,地瓜蔓长起来透光透风不好,养分供不上,结的地瓜小而少。捣得稀了,密度达不到,减产。捣埯又是个累活,一个姿势,一种步伐,扭着身子,半弯着腰,力气用在两只胳膊上。捣不一会就腰酸背疼,浑身冒汗。
挑水的要选仲地瓜这样的个子高有力气的劳力。水从白沙河底往上挑。河坡上斜着挖一条小道,挑着水桶爬坡时,前高后底掌握平衡。一不注意,前面的水桶碰到河崖上洒了,空桶和担子撅到天上去,后桶的水也保不住,就要到河底另挑。挑到地里一步一个地瓜垅的迈。步子小了迈不过去,个子矮了担不起水桶。担水也是个累活。
浇埯,撒蔓是栽地瓜中最轻快的活儿,年老体弱的或小学生都可以干,把水舀到埯里。撒蔓的要沿着地瓜垅右面朝向阳的方向把芽撤到埯里。
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栽芽埋埯。这里面也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人们蹲在地瓜垅的右边,左手拿起地瓜芽,右手食指、拇指、中指呈执笔状,捏住地瓜芽根部搬进泥里,用两边的土埋平,两只手在垅上一拍,再收上干土埋住湿土,起到保墒作用。
地瓜芽留在垅外的叶片,四到五片为宜。过高招风,地瓜芽嫩容易摔打油烂,过低,外面叶片少,生长不旺。
生产队里干活,格外热闹。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一起干着活相互咂牙说笑。张家长,李家短,三只家猫六只眼,絮来絮去的没完没了。正经的话讲完了,自然就换上裤腰带以下的。调皮的男人不时的与爱闹的女人动手动嘴。地瓜油是鳞刀鱼头一轱轳。埋地瓜时社员们面东背西弯着腰一人一垅由北往南埋。地瓜油有意识地选在黑面包后边。年轻的姑娘媳妇内衣扎在裤腰里,以防弯腰时露出皮肉。黑面包却不在乎,扎在腰里不透风,热燥燥的老出汗,就把衣服挣在外面。撅着屁股埋地瓜时衣服簇到背上,两只鞋底****一半垂在衣服外。地瓜油一边埋地瓜一边透过黑面包双腿间欣赏,他看着看着竟然忘了埋地瓜。
地瓜油是个完整的男人,他不是不要女人,而是说不上,又没有女人喜欢他。天天用嘴给自己过年。找那些爱闹的女人闹一闹,占不着大便宜,却能寻找点刺激。
地瓜油的一举一动被身后的田薯芹看得一真二切。田薯芹大声喊黑面包:“玉美嫂,玉美嫂。”
黑面包只顾埋地瓜,听到喊声问:“啥事?”
田薯芹说:“把你那两大件藏起来,别让你身后的馋猫叼了去。”
黑面包回头一看,见地瓜油在那儿直着眼看。黑面包:“地瓜油,馋了给你奶口。”
地瓜油:“好,拿来吧,你当我不敢奶。”顺手抓了把土扔进黑面包的衣服里。
黑面包起身去追打地瓜油。地瓜油漫着地瓜垅跳到甘薯花身后。黑面包指着地瓜油说:“你等着,歇息的时候盖你的土地庙。”在后面检查质量的夏八斤呵斥道:“地瓜油,干活时间,胡闹什么?看你埋的地瓜,二猫抓得似的。”
地瓜油知道夏八斤是因为他与黑面包闹的原因,一声不响的回到自己的地瓜垅上。
黑面包回头低声的对地瓜油说:“有本事你去看看甘薯花的,那可真好看。”
地瓜油:“没结婚的是金****,结了婚是银****,像你这样的生了孩子就成了狗****了。”
黑面包:“啥样的你也捞搔不着。”
地瓜油:“你那狗****谁稀罕。”
黑面包趁地瓜油说话没注意,屁股往后一撅,朝他脸上“咚”地一个响屁。地瓜油抬手在她腚上摸了一把。
黑面包:“地瓜油,臭不臭?”
地瓜油:“响屁不臭,臭屁不响。不过你这屁一股子驴屎蛋子味。”
黑面包:“放你娘的狗臭屁。”
地瓜油:“哎,黑面包,刚才这一举动,我想起一个故事。”
黑面包:“又要狗嘴里吐象牙?”
地瓜油:“这故事不骚,你可能听说过,有句歇后语叫坏地瓜家糊饼子——早怎么样还怎么样。知道什么意思吧?”
黑面包:“歇后语我听说过,里面的故事不知道。”地瓜油抬眼看了看其他女人说:“大家都听着,我讲给你们听听。”
早年,地瓜庄有个外名叫坏地瓜的,出地瓜回来看到刚过门的儿媳妇往铁锅上糊饼子。灶里的火着着着着掉了出来,儿媳妇两手面子顾不得往灶里填。坏地瓜就蹲下来帮儿媳妇烧水。儿媳妇弯着腰撅着个******,坏地瓜把脸歪在一面,假装不好意思看。可是,又忍不住看了一眼。儿媳妇穿了一条又瘦又薄的新裤子,后面的裤缝勒进屁眼里。糊饼子时转来转去很别扭。儿媳妇认为公公摸她屁股,脸一变就骂起来。骂得很难听。骂公公不正经,是骡子是鳖。坏地瓜觉得很委屈。好心当成驴肝肺,生气地说,好,早怎么样还怎么样。食指往嘴里沾了一下唾液,顺着儿媳的屁股用力一抿,裤缝又夹了进去。
黑面包听了笑得一腚镦在地瓜垅沟里,裤尿湿了一大片。
周围的女人也笑的前仰后张的。大家都说,这是地瓜油吐出的第二颗象牙。
黑面包笑声未息、听到儿子夏土豆的哭声,走过去,问儿子哭什么。
夏土豆说仲瓜蛋欺负他,把他手里的鱼夺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