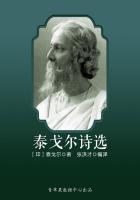我们村是库区移民村,几十户人家坐落在山上,房子都是由国家统一盖的,一排一排,虽不高大,却整齐划一,干净整洁。建村的时候,父亲也就是十几岁。在那个村子里,我度过了贫寒却快乐的童年。
村子在山上,出门几十米就有大片的松林和沟壑,我七八岁的时候,就主动承担了拾柴草的活。下午一放学,我们呼朋引伴,拿着小筢和篓子,唱着儿歌上山了。说是拾柴草,其实是为了打闹。我们爬上松树扮“日本鬼”,趴在小沟里捉迷藏,男孩给女孩蒙上红头巾“过家家”,我们笑啊,闹啊……不知不觉间,太阳就下山了。娘站在村头喊我,我一看篮子里的草还不到半截,只好折几块鲜松树枝垫在篮子底下支撑支撑。娘见了并不责骂,还摸着头说我长大了,能替家里干活了。
春天,山上和沟里到处是青青的野草,我们那里家家养牛,我除了拾柴禾,还特别爱放牛。把牛往树桩上用长绳子一拴,自己就坐在山坡上看书,各种连环画,还有哥哥买来的名着都是放牛的时候看的。那实在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老牛静静地反刍,我有滋有味地翻书。
夏日的雨后,会出现一种黑色的飞行小动物,我们叫它“水牛”。“水牛”比知了小一点,用盐炒了是一种无上的美味。一下过雨,小孩子们就拿着针和线到山上拾“水牛”,一只一只用针线穿成一串一串的。“水牛”大多在地上爬行,也有在空中飞的,我们从来不肯放过一只“水牛”,一边喊着一边跟在它后面奔跑。有时候,为了追上一只会飞的“水牛”要跑半里路,把凉鞋都跑断了带。
到了秋天,山上到处结满了野山枣,一颗一颗,红红的,又酸又甜。大人孩子人手一个篮子去采山枣,不是为了吃,是为了搓出枣核卖钱。在那个年代,一斤干枣核能卖一块钱。我经常拿着篮子跟娘走到几里外的仙山上摘山枣,渴了就挖沟里的沙子,渗出水就用手捧着喝。别看娘体弱多病,可是手脚麻利,摘的山枣在村里是最多的。各家各户都会把山枣放在锅里煮熟,拿到村东头的湾里放在石头上搓,再在水里冲干净,晒干后就可以拿到集上卖了。那些可爱的枣核最终会变成我和哥哥崭新的小书包、漂亮的塑料凉鞋。
冬天,我们的学校都是靠烧松球取暖。山上的松树上结满了累累的果实,在树上时青青的,很沉,摘下来晒干后就像一朵花绽放开来,还会有松子从松球里掉出来,我们把它用簸箕扇干净卖钱。摘松球是一个又脏又累的活,松树油会粘得满手满脸都是,更可怕的是遭遇马蜂。有时看到树顶有大颗大颗的松球,只顾伸手摘,一不小心碰了马蜂窝,就会被马蜂蜇肿了眼。有一次我被马蜂蜇了脸,好几天不好意思出去见人。松球晒干了特别好烧,每个班都会生一个炉子,放进松球,炉子就被烧得通红,暖暖的,被马蜂蜇的痛苦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后来我和哥哥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我们到城里工作后,把父亲也接到了城里,可是娘的坟却永远留在了那个小山村。前些年,国家为库区移民每人每年补助600元钱,为我们村庄铺了柏油路,街道也全部铺了水泥。村子周围的那些山,因为空气清新,风景优美,被打造成一个旅游度假区,建起了五星级酒店。老乡们养起了奶牛,日子越来越红火。
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回到我那可爱的小山村了,可是在梦里,我常常梦到那熟悉的街道,红红的山枣树,苍苍的老松树,梦到娘坐在我们生活过的院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