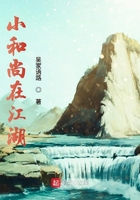“师姐,别闹了,再让我睡会儿。”我翻了个身,下意识推开背后推攘的手,隐约觉得那手带着尖锐的指甲。我那么一推,背后消停了,可是接着鼻孔痒痒的,像被什么东西扫过,又有点像毛毛虫爬过,等下,毛毛虫!!可怕的毛毛虫!!我一个激灵,瞬间如鲤鱼打挺坐了起来。
“师姐!你做什么吓我!”
我一肚子火气,可转头却愣住了。再看看周围,陌生的床帘,周围的摆设极致简单,那只死鸟扑哧着翅膀,扯着嗓子叫唤道,“丑丫头醒了!丑丫头醒了!”
敢情刚刚弄我后背的是它的爪子,挠我鼻子的是它那艳丽的羽毛。还真是人善都能被鸟欺,还是当坏人好啊。
我看它离我近,作势要抓它,欲拔它的毛。它一惊,骇得飞老高,绕过我,直接立在一男子肩上,彼时那男子正背向着我,望向窗外的梅花树,似在想着什么出神了。光影投射在身上,留下地上颀长的身型影子。那鹦鹉落在他身上,侧着身子,肆无忌惮的看着我。
原来我昏迷前的感觉真的没错啊,真的是他救了我。可那会儿那么难受,怎的这会儿没事了呢?我突然间看向胸前。
“啊~” 这分明不是我的衣服。“你个死流氓,你对我做了什么?”
怒向胆边生,一边说着,一边下意识的手边有什么就扔什么。一个杯子就那么被我狠狠的扔向他后脑勺。我以为只他的身手,再怎么着也躲得开的。然而事实是他居然被我砸到了。
只被我砸了那么一下,电闪雷鸣般的速度,一只手直接掐到我脖子上,我看着他眼里的搵怒,恐惧如狂风暴雨般袭来。
他的眼睛里像是变得极蓝,放佛宝石般,却泛着幽幽的阴冷气息。嘴巴的空气被渐渐抽去,彼时我才感到后怕与后悔。他可是北轩王!不折不扣的嗜血大魔头!
我以为我会就此离去,可那鹦鹉却将爪子摁在楚昭然的手腕上,挠出几道血丝,它似在阻止他,这会儿我居然有这念头,这鸟儿通人性!
“楚昭然!丑丫头!丑丫头!楚昭然”它急急叫了两声,叫唤的节奏有点像民谣。
突然楚昭然的手松开了,我离地的身躯终于有了着落,软软跌倒在地。我惊骇得看着他,快快向墙角靠去,有多远离多远。
他的表情有些奇怪,似乎不明白自己刚做了什么,彼时愣愣的看了下自己被鹦鹉挠过的那只手,神色难辨。而后他眼睛里的蓝色渐渐褪去,只留下宛如黑葡萄的眼眸,片刻后闭眼后,神色恢复如常。我如看怪物般看着他,眼里只余下恐惧,那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和森林里相见的那回相比,这次的感觉更甚。
我下意识的吞了吞口水,不知道该懊悔那日花灯节执意要出门,才受这接二连三的惊吓,还是该庆幸自己的脑袋瓜还在脖子上。
“你也怕我?”似乎是疑问,又像是在肯定,我不敢答话。说不怕,委实是假话,说怕了,他会不会一怒,完成刚刚未完成的动作,直接掐死我?
一瞬间,房间里静寂得恐怖。那鹦鹉也不语了,转头瞅瞅我,然后再瞅瞅楚昭然。
“进去搜!”外面突然传来一个尖细的声音,跟房间里的静寂相比,宛如平地惊雷。
“徐公公,恕难从命,这里是北轩王的客房。”门口一左一右侍卫提刀阻拦道,其中一人应答道。
“大胆,咱家奉的可是皇上的懿旨,前来捉拿朝廷钦犯,谁敢阻拦!”
“卑职不敢!”那侍卫嘴上应着,可丝毫未见退让。一个小小侍卫居然有如此胆魄,倒让我有点惊讶。
“不知道我房门中有何钦犯,要劳烦皇兄下如此懿旨?还是你们这些狗奴才拿了懿旨胡乱指证我,居然认为我堂堂北轩王房中藏有钦犯?”楚昭然幕的推开房门,气势逼人,声音温和,却只一句话便将那公公呛住了。
“王爷恕罪,”徐公公定是仗了谁的势,言语间谦卑,却无忌惮之色。“咱家也是奉命行事,督主接到线报,说明月戏班团的白狄正是前朝那余孽,咱家也是奉了皇上的懿旨前来捉拿,只谁想到那白狄还跟外邦勾结,被他们给逃了。他们斩杀了一百多府兵,却也负了伤,相国公府外围又有重兵把守,方才奴才又在浣衣坊搜到他们的戏服。料想这会儿他们应该还藏在府中,所以这才斗胆搜府。”
听这一席话,我心里一慌,师兄他们果然动作了,那日里师傅说要搬回京师,我就有这种预感。我知道我劝服不了他们,正如他们劝服不了我一般。娘亲说,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苦。她走时的那日一脸的虚弱,嘴上、手上到处沾着鲜血,饶是我再怎么擦都擦不尽,可是她的神色却是平静的,她抓着我的手说,“倾城,你要记住了,不要去报仇!我只要你好好活下去,一定要开开心心活下去!我要你发誓!”
她那时候脸上的决绝现在想起,依然是那么的清晰。
我只想远离这些,就像娘亲说的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好好活着。可是他们都还是找上了我,只师傅他们从来不相信我手中没有他们要的东西,可我确实知道那东西已不在这世间。因为那东西娘亲死去的那日我亲手一并将它烧了,尸骨无存!
我知道师傅是把对娘亲的遗憾弥补在我身上了。有次我看着他喝醉酒,叫着娘亲的小名。我就知道,他这一生都难逃娘亲的情网。应该说在更早前我就知道了:娘亲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写信嘱托他照料,当我在那荒凉大街上被他捡起那一刻,我就知道了。
师门里就二师兄比较没心没肺,他的喜怒哀乐均表现在脸上,其他人我均看不透。师傅、大师兄、三师兄、连着小师姐他们是对我好,好得让我特别眷恋跟他们在一起的点滴,如果不来京城,我会觉得我有了一个温暖的家,还有了一堆可以依赖的家人。
只是那些只如水月镜花,终将幻灭。虽然我很早就知道,可是我却选择回避,不去想,只当师傅只是师傅,师兄只是师兄,师姐还是师姐。可现实就是在一一提醒你,顾倾城,你别傻了,除了你爹爹和娘亲,没有人可以那般无条件的对你,他们对你的好是有条件的。
先是师傅想借问娘亲死前都跟我说了些什么,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我?我就知道他在套我的话。我言简意赅回答他没有。他顿时就特激动,直言不可能。是的,他们都不完全相信我,我说了实话可是他们没人相信。
师傅把我收为门下后,却从来不教我武功,他说女孩子舞刀弄枪的不好,其实我知道他怕我有一天摆脱了他们的禁锢。我那会儿蛊毒并未深入骨髓,就他的医术,可是他选择了压制而不是根除,所以只我每半个月都要喝一次药。
师傅拐弯抹角得到我的实话后却不相信我,本意也许是让大师兄、二师兄、小师姐对我百般好,让我说出真话。所以授意大师兄带我去坊间,听当今天子如何的不仁;让二师兄给我做各种好吃的,欲予我滋生一种“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的愧疚感;无视三师兄在我醉酒之时拿毛毛虫吓我,寄寓我酒后吐真言……他们只觉自己百般试探,失败无果,是因为自己皆是男子,与我不够贴心,所以才有了后来小师姐的出现。
这么长时间,我累了,他们也累了。那日里,大师兄被刺客追赶,倒挂在我屋梁上,屋子倒了,我们被埋。九死一生被挖出后,我索性跟师傅师兄说,很多事我忘了。后面我的所作所为,比如行动呆滞、健忘、时常头痛、脉搏紊乱等也确实印证了,我失忆了,估计他们也死心了,所以才来京都铤而走险。
关于我失忆的事,我也真没说谎。那日里一根横梁直接砸在我脑袋上,害得我躺在床上近半月。很多事情我迷迷糊糊的,实在想不起。
只是没人知道,有些事情,我从未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