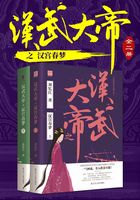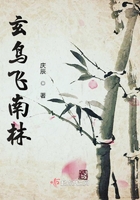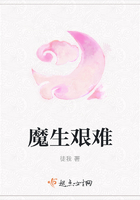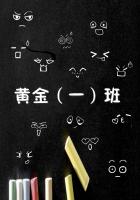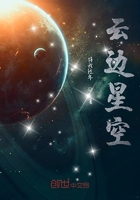1923年春天,三十九岁的俄国人鲍罗廷到达广州后,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任中国国民党顾问和孙中山首席顾问。身材矮壮的鲍罗廷是犹太人,出生于俄国,年轻时移民到美国,就读于瓦尔帕索大学,毕业后在芝加哥教书,几年后开设了一所俄语学校。俄国革命爆发后,鲍罗廷回到俄国从事革命工作,很快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鲍罗廷显然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精力充沛的党务工作者,在广州不长的时间里,他高效率地帮助孙中山重组了国民党,还安排国民党中坚力量蒋介石在1923年出访了苏联,中心议题是商谈中国国民党与苏联的实质性合作,包括经济和军事援助,设想建立一个军事干部学院。鲍罗廷还帮助孙中山赶走陈炯明残部的进攻,陈炯明与孙中山最大的分歧就是对苏联人的态度,由于分歧无法调和,双方大打出手。在苏俄的帮助下,濒临出局的孙中山重新在广州站稳脚跟。在物质援助之外,苏俄告诫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要获取成功,不可须臾离开广泛的政治思想准备工作。孙中山同意将苏俄的政党体制引入国民党,以此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孙中山特别指出改组国民党的用意,就是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此前的国民党,接近欧美式政党;孙氏认为这样的方式组织松散,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希望借助苏俄的“革命技术”,将国民党彻底改组。
稍后,苏俄方面向广州派遣了大批政工、军事人员,派加伦任大元帅府首席军事顾问,巴甫洛夫为孙中山军事总顾问兼军事顾问团团长,切列潘诺夫为黄埔军校首席军事顾问,俄军事顾问李糜为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长,沙非爱夫顾问为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作指导。孙中山领导的黄埔军校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航空局等军事单位和部队的一部分机关枪长枪短枪大炮等武器弹药也是苏俄运送来的。8月底,国民党方面派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考察。12月15日,代表团回国抵达上海,一个很反常的行为是,团长蒋介石没有继续前往广州,而是坐船赶回溪口祭奠母亲王太夫人的六十冥诞。临走前,只向孙中山捎去一个建议,任命杨庶堪为广东省省长。回奉化后,蒋介石又将他所写的《游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然后便“息影慈庵,拂案焚香,绕茔抚树;入夜,则闲躅山门外,岭上寒风,松间明月,清景耐人寻思”,过了一段与世无争的恬静生活。不过,这份报告至今尚未发现。后来,蒋介石曾写作《我的游俄观感》对这一段时间的思想动态作了阐述,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很难被简单地嫁接在一起。前者立足于“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后者立足于“民族独立”和“国民革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并且,经过对苏联的近距离观察,蒋介石认为苏俄的“国际主义”是靠不住的;不但靠不住,而且苏俄的真实用心,是通过扶植共产党来吞噬国民党,绝不会对国民党抱有善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既不愿违心称赞苏俄,又不愿忤逆孙氏意旨,只好选择半路“逃回老家”。
孙中山并非不了解苏俄及共产国际的用心,可能他自认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在获取苏援和抵制“赤化”之间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就像他以往对日本及其他力量那样。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刘成禺曾提醒孙氏:“联俄容共”之后,共产主义在党内渗透,“党员恐不能持定吾党义”,“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意在吞并消化国民党”。孙氏以“吾自有处理之法”为由,呵斥了刘氏,劝其“此后党务,可不必问”。
在“联俄容共”战略思想下,重组后的国民党如虎添翼,在一种新的“党治体系”下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这时候,孙中山可以理直气壮对北京政府表示不耻,高高擎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早在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就明令废止五色旗和十八星旗,代之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不过他那时的话似乎不太管用,直到1923年8月就任临时大元帅后,在广州举行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五次评议会,发现会场上仍然悬挂着五色旗。孙中山很不高兴,训导学生们道:“我想你们对于革命的主义和精神怕不大明白,恐怕对革命的认识与历史也不大明白吧。比如五色旗,你们刚才向伊三鞠躬,我就不。你们一定以为我不敬国旗了,哪里晓得五色旗是满清一品官的旗?我们革了皇帝的龙旗,却崇拜官僚的五色旗,成什么话!”孙中山对于青天白日旗的青睐,甚至还可以追溯到1907年,那一年的2月,在同盟会会议上,因国旗样式问题,孙中山与黄兴发生争执。孙中山主张用青天白日旗,理由是图案由烈士陆皓东生前设计;而黄兴认为图案太像日本国旗,主张用井字旗,以代表平均地权。两人发生了激烈争执,黄兴一气之下,要脱离同盟会。争执中,宋教仁站在黄兴一边,认为孙中山过于专横跋扈,导致会员离心离德,同盟会前景黯淡,也辞去了代理庶务干事的职务。……孙中山不仅想撕扯掉五色旗,他同样想打碎的,是五色旗后那让他极不舒服的制度。在孙中山看来,只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才能代表中华民国:红色是鲜血之色,代表为自由不惜流血;青色是天空之色,代表公正平等;白色是纯洁之色,代表人心清洁乃能博爱;十二道叉光代表干支之数,象征中国传统。现在,南方的孙中山终于可以借助苏俄人的力量,了却自己的心愿了。
再左转
1922年,一向跻身于前沿政治的梁启超已从漩涡中退隐,决意避免政治的直接论战,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上来。梁启超苦苦探究的,是如何找到一条适合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道路。这一年,他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等着作,这是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史稿”等选题的结集。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梁启超觉得仿佛抖落了一身疲惫,剩下的只有清醒和客观。面对过山车似大起大落的中国格局,梁启超决意回头远望,一直回溯到中华民族的源头,去探究历史、民族、文化发展的脉络和走向,探究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中国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的原因……只有弄清楚这些,才能发掘出中华民族的不足和弱点,并对世界的走向作一个清醒的预判。梁启超考察了上古时代的满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濮族等民族的地理分布、语言特点、生活习性,以及其融合于中国民族大家族的历史过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在梁启超看来,一条奔腾不息浊浪滚滚的黄河,最能说明历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最能说明中国历史起伏落差之大的特点:
一、中国黄河汉域原大而饶,宜畜牧耕稼,有交通之便,于产育初民文化为最适。故能以邃古时即组成一独立之文化系。
二、该流域为世界最大平原之一,千里平衍,无冈恋崎岖起伏,无湾(碕)离旋折,气候四时寒燠俱备,然规则甚正,无急剧之变化,故能形成一种平原文化,其人以尊中庸爱平和为天性。
三、以地形平衍且规则正故,其人觉得自然界可亲可爱,而不觉其可惊可怖。故其文化绝不含神秘性与希伯来埃及异,居其地者非有相当之劳作不能生活,不容纯耽悦微渺之理想,故其文化为现世的,与印度异。
四、天惠比较的丰厚,不必费极大之劳力以求克服天然,但能顺应之即已得到安适,故科学思想发达甚缓。又以第二项所言地形气候皆平正少变化故,故乏颖异深刻的美术思想,又以爱乐天然顺应天然之故,故伦理的人生哲学最发达。
五、此一区域,别无第二个文化系,而本部(即第一部)地势毗连不可分割,故随民族势力之大发展,文化亦愈益扩大,结成单一性的基础。
六、以第二项理由故,中庸性质特别发展,惟其好中庸,万事不肯为主我极端的偏执,有弘纳众流之量,故可以容受无数复杂之民族,使之迅速同化。亦惟因周遭之野蛮或未开的民族太多,我族深感有迅令同化之必要。而中庸性格实为同化利器,故演化愈深,而此性格亦愈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