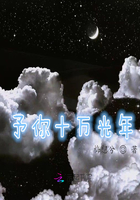从延安北上定边,沟壑愈来愈浅。山峁与蓝天的交接处,鲜丽的黄杨亮得象雨后阳光里的云霓,疑是黄土高原黄色的极致。上了沙原,天地阔大,远处间或有一株绿的云与一抹黄的浪。略见平缓的泥顶土屋,同树荫簇成一个沙海的岛屿,便是抵达地处陕北高原之西北边缘的边城了。
这里可以看见古长城的遗迹,可以看见不少的盐湖,其余似乎只是一个连着一个的沙丘。登高望远,沙如海坡,呈有节奏起伏的波岸与浪谷。新月型沙梁,在风力强处,伸展成弯曲的长带,抛向绿色的草甸子。
据说,清朝以后实行“中外和耕”多年,汉民出边耕收,斩荆劈棘,垦生废熟,自然植被逐渐衰退,黄沙便壮着胆子向南开发了。导源于北部白垩纪紫红色质页岩层的游沙,每年几米、十好几米凭风前进。植被茂密的草原在收缩,“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况味也淡起来。
抬眼看去,沙土裸露,寡有河湖。这也就三年两头旱,全年一场风,有日犹如飞雪,无风也起沙尘。年岁不大的定边人,也记得那场大风,飞沙走石,移砖揭瓦,天昏地暗,路人失迷,大白日室内点灯照明。
置身于沙的世界里,听说有别一世界的一个去处,定边人叫它“海子”,实在是令旅人向往呢!
超过几个沙丘,未能看见海子,眼底却有一种绿意荡漾。沙柳,有绿中带黄的叶片,青色的枝条,背着阳光在沙上摇着倩影。有着黄色树冠的小叶杨,枝干白得艳丽。暴出沙土的根须,抽发出鲜亮的嫩枝儿。灰色的沙枣树,果实小若钮扣,黄的或红的皮儿,包着如絮的果肉,却有炒面一样的美味。
林中的沙没有沙粒微细,被风刻成各种木纹形,变幻万端。沙的纹饰上印有枝屑,羊和兽以及鸟的足迹,说明它并非是一块寂寞的土地。
阳光暖暖地照着,此刻竟没有一丝风,静得树叶都如同雕塑一样。忽地,远处有雷吼声,接着树林便狂然挥动起整个枝条来,象一个凶神匆匆走过。片刻工夫,又消失在远处的沙洼里了。
看沙上凸起一丛伞顶状的沙堆,用手刨开,竟是一簇雪白的蘑菇。拱形的外部,因顶着沙子而结成青色的壳子,却在细线一样纹饰的内部,藏着白色的露珠,轻轻一握,湿得能捏成一团块。
听不到鸟儿的啼叫,呼地飞起几只,一阵翅膀的扑打声,令人一怔。一只大鸟在云下盘旋着,象朝地面寻找着什么。嗡嗡嗡,是一只失群的黄蜜蜂,绕着陌生客人不离的飞动着,最后竟亲昵地落在客人的手掌上,扇着透明的薄翼。许是闻到了芬芳,蜜蜂飞到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似的花上,这花儿不同的是有一顶白色的小伞,高高地擎着。
这林中的沙没有沙丘上的性野,却有几分柔意。只因为面临的是一片盐蒿丛生的紫红色的草地吗?盐篙间隙,是绒毯一样的无名草。这里简直是一座天然公园了呢!
更显得象公园的是沙林中的一泊湖水,许是定边人说的海子了。林子的倒影,覆盖了整个湖面,树的枝叶隙问,有织着的浅蓝色的天空。海子的水,被四周不同颜色的树木染了,微风中的细波,宛若沙纹在流动中。湖面上,有几只戏水的蝴蝶和蜻蜓。湖畔的一棵树倒下了,根子拔起来如无叶的枝条,而枝条插入了湖中,一种殉情于海子的静态。
天呈现紫绛的暮色时,从草地上围拢来了羊群、驴群、牛群,被牧羊老人或骑驴的小子或放牛的女子吆喝着来海子边饮水。鸟儿们在归巢前也来了,有白肚皮的麻燕,有扁嘴的水黄鸭,有沙鸽,还有乌鸦,在海子上举行鸟国的盛会。忽有一只鹞子飞来,打破了海子上安温的境致,撵散了麻燕,冲击着,追逐着,在空中形成弧形和波浪形的图案。鸟儿们嘎嘎地飞出了林外,一种战事的气氛。
牧人会告诉远方来的旅人,说明湖水叫“圆海子”,传说是人工挖的。会问你这圆海子象什么。象什么呢?旅人会思付着:一个眼镜片,林中的眼睛,沙海的酒杯,草原的心。
因为有了这海子,边塞才显得美丽。有了它,才会少了沙丘的枯燥,多了防风林带,宽了草原和田园。总说沙海沙海,而海子才是真正富有生命的活力的海。
海子中的水来自地下,也同样来自天上——大海母亲那儿。
《朔方》一九八三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