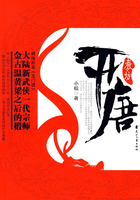这吊脚楼的主人姓胡,因为性格憨厚,人们叫他二憨牯。二憨牯是一个没有成家的光棍汉,因为穷,也没有土地,所以把小屋子吊脚在水塘里。刘桂子的家离这里不远,她打猪草在这水塘里洗,经常看到这二憨牯曾在后楼端开过活动板用吊桶提水,二憨牯在这次均田运动中获得了土地,对周立英很是拥戴。刘桂子熟悉了地形地物,掌握了屋主人的心态,所以她让周立英把秘密活动选择在这里。现在巡捕队从三面包围了吊脚楼,立马就会破门而入,在这危急的时刻,刘桂子所作的选择果然派上了用场,周立英和党人们无不感激。不一会周立英等几人一个个从这楼口下去,不声不响地潜到了水里,最后刘桂子把后门关好,也准备潜水。
然而,时间太短促了,就在最后一党人刚刚从楼口下去,巡捕队已从前门破门而入。刘桂子本想也从这楼口坠下一起潜水出去,可是她下去之后那两块活动板便没人盖,喊二憨牯来盖已来不及,只要露出这个楼口,巡捕队便会知道他们要追捕的党人在这里下水潜逃了。现在已经下水的丈夫和五个党人还在水塘里,如果巡捕队知道这些党人是从这里下到了水里,那他们肯定会将水塘包围,到时丈夫和五个党人一个也跑不了。为了掩护他们,刘桂子没有再下水了,她迅速盖好了那两块活动楼板。
投进水塘的党人暂时应付过去了,可她这个大活人怎么办?这吊脚楼又不是她的家,一个女人夜不归宿跑到这小楼来做什么?巡捕队追问她,她该怎么应答?如果露出马脚,岂不让巡捕队疑窦大发,岂不会给尚未脱身的丈夫和党人带来危害?她得找个借口应付才是哇。
这吊脚楼是并排两间,一间为堂屋,一间为内室,后向为吊楼,两间都有后门,刘桂子灵机一动,从后门钻进了二憨牯的内室。其时二憨牯尚未安睡,刘桂子迅速贴上去,对他耳语了一番。
巡捕队破门进来后在如狼似虎的搜查,自然他们没有搜捕到党人,只从内室把刘桂子和二憨牯双双推搡了出来。尧棍子眯缝着三角眼来到刘桂子面前,半晌,他伸出一只手托起刘桂子的下巴,喝问:“你男人呢?嗯?你男人和那几个革命党都到哪里去了?说!”
“什么革命党,我不知道。”刘桂子不卑不亢,回答他。
“不想说是吧?”啪,啪,啪,尧棍子左右开弓,对刘桂子劈脸就是几巴掌,立时她嘴角流出一行殷红的血。她怒目而视:“你凭什么打人?”
“凭什么?”尧棍子睁着三角眼,露出一副凶相,“老子还没和你算账呢。”
尧棍子尽管凶,可他心里却在纳闷:妈的,那密探报告说,他亲眼看到周立英和五个非同寻常的人进了这个屋子,那肯定是革命党在这里搞秘密活动,片刻的功夫他就带领手下把这屋子包围了,蚊子都没有飞出去一只,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人了?他也想到了他们可能会跳水潜逃,可这吊楼离水面也有一丈多高,跳下去也该有些响动,可他们怎么一点也没听到,莫非这女人为他们通风报了信?可这样那她为什么又不跑,她还要留在这里做什么?这里面一定有文章,说不定他们就藏在什么地方,是仓促之间她已经来不及了才留了下来,进了这光棍汉的房里。
他吼叫起来:“搜,给我继续搜,里里外外的搜。”
尧棍子下了令,十几个巡捕便像没头苍蝇一样,立时乱钻乱敲,把这吊脚楼的楼上楼下闹了个翻天覆地,最后还往水塘里放了一通乱枪,可还是搜不出人。
尧棍子没辙了,他只好再去撬刘桂子的嘴,他拿来一付绳索在刘桂子面前扬了扬,说:“刘桂子,你给我说实话我可以饶了你,你要继续装蒜,我现在就把你吊起来。”
“你要我说什么?”
“你男人和那几个革命党你到底知不知道?他们现在藏在哪儿?”
“我不是告诉你们了吗?我不知道。”
“你不会不知道,”尧棍子耐住性子,说,“我们的人亲眼看到你男人和五个乱党进了这个屋子。你这是在抵赖。”
“是有几个人进了这个屋子,可那是我请的帮工。”
尧棍子略有快意,看来情报没有错,确有人进了这个屋子,他问:“你请什么帮工?”
“砌猪圈呀!”刘桂子早已想好,并与二憨牯打了耳语,因此她坦然而答,“不是说富人靠读书,穷人靠喂猪吗?多喂几头猪养家糊口呀,怎么?这你也要管?”
“这不是管不管的事,现在我只问你,人呢?”
“走了,在你们来之前就走了,不信你问问他。”刘桂子指指站在她旁边的二憨牯。
“走了?”尧棍子冷哼一声:“那你为什么不走?再说了,你请帮工不往自己家里去,却请到这屋子里来了,这怎么解释?”
刘桂子泰然自若:“这你也不懂?你们大户人家什么事有管家管着,我这小家小户的没有管家,可请得三五个人也要有个掌本的呀,这二憨牯又会砌浆,又会木匠活儿,我男人不在家,只好一付卦儿交给他,本也由他掌,工也由他请,可他也不能白干,刚才他们走了以后,他便把我留下来,问我要酬劳,我正和他讨价还价呢,说着说着你们就来了。”
刘桂子说得滴水不漏,人也搜捕不到,尧棍子再也没有办法,可他不甘心,妈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唯她是问。可怎么个问法呢?说她私通乱党吧,既没有她的口供,更没有别的证据,怎么治罪?他脑筋一转,有了,她与这光棍汉孤男寡女的深夜在一起被他们抓住,这不能算奸情吗?在他们木坪山周氏家族,女人偷汉子按族规是要被活埋的,偷情的汉子也是死罪,正因为族规森严,他被这女人砸掉两颗门牙,砸得嘴皮开了花,他也不敢声张。这女人太可恶了,他得不到她尚且不说,还为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她夺去了那五亩田产不说,她男人又发动那帮穷鬼夺去了他的大片田地,现在她口舌如簧,实际暗地里在私通乱党,不借族规除了她,难解他心头之恨。
他吼叫:“把这对狗男女都给我捆起来,带回去审问。”几个巡捕一涌而上,把刘桂子和二憨牯五花大绑捆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