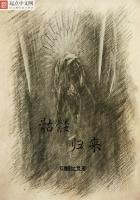面对如此惨象,陶斯任伤心极了。他追念他,当年他曾双手捧着他的脸蛋,以脸颊亲热他,抚爱地吻他。他依稀记得,他仰望他,他是那样的浓眉大眼,英气非凡,却又是那样的和蔼可亲,令他喜欢,令他崇敬。而现在这英气非凡的头,这和蔼可亲的脸却被砍了,还要让他身首异处在这城头示众,他日夜思念着他,没想到是以这样惨烈的场景和他相见,这现实太残酷了,他心如刀绞。
陶斯任不忍再看下去,转身大哭了一场。哭着疼着,突然他萌发出一个念头,不行,周叔在生他没能报效,现在他虽然牺牲了,他也要补报,他要收殓他的头颅,他在生那么奔波,那么劳累,现在他死了,他要让他身首合一,让他安息
是夜,陶斯任短衣短扣爬上城头,他先在城头西边往下抛物,故意弄出声响引开游动哨,然后在黑暗中迅速奔回城门处,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钩绳,以锚头钩住城头石缝,随即像壁虎一样拉着绳索下到了门洞之顶,将他周叔的头颅摘了下来,放进了随身带来的书包里,随后又顺着绳索往下滑,等到那游动哨从西头回头过来,他已稳稳当当地落地了。陶斯任得手了,可是门洞上有大灯,亮光之下,他的身影被那游动哨看到了。原来当局不但要用周立英的人头示众以震慑百姓,而且还要利用这颗人头来钓地下党的鱼,谁来摘取就抓捕谁。当下那哨兵开了枪,引来了一大帮兵丁,只是陶斯任手脚麻利,一眨眼便消失在夜幕里。
陶斯任连夜把周叔的头颅送往木坪山,他整整走了一个通宵,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到达。在老周家人们一遍悲哀,三天前周立英的尸身已被亲邻收回,但身首未合既不能安葬,又不能不葬,家人族人正不知如何是好。现在陶斯任冒险把周叔头颅收回来了,周家人感激不尽。当下周立英之父周老大接过儿子的头颅,一阵儿呀肉呀的大放悲恸,之后将其身首合一入了殓。
陶斯任为报答周叔办了这件大事,他该走了,可是他的心愿未遂,他想打听周家妹妹的下落。然而一提到小妹妹,周家人仍对他摇头,老爷爷周老大对此更是讳莫如深。现在陶斯任已十八岁了,他记得在桃花营周叔托付他的时候,他说他女儿比他小,还只有五岁,时光流过了十余年,算来小妹妹已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都是少男少女的,问多了他怕背上轻薄之嫌,况且周家人又处在大悲大恸之中。因此他跪拜了亡灵以后只好无奈地走了。
回到学校,陶斯任被警察抓了。警方抓他的理由有三。其一,他在警局有案底,而哨兵看到的那个身形与案底上的他有形似。其二,警方怀疑他后便去县立中学查他,而他恰恰在案发后旷课,时间上的吻合又认定了他。其三,他现场遗留下来的钩绳被警方获取,凤西县城不是大都市,拿着这钩绳往几家杂货铺一查,很快就被一家店铺的伙计认出,此物系一学生模样的少男在本店所购。有此三者警方认定案犯系陶斯任无疑,于是陶斯任第二次进了监牢。
陶家的大少爷,在家有奴婢,在校有伴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么娇贵,那么优裕,现在进了监牢,可让他受苦了。当局以为抓到了地下党,先是利诱他,让他自首,让他供述机密。陶斯任才十七八岁刚刚成年,只不过个子长得高大像个人才,可什么党不党的,什么机密他哪有哇。后来对他用了刑,皮鞭子老虎凳把他折磨得皮开肉绽,可他挺坚强的,没有就是没有,不屈打成招,不乱供祸及别人。
为了周叔受苦他并不后悔,他就这么熬着挺着。两个多月过去了,当局在他身上实在做不出什么政治文章,又看他是大地主大豪绅家的少爷,便在钱财上狠狠的宰了他一把,父亲陶西田前去保释交了银洋五千,还交了牢饭费狱教费等一千才放人。陶斯任出来后仍想去上学,校方也还主持正义,大包大揽的想把他的事消失掉,让他就学,可是那学监高低不准,他认定陶斯任被****了,留在学校会煽动学生产生对政府不满。那学监是个政客,反动透顶,他又足当局委派来的,牵涉政治上的问题他说了算,最后硬是把陶斯任给开除了。陶斯任好气恼,他恨不得一拳头把这个黑世道给砸烂,可是他做不到,没办法他在县城的陶家店铺里躺了几日。后来他想通了,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反正他也快毕业了,不如就到南州考学去。于是他拿了凤西县立中学的肄业证去了南州,在一所华侨办的大学报了名。
这学校叫燕南大学,创办人叫燕妮,与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女儿同名,是一位爱国的南洋华侨,一位豪富女商人。燕妮祖上是南州人,她在这里办学商业目的是其次,主要是为报效祖国,报效故乡,让故园子弟在她办的学校受到好的教育,因此尽管她的学校无论校园校舍教学条件还是师资力量都不亚于省城的国立大学,并且南州也是大都市,消费水准不低,但她的收费却比省城的国立大学要低得多,因此生源丰足。又因学校办在南州,自然要接受南州当局的管理,体现在校名上便各取一字,所以叫燕南大学。
陶斯任在燕大报了名,之后便在凤西城里温习功课。凤西城里有他陶家的商号,少东家要在这里存住不在话下。到了秋季燕南大学招考,陶斯任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上了。他很高兴,为此他回了一趟桃花营。他要向父母报告他的这一上进。母亲陶窦氏自然为他高兴,她痛他,现在儿子长进了要成为有大知识的人了,她怎能不高兴?她向夫主陶西田进言,让他请会尊族尊并集聚家人为儿子置酒作贺。
陶西田则不然,在他看来儿子的这一长进对陶家基业并不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儿子从小被娇惯了,任性,以致十年前会上的大旗他也敢砍倒。这十年来在山外读书又弄出事来,两次进了当局的牢房,没有他的重金保释这事不可设想,虽然他弄出的这些事都是为了报恩,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却反映了他敢做敢为,敢以当局为对立,他的这种敢做敢为可是陶家基业所不需要的。他在山外读的是新学,在思想上,在理念上与他信奉的儒学已经完全脱节了,现在他又要到南州这大都市去读书,在新的思想流派的影响下,说不定读了以后他就再也不会回桃花营了,而他是他唯一的儿子,是他身后陶家基业的传人,他不能让他飞了。因此他对儿子的这一长进不但不觉得可喜可贺,而且还深为忧虑。
不过他也痛儿子,内人要置酒庆贺他不能让她扫兴,正好为管束儿子几年前在程家为他说的一门亲事也要置酒席正式定下来,因此宴请的事他便按内人说的让管家梁满福去办理。
现在陶西田已成了当家老爷,因排行第四,被人们尊称为陶四爷。翌日,陶四爷请来了会上长老、本族族尊、结交较深的外族头人及亲友,程家亲事的父长未来的亲家公程友四也坐着大轿订亲来了。此前陶四爷对这门亲事曾几次在儿子面前提起过,儿子一直没有表示过从命,这次正式定亲了,陶四爷怕儿子不从有失体统,盛宴之前他以父命和儿子单独说起了此事,让他顺从,并在席上显示得体,对未来的岳丈表示恭敬。然而他没想事到临头儿子竟激烈的反抗起来。
当下陶斯任问:“父亲,母亲不是说是为我考取大学而设的宴吗?你怎么变成这事了?早知是这样,我不要你庆贺,我要走,现在就走。”
“你敢,”陶四爷吼了起来。程友四是桃花营三个半家族中的程家头人,今天又是上席之主,面子很大,现在客房里他被宾客众星伴月一般的捧着,如果儿子走了,那程友四的脸面可就丟大了,为此陶四爷着急,他使出父威,也第一次对儿子甩出恶狠狠的话,说,“今天只要你跨出大门一步,我就打断你腿。”
陶斯任仍是不从,他心里只有周立英的女儿。他想,周立英托付了他,要他保护他的女儿,一辈子的保护她,这里面包含有将女儿许配于他的心愿,现在周立英也真的死了,为了革命被砍头了,他决不能辜负周叔的期望。因此他坚持要走,他使性子:“你打吧,只要腿没断我就要走。”
这下陶四爷没辙了,他怎么舍得打儿子呢,可是儿子不从命,现在宾客都来了,马上就要开席,马上就要举杯定亲,他真要走了,帽子下面没人,他怎么向程友四交待,宾客满堂的他怎么收场哇。
这时管家梁满福却找他来了,说女方的父长程老爷有事要和他议议。陶四爷正焦头烂额,刚好他把儿子交给梁满福,交待他不许儿子走出陶府,还要说服儿子,要把儿子整理得衣冠楚楚的入席,不能失了陶家少爷的体面,上了席他就可以不管了,由他想办法稳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