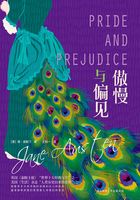兴儿是贾琏的心腹小厮,也是个眼尖心细、伶牙俐齿的机灵鬼。第六十五回,贾琏偷娶尤二姐后,尤二姐为摸清荣府底细,以解心中疑虑,一日特备点酒菜,叫来兴儿问长问短;兴儿“在炕沿下一头吃,一头将荣府之事备细告诉”尤家母女。兴儿细说荣国府的一席话,较之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语境不同,侧重不同,各尽其妙,相映成趣。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是冷子兴与贾雨村“在村肆沽饮三杯”时谈天说地的闲聊。谈到贾氏“一族”必从根根底底说起,摆出贾氏三代宗族谱系;谈到贾府宅第,也要追述荣宁二府“先年”的“兴盛”,对比今日的“气象”;谈到贾府家人现状,自然更要从硕果仅存的老祖宗贾母说起,一直说到贾宝玉等孙辈弟兄姊妹及其相关配偶。这段“演说”,介绍重于评说,相对较客观,内容似乎面面俱到,但多是泛泛而谈,语言也缺乏“演说”者的个性——与其说是个性化的人物话语,不如说是作者借冷子兴之口说叙述者要说的话,作为叙述话语的功能大于作为人物话语的功能。但在主干故事情节展开之前,借冷子兴之口来全面、概括介绍一下主要故事环境、人物关系等等情况,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线索复杂、人物众多的小说,不仅完全是必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毕竟比由叙述者平铺直叙一说到底更巧妙、更自然,可读性更强。
相对而言,兴儿细说荣国府,则评说重于介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语境不同,话语内容、话语功能也大异其趣。兴儿的一席话,既是这个机灵鬼应对如流地回答尤家母女问题,内容很有针对性,不是泛泛而谈,语言也具有说话者鲜明的个性;同时,在《红楼梦》故事情节已经过半的第六十五回,作者也是要借兴儿之口进一步细说荣国府,给有的重要人物作出必要的评说或概括,向读者传达或透露某些重要信息。因此,兴儿的长篇细说,既是个性化的人物言语,又兼有一定叙述话语功能。
评说王熙凤,是兴儿细说荣国府内容的重中之重,也是评得最尖刻、最精彩的部分。王熙凤是荣国府炙手可热的管家少奶奶,又是贾琏也畏惧三分的“夜叉婆”,更是尤二姐要光明正大跨进荣府大门最难迈过而又必须迈过的一道铁门槛,因此,按尤二姐的提问,兴儿把王熙凤作为首要重点评说对象自在情理之中。
先是评说王熙凤在荣国府的人际关系及其权威后台:“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人,没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儿怕他。皆因他一时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两个人喜欢。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人敢拦他。……连他正经婆婆大太太都嫌了他,说他‘雀儿拣着旺处飞,黑母鸡一窝儿,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瞎张罗。’若不是老太太在头里,早叫过他去了。”王熙凤在荣国府上上下下不得人心,遭人忌恨,她说一不二的权势,仅仅建立在博取贾母、王夫人的信任和欢心的基础上,而她所特别仗恃的硬后台贾母虽至高无上,可以镇得住对她十分嫌恨、虎视眈眈的婆婆邢夫人之流,但毕竟已经风烛残年,来日无多,因此她的权力基础并不牢固持久,就像“太虚幻境”中她的判词画面是“一只雌凤”站在“一片冰山”上一样。兴儿虽然胆子小、骨头软(在第六十七回被王熙凤审讯时的表现即是明证),但颇有点头脑和见识,对荣国府家政的三级权力结构(贾母处于权力顶端却高高在上,不干实事,王夫人作为“二房”内当家名义上执掌大权但精力不济、能力有限,因而实际上真正掌权管事的是王熙凤)洞若观火,因而能把王熙凤在府内人际关系和权力基础说得甚为透彻。
兴儿对王熙凤为人和性格的评说,更称得上字字珠玑,可圈可点。“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估着有好事”,“他先抓尖儿”,“有了不好事或他自己错了,他便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他还在旁边拨火儿”。大概王熙凤本人也万万料想不到,一个在她面前俯首帖耳、唯唯诺诺的奴才小厮,背地里竟对她有这样尖刻如刀、入木三分的酷评。兴儿这些字字精彩的评语,几乎成了对王熙凤形象的经典性评说,人们都已耳熟能详,迄今为止红学家们写的王熙凤论也很少有不加引用的。这是兴儿口中的王熙凤,一定意义上也代表了曹雪芹心中的王熙凤。正因为有了这画龙点睛似的评语,王熙凤形象的负面特征才会如此鲜明突出,使读者印象深、记得住。除了王熙凤,兴儿还评说了荣府的“寡妇奶奶”李纨和“几位姑娘”。“我们家这位寡妇奶奶,他的浑名叫作‘大菩萨’,第一个善德人。”对李纨这一语定褒贬的评价,未必全面,倒也抓住了人物的善良秉性。说二姑娘迎春的“浑名是‘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嗳哟一声”;说三姑娘探春的“浑名是‘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只是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养的,‘老鸹窝里出凤凰’”。这些评语都突出了人物的主要特点,比喻也很贴切、生动。此外,兴儿形容林黛玉像“多病西施”,“风儿一吹就倒了”,薛宝钗长得丰腴白嫩,“竟是雪堆出来的”,这已经够生动、形象了,然而,他更出人意料地说:“……我们鬼使神差,见了他两个,不敢出气儿。”为什么呢?“是生怕这气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气暖了,吹化了姓薛的。”这极度夸张更强化了前面的比喻,近于说相声的“抖包袱”,所以“说的满屋里都笑起来了”。可见兴儿语言天赋很高,颇有幽默感。
兴儿细说荣国府,自然少不了要评说那位远近闻名的宝二爷,这也是尤家二姐妹、特别是尤三姐很感兴趣的话题。对于作为情痴情种的宝玉“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文化水平不高的兴儿绝不可能像饱读诗书的贾雨村那样,能提到人性高度大发一通“正邪兼赋”之类高论,只能用一般世俗的眼光来看取宝玉一些异乎常人常态的奇言奇行,评说中有隔膜和误解,揶揄和调侃,也带几分亲近和欣赏——虽是取世俗的平民视角,却带有兴儿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最后,针对尤二姐玩笑似的提到把尤三姐许给宝玉“岂不好”的问题,兴儿笑道:“若论模样儿行事为人,倒是一对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如果说老祖宗贾母对宝黛“木石姻缘”的赞许意向前面已有多处伏笔或暗示,在这里,通过兴儿的话,则向读者透露了更加确定无疑的信息。按照雪芹原著构思,尽管因种种阴差阳错“木石姻缘”“终虚化”,宝黛爱情只开花未结果,以悲剧结局,但具体情节绝不可能如高鹗所续后四十回写的那样,即,由王熙凤主谋、贾母主宰用“调包计”骗局撮合“金玉姻缘”(即宝玉与宝钗结婚),促成黛玉之死。这个“调包计”是浅薄的戏剧性,也违背了作者原意和贾母的性格行为逻辑。
当然,也要看到,兴儿细说荣国府,虽有不少独具只眼的洞察,相当精彩的评说,但也带某些偏激和偏见。这与兴儿的身份境遇密切相关。他是贾琏的心腹小厮,而贾琏与王熙凤又是同床异梦、或者异床异梦的冤孽夫妻,这就决定了他在男女主子的明争暗斗中,内心必然是倾向于贾琏一边的,兼之王熙凤平时待下人过于苛刻,更增加了他对女主人的怨愤和仇恨。从他对王熙凤的评说中,我们可深深感受到他的满腹怨怼、满腔仇恨。他对自己这位大奶奶人性之恶、为人之诈、整人之狠,固然看得很清,说得很准,但毕竟只是攻其一面,不及其余。通观他对王熙凤的全部评说,除了攻击,还是攻击,没有一言半语的肯定之辞,这同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肯定王熙凤的才能“男人万不及一”,“言谈又爽利”,“上下无一人不称颂”,等等,恰成鲜明对比。两种评说,两种取向,都是各说一面,未及全人。其实,王熙凤尽管心狠手辣,劣迹斑斑,但她毕竟是“人”不是“鬼”,也有人之常情常性,更何况作为女强人、女能人,她也干过一些好事或正事。兴儿的评说也许抓住了她性格中较主要的一面,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片面。
如果说兴儿带着过多的个人感情和个人恩怨评说王熙凤,难免偏激,那么,基于某种思想意识偏见来评说王熙凤,则更可能会把基本是非弄得混淆颠倒。谁都知道,贾琏和王熙凤夫妻不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与贾琏一再妻外纳妾或婚外淫乱密切相关。而兴儿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不仅对贾琏没说半个“不”字(当着尤二姐的面,他自然也不好说,不敢说),反倒怪罪王熙凤“吃醋”,大肆渲染说:“……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瓮……”别看兴儿是地位卑微的奴才小厮,却满脑袋的大男子主义和三妻四妾思想。
在《红楼梦》里,兴儿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人品上也确有阳奉阴违、易反易复的“小人”一面。然而,我们不会因人废言,他细说荣国府的一席话,帮助读者深一层认识了荣国府诸多人和事,他本人的“好刚口”、机灵劲儿也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的这段细说,虽兼有一定叙述功能,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叙述者或作者的观点和意向,却又在思想感情、语言风格等方面深深烙下了他个人的印记(包括他的某些偏激和偏见),所以,归根结底,乃是一种充分个性化的人物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