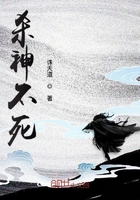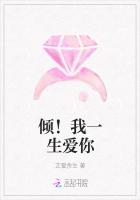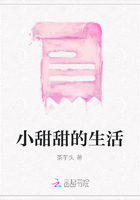李斯奏曰:“韩非,韩国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兵加于韩,韩危急而遣韩非使秦,韩非必为解韩危而来,如此,必不肯为秦王所用,且韩王与韩非有骨肉之情,彼焉能弃亲情而为异姓乎?”姚贾亦奏曰:“昔苏秦为燕入齐行反间之计,大败齐政。今韩危急而遣韩非入秦,安知彼不是行反间之计乎?愿大王思之。”
秦王然李斯、姚贾之言,复问李斯曰:“然可放其归国乎?”李斯曰:“万万不可。韩非天下奇才,若纵之归国,必不利于大王一统天下。昔魏公子无忌、赵公子平原,皆曾入秦而归国,终成秦患。韩非之才十倍于此二人,若纵之使归,其患远大于魏、赵二公子。王不如将其下狱,按律定罪。”
秦王遂将韩非下狱,命官吏治其罪。可怜韩非竟为自己的同门兄弟所害。在牢中,韩非欲见秦王自辩其冤,皆被李斯阻挡;欲上书自陈,书也为李斯所获,不能得见秦王。后来李斯使人送韩非药,令其自杀。
李斯何其毒也!所以说中国人喜好窝里斗,并非今日才有,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们李哥哥、庞哥哥(庞涓陷害自己的同门兄弟孙膑)已这样做了。看来中国人喜好窝里斗这个毛病,是从老先人那里遗传下来的。
不知过了多久,秦王又想赦免韩非,使人到牢中宣旨,韩非已死多时矣。秦王大悔,夸韩非之才,惜其已死,感叹不已!
李斯进曰:“臣举一人,姓尉名缭,深通兵法,胸中韬略远胜于韩非。”秦王闻听有人才能竟超过韩非,大喜曰:“果如是乎?其人安在?”李斯曰:“其人今在咸阳。然此人自负甚高,不可以臣礼屈也。”
秦王乃以宾礼召之。尉缭见秦王,长揖不拜。秦王答礼,置之上座,呼为先生。尉缭曰:“关东诸侯比之秦国,犹郡县耳,然六国若合纵一起抗秦,秦亦无可奈何。”
秦王曰:“欲散诸侯合纵,先生计将安出?”尉缭对曰:“今国家之计,皆决于豪臣,然豪臣未必忠智,不过多得财物为乐耳。大王勿爱府库之藏,厚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
秦王大悦,从其计,尊尉缭为上客,衣服饮食与尉缭同,常至尉缭房中请教破敌之策,在尉缭面前极为谦逊,从不以大王自居。尉缭私语于弟子曰:“吾观秦王面相,已知其为人。此人刻暴少恩,内怀虎狼之心。用人时能屈己待之,得志则必不能容人。我本布衣,彼竟以上客之礼待之,欲我为之并天下矣。倘若得志,天下皆为虏矣,况我等乎?不如弃之而去。”遂与弟子连夜离去。
秦王闻听尉缭离去,大惊,举止失措,如失左右手臂。急忙派人沿四面八方追寻,务必追回尉缭师徒。手下哪敢怠慢,遂出动王宫所有人马,不惜一切手段寻找。终于在天黑以前追回尉缭师徒。
秦王大喜,亲自迎接尉缭入宫,跪地对天盟誓曰:“嬴政将以天下苍生为重,一统华夏,尽快结束连年战争。今幸尉缭先生光顾秦国,此乃上天使孤完成先王一统大业也。寡人对尉缭先生绝对信任,并将言听计从,他的计策一定能使秦国尽快实现一统大业。若逾此盟,天诛地灭。”
尉缭感其诚意,遂答应留下来辅佐他成就大业。秦王遂拜尉缭为国尉,其弟子也俱封官。李斯因推荐尉缭有功,也被官拜廷尉。
于是,秦王嬴政文依李斯之谋,武赖尉缭之智,谋求一统大业。秦王嬴政13岁登基,19岁主政,赖李斯、尉缭二人出谋划策,更兼王翦、桓猗、王贲、蒙武、蒙恬等辈用武,加上先辈创立下的殷富家业,先灭韩、赵、魏,再灭楚、燕、齐。这样,秦国便在秦王嬴政26年,即秦王嬴政38岁时一统华夏,自称始皇帝。
秦始皇帝大宴群臣,群臣皆呼万岁。始皇意气盈满,十分得意。尉缭私叹曰:“秦虽得天下,而元气大伤,必不能长久。皇帝意气盈满,傲慢之心已生。吾不乘此时离去,祸必不可免矣!”遂与弟子一起离去,不知所往。
群臣请皇帝分封诸子功臣,始皇犹疑不定。李斯曰:“周朝分封诸侯,遂致兵戈连年,天子不能禁。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厚其俸禄,皆无尺土之封,以绝兵戈之源。”
始皇闻言大喜曰:“天下患战争之难数百年之久,皆因分封诸侯所致。今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廷尉之言是也。”
遂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不立子弟为王,不立功臣为诸侯,使后无战争攻伐之患。进李斯为丞相,诸将帅有功者赏万户、或数千户之封。
始皇帝命李斯明法度、定律令等诸项事宜。李斯奏曰:“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然诸侯国大臣、学子等皆各持己见,未必真心臣服,此诚不可不虑也。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王不如收天下《诗》、《诸子百家》等书以焚烧之,令国人不得以古非今,有敢以古非今,惑乱黔首者,灭族,官吏知情不报者,治罪。惟留医药、种树、卜筮之书。”
李斯这样做,实在过矣!俗语云:“古为今之师。”然李斯却焚百家之言,不准人以古非今,欲禁众人之口,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其实大谬矣。
李斯本出身黔首之家,富贵后竟以这样的办法对待百姓,愚弄百姓,欲使百姓变成愚昧无知的顺民,足见其心胸之狭窄。
始皇准丞相李斯所奏。接着,李斯开始制定法令,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车同轨,民同俗。
秦始皇本来就好大喜功,如今一统华夏,更是唯我独尊;遂大兴土木,修阿房宫殿,建造陵墓,修万里长城,以拒胡人,巡游无度,焚书坑儒。根本不顾百姓的死活,苛捐杂费日甚一日,各种赋敛,年年加重。百姓嗷嗷,不得聊生;民怨甚怒,只是惧秦之法,不敢言而已。然这种暴政只能维持一时,毕竟不能长久。果不其然,始皇死后,天下之民纷纷揭竿而起,使秦很快灭亡。
李斯辅佐秦皇,一统华夏,此不朽之功也。然他不仅不能劝主施行仁政,且让主焚书坑儒,严威酷刑,是其过也。至于始皇帝巡游无度,大兴土木,重敛于民,李斯竟无一言谏阻,致使民怨沸腾,秦朝很快灭亡,李斯之过大矣。
后来,李斯与赵高同流合污,沙丘政变,废长立幼,更是罪在不赦。所以最后李斯为赵高所杀,夷其三族,实在是咎由自取。
假使李斯辅佐秦皇一统华夏成功后,像尉缭一样,及时身退,岂能招致身首异处,灭族之祸哉!
李斯之祸,实贪富恋贵所致。这一点赵高看得很清楚,赵高知道李斯舍不得丞相之位,所以他对李斯说曰:“长公子刚毅而武勇,假若长公子扶苏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如果你我拥立胡亥为帝,足下丞相之位岂不安如泰山?”就这两句话,便击垮了李斯,使他甘心情愿与赵高同谋,立胡亥为帝。
李斯当年未发迹时,曾说过“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穷困”。正因为他的这种认识,才使得他把富贵看得很重。为了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与与赵高这样的人同流合污,以致最后遭受五刑,身首异处,三族被灭。
二世胡亥,荒淫无度,暴虐更甚,在搜刮民脂民膏方面更甚于秦始皇,但他比秦始皇要愚蠢得多,宠幸百无一能、只喜欢玩弄权术的赵高,自己不理朝政,一切大事皆决于赵高,致使天下大乱。这时大错已经铸成,李斯才想起向皇帝进谏,岂不可笑?
事实上,李斯也早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也就是说,在功成身退的问题上,他的智慧是有的,只是贪恋富贵,不愿从高位上退下来,才惹祸上身。
李斯的长子李由官拜三川守,其他儿女皆与秦公主或公子婚配。一次,三川守李由回咸阳探亲,李斯摆宴宴请百官,咸阳城所有的官员能来的全都来了,丞相府门前停的车马数以千计。李斯喟然长叹曰:“嗟乎!恩师荀子有云‘物禁太盛’。吾本楚国一布衣,当初连饭都吃不饱,如今官居百官之上,可谓富贵已到极点。物极则衰,吾不知所归矣!”
呜呼!李斯有此识而不能去,遂致灭族之祸,身首异处,岂不悲哉!
李斯对我们今人的启示
1.李斯本出身农耕之家,做了两年郡县小吏。他从粮仓中的老鼠与厕所中的老鼠之不同命运,联想到人,悟出人的命运也如鼠一般,处卑贱之位,纵有天大本领亦难有所作为。其悟性可谓深远矣。
于是辞掉郡县小吏之职,投靠大思想家荀卿,学习帝王之术。学成后弃楚赴秦,欲借秦之势,成就自己的宏图大志。其智慧绝非常人可比。
后又遭到秦王逐客令的驱逐,但他从不轻言放弃,遂上书秦王,请其收回逐客令,文风犀利,言简意赅,论据充分,事实清楚,终于感动秦王,废除逐客令,李斯也官复原职。
李斯遂推荐韬略过人、谋略深远的尉缭给秦始皇,并与尉缭一起,开始了秦王朝一统天下的宏图大业。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遂使天下归为一统,李斯官至丞相。
李斯的成功得益于他的借势而发,因时而为,不失时机,推荐贤才尉缭为其辅。
2.李斯遭灭族之祸,身首异处,非其智不足,实人之贪婪之心所致也。李斯早已意识到物极必衰,想到老师荀子的话‘物禁太盛’。自己从一布衣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可谓富贵极矣。
然不能及早身退,又不劝主施行仁政,且让主焚书坑儒,禁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严威酷刑,是其过也。至于始皇帝巡游无度,大兴土木,重敛于民,李斯竟无一言谏阻,致使民怨沸腾,秦朝很快灭亡,李斯之过大矣。
后来又与赵高同流合污,沙丘政变,废长立幼,更是罪在不赦。所以最后李斯为赵高所杀,身遭五刑,被夷其三族,实在是咎由自取。
看来人不能太软弱,更不能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不顾大局,一味忍让坏人,以至于与之同流合污,助纣为虐。李斯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丞相职位,一味忍让赵高,才铸成大错,身首异处的。
当你无法坚持正义时,千万不要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与坏人同流合污,否则,你会落一个向李斯一样的下场。当你对环境无可奈何时,你可选择离去。
3.李斯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是其功也。要不然我们今天陕西人看山东、河南人写的东西还要有翻译才行;陕西人到河北出差还得兑换货币,不能明白对方的度量衡是怎么回事。然而李斯让焚百家之言、焚书坑儒,则过矣。
当然,秦国刚一统天下,各国文人心里不服,私下议论纷纷,为了稳定人心,统一思想,适当采取权宜之计,临时管制,也未尝不可。但把它当作一项法律,严威酷刑,长期实施,则大谬矣。更不应该将百家之言付之一炬,愚弄老百姓,将持不同政见者全部坑杀,禁止言论、僵化思想。
看来李斯的度量实在太小,尽管辅佐秦皇成就了一统大业,但仍缺乏大将风度。他不知道民意人心,是不能靠高压,严威酷刑来获得的,更不懂得人的思想、言论是禁止不住的,而必须顺势而为。
4.李斯实在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年为了让秦王收回逐客令,使他留在秦国,他写下了“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的千古名言。
然而,在做事、容人的度量上不仅不像泰山、大海,他连小土丘、小溪流的风度都没有,禁百家之言,焚书坑儒,严威酷刑,陷害自己的同门兄弟等,无不体现他的小肚鸡肠。
尤其在对待自己的同门师兄弟韩非的问题上,显得嫉妒心极强,度量十分狭窄,他不仅让秦王将韩非下狱,最后竟亲自派人送药将其毒死。李斯之心可谓歹毒甚矣。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李斯应该懂。韩非也是倒霉,遇上这么个同门兄弟,竟然死在他的手上。再说李斯杀死韩非并非为了秦王,不是战场上的各为其主,不得已而杀死自己的同门兄弟。当时,秦国灭韩已成必然,韩非本想效力秦王,即使韩非是为韩国作奸细,也没有必要将其杀死,囚禁起来,足矣。可见,李斯杀死韩非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嫉妒心。
本来李斯善言,韩非善书,二人一同辅佐秦皇,互相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皆可成功,他却非要致其死地而后快。
难道韩非与李斯一起求学时,两人就有矛盾?莫非李斯家贫,韩非仗着自己是韩国公子,有钱有势欺辱过他?不得而知。要不然李斯怎能害韩非,却推荐尉缭呢?果如此,李斯之行为尚情有可原,但把人致死,也未免太过矣!
当然,李斯之所以推荐尉缭,也可能是他知道尉缭无心功名,将来不会对他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
假若李斯、韩非两人上学期间并无矛盾,韩非也没有欺辱过他,那他这样做,实在有点禽兽不如。他的境界比起鲍叔牙来,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首先,鲍叔牙与管仲原本素昧平生。而李斯与韩非有两年的同学之谊;其次,管子在几件事情上对不起鲍叔牙,如做生意时分金不公,打仗时总让鲍叔牙往前冲,射伤公子小白人中等。所有这些,都是管子对不起鲍叔牙。而韩非并未做任何对不起李斯之事;第三,管子被囚,齐桓公欲杀之,鲁侯也想杀掉管仲,只要鲍叔牙不吭声,管子小命便休矣。而鲍叔牙却千方百计营救管子,并把本属自己的相国职位让给了才智过人的管子,自己甘愿屈居其下。韩非出使秦国,本来活得好好的,无任何过失,也未对李斯的仕途之路构成任何直接威胁,李斯只是出于嫉妒之心,竟将其置于死地。
怪不得后来李斯被赵高所陷害,以至灭族,也未能引起多少人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