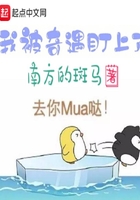白虎者,西方庚辛金白金也,得真一之位。此星大现,主国有刀兵征伐之事也。
秋凉似水。
夜渐深,已过四更天。
运粮的队伍前后绵延数里,行进缓慢,拉车的牛不堪重负,吐着舌头试图耍赖停歇,立刻鞭子就落到了脊背上,疼的牛抽动着鼻孔,哞哞的吼着奋蹄向前。
五十里路,若按平地走,不上两个时辰就可到达,但此地是山脉与丘陵交界处,上坡下坡,沟转路旋的,不歇脚的走也不见出路。薄雾时隐时现,露水也来的早,打湿了赶路人的裤脚,也湿滑了路面上的石子,不小心,脚下就是一个趔趄。
征调来的民夫每人都挑着一石粮食,白天赶路集结,晚上还要下力气挑担,走不上十里路,已是人困马乏,肚中饥渴,官吏兵士们来来回回的呵斥着,时不时还用棍棒抽打民夫,让他们加快脚步。
县尉骑在马上东倒西歪的,手里提着酒壶,没一会镶银丝的酒壶里一滴酒不剩,他还意犹未尽,打发小厮快马回县城去给他取酒。小厮去了半天还没回来,县尉口中寡淡,心下烦躁,瞧什么都不顺眼,身边的皂隶被他骂的狗血喷头。
县丞躲得远远的,骑着马来来回回的巡视整个队伍,他也着急,虽然五十里路不多,天亮前指定能赶到,不会误了差事,但他心里惴惴的,忐忑不安,总觉得这趟差事不那么安稳,这些民夫倒不会生什么事端,谁知道会有什么其他幺蛾子事蹦出来呢?
玉林寺的僧人们走在队伍的中间,一百多僧人和三百多庄客护送着一百辆牛车,他们承载着这支队伍运送任务的一多半量,这些粮食是玉林寺多年来的囤积,关乎前线将士生存,护送人员都是早就精挑细选出来的,都随身携带着兵械,以备不时之需。
王和十九郎徒步跟随,僧人们让王坐上牛车,王不肯,牛拉车已是汗流浃背,再说大家都是步行,那些民夫还肩挑背扛的,空着手已是心下不忍,他哪里还能去车上坐下。
午夜将至,夜更深了,月本在中天,此时却隐入厚云中,四野戚戚,秋虫不鸣,风停云驻,骤然闷热起来,民夫们纷纷咒骂起这鬼天气来,县丞却明白这不是好兆头,朝雾晴晚雾阴,一连几天都是天刚擦黑就起雾,今夜薄雾褪去却又闷热异常,闹不好骤雨将至。
他吩咐走下人前后呼应着,催促民夫们加快脚步,离县城还有一半的路程,最好雨来之前,大队进了城,人不挨浇粮不淋湿。
官吏和兵士们喝斥着,催促着,民夫抱怨着,牛喘息着,队伍中随着鞭子棍棒的落下,一阵阵的骚动,王看着凶神恶煞的兵士和皂隶们,皱着眉,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十九郎知道王是不满这些欺压人的举动,但这事不是他们该出头的,小声的拉了拉王的衣袖,劝了两句,王叹了口气,不再理会。
突然,前队传来噪杂声,王侧耳听,绝不是寻常吵闹,是惊呼声,还不是一个两个人发出的,由远而近的,眼见的众人纷纷闪躲,粮担和背驮散落一地。道路左侧的兵吏们也是七零八落的闪躲着。
是一匹马,是一匹剪了鬃毛束了马尾的官马,呼呼地喷着白气,蹄飞怒号的,呲着牙,甩着头,沿着官道一路劲驰,好几个兵吏躲闪不及,被撞翻在地。不少人想去抓飘扬的马缰绳,但似乎是看到了什么,像被烙铁烫了一般的缩了回去。
王看清了,众人惊恐的倒不是这匹马,一匹惊马是能使人惊慌,但还不至于让这些兵士们恐惧,他们恐惧的是马背上的东西,确切的说,那不是个东西,是一个人,更确切的说,是半个人,没了头颅和缺了半边肩膀的一具残尸。
喝醉了的县尉也听到了官道上的纷乱,刚刚睁开眼,举起手里的马鞭还想胡乱的抽上几鞭子,发发威,谁知那匹惊马瞬间就冲到了他的马前,县尉的坐骑是匹五色马,这种马本来就是打打马球,溜溜弯,春野秋湖旁泡泡妞用的玩物,乍一见疯了的同类,还有那扑面而来的血腥气,骤然也惊了,恢恢的嘶鸣着,后腿直立,前蹄腾空,县尉哀嚎着重重的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两匹马一前一后的疯跑起来,眼看就要到了运粮队伍的中队,这里可是一百多辆牛车,要是牛也被惊了,那可不是一两匹马惊了的小事,轻则车毁牛伤,重则碾压冲撞伤人无数,民夫们惊恐的连连后退。
玉林寺的僧人们倒还镇定自若,十数人立时就挡在了王的身前,为首的胖大和尚一声吼:“挡车!盖牛眼!”玉林寺的人们闻声迅捷各司其职,僧人挡在牛车前,庄客们握紧了牛鼻环,用笼布遮挡着牛眼
两名首善堂的僧人手持戒仗,跳到官道左侧,一左一右的分开,头匹惊马已然冲到他们身前,但见二人奋力挥仗,只听得“咔嚓!咔嚓!”两声,那马斜刺刺的摔落出去,马儿哀鸣不断,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惜两条前腿齐刷刷的断了。
紧跟着来的那匹马,受惊程度不如前马,但见同类摔落在地起不来,长嘶一声,前蹄在空中刨蹬着,被那两名僧人拉住缰绳,强按下马头,马儿咆哮着撂着蹶子,但还是被制服了。
电光火石之间,一场风波平息,县丞长长出了口气,他刚才被手下人拉下马,躲到路边的树后去了,眼见着玉林寺的僧人和庄客们临危不乱,训练有素,不禁心中暗暗称奇,想不到佛门禅地,居然进退有据,比那些兵吏和民夫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他哪里知道,玉林寺不仅仅是僧人修行之地,这年头,乱世之中,佛门也要自保,僧人皆习武练兵,山下田庄的庄客们平素也是要练兵的,别说对付流民山贼,就是真来个一两千的官军,也不见得讨得便宜。
县丞嘴里一迭声的感激之词,玉林寺众人也只是合掌唱个偈,并无过多言语,僧人们给王施礼后纷纷归队,等待前方号令,而王对县丞也只是微微点下头,县丞心说,这人也不是僧人啊,为何派头这么大,粗布衣衫的也不戴冠,却望之若观山林临沧海,不由得身上一凛,混迹官场的本能促使他上前去施礼,但却被那人身旁的童子挡住了。
十九郎拦下了县丞,小声提醒他速去查看那具残尸,并替王吩咐县丞,让大队停下,都歇口气,吃点东西等查明情况再行赶路。
那个素衫青年就让人不由得屈膝了,连他的童子讲起话来,虽然轻声轻语的,却不怒自威的带着不容抗辩的尊势,县丞一边嘴里诺诺的应承,一边心头打着鼓,他凭直觉隐约猜测这两位青年男子的背景一定深邃,后背上汗立时就溻透了内衫。
县丞虽然胆小,却通熟世故圆滑至极,当下一一唤过三班皂头,卫所哨官,命令严加戒备,看管民夫和军粮,他自己带着几个人去查看死尸和伤马,而那位县尉老爷,摔的不轻,站都站不起来,卧在下人铺的的席子上哼哼唧唧的。
不多时,已经查明,死尸虽然没了头颅,但从服饰和那匹伤马来看,应该就是回县城去给县尉取酒的那名小厮,这小厮是县尉来赴任时从京城带来的,得县尉之宠,平素里习的主人的狂傲奢靡之气,身上穿的配的都是县尉穿旧和赏赐的,这死尸身上正是那小厮的平日装扮。
是什么人下手如此狠毒?县丞一时判断不出,本地虽然有些盗贼和强人出没,但多为小偷小盗,长山县算是虞国腹地,离边境遥远,衍武帝登基后休养民力,施行减赋减徭之治,本地治安好的很,多年没发生杀人凶案了。
县丞一筹莫展着呢,十九郎走过来了。
王命十九郎来和县丞说几句话,县丞诚惶诚恐的把十九郎让到一旁。
“大人请了,我家主公命小的来带个话,烦请大人差人做三件事,一呢前方不远应是蒲林亭,亭长此时应在路旁守候,烦大人差人去唤亭长来问话。二呢烦请大人下令大队停止前行,暂不出发,大人不必忧虑误期之罪,自有人担承此事。三呢还望大人速差人四下里寻找溪流,多捞河泥。”
十九郎不紧不慢的说完,还关切的问县丞听清楚没有,县丞唯唯诺诺的点头哈腰的,表示听的很真切,等这年轻人才一转身走出几步,马上喊过手下来,一一嘱咐了三件事,催促赶紧去办。
玉林寺后山脚下是含玉亭,亭长就是玉林寺田庄的一个庄头,他此次也跟着运粮大队一起来,此刻正在玉林寺的车队那里听王的问话,去长山县县城,还要路过的蒲林亭的亭长,和庄头相熟,三天前就派了人去送了官报,通报了他们运粮队今日夜间通过蒲林亭,让亭长多备茶水。
按官制,蒲林亭的亭长应该出亭三里迎接,此地据含玉亭长说最多两里地就到蒲林亭了,却不见迎接的亭长或是亭卒,而县尉的小厮正是在那个方向被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