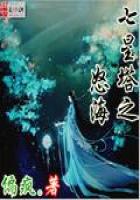1990年代以来势头愈益猛烈的全球化过程在一些学者中间引起新的焦虑,认为“全球现代性”已在迅速地改写世界历史,并日益侵蚀到人的记忆,对于各民族地区的历史记忆造成威胁。因此提出重视、挖掘地区性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当然主要指的是20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现代经验。确实中国自90年代进入全球化新时期,在文化上不啻换血。不少人怀恋革命年代,而通过文化生产转化为消费性的“怀旧”或“恋物”现象,骨子里已经“向革命告别”。不无吊诡的是,这一“另类现代性”理论根植于“后殖民”、“后认同政治”话语的文化批评视域中,旨在响应和对抗当下消除民族记忆的“全球现代性”,固然合理且紧迫。但这一“另类”指的是对于西方启蒙理性现代性的接受和移植,其理论资源有其片面性。这里的“现代性”,不外乎一种“永恒的现时”的迷思,肇源于西欧18世纪启蒙思潮,在“新纪元”或“现代”的观念中,蕴含一种人定胜天、自我作古的历史意识,遂声称与“传统”一刀两断。关于现代性理论名家林立,其中以黑格尔版本独领一时风骚。 尽管他认为德意志民族精神借历史过程而展开,在无限中完成自身既定之目标,但在黑格尔哲学体系里,“进步”、“革命”、“危机”、“解放”等重要概念却含有普世价值。 后来马克思把黑氏体系颠倒过来,强调“上层建筑”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更发展出一套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各阶段发展的理论,进而勾画出资本主义必然导向无产阶级全面胜利的理想图景。在1920年代末茅盾的“时代性”认识中已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素,也反映了当时“左派”知识分子的集体认同。
中国文学现代性不止一种,如果以地域文化“内视”的角度,对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涉及文化主体的复杂问题,就会觉得这个“另类”的范畴规定了某种主次的权力秩序,包含着如福科(Michel Foucault,1926—1984)所说的“排斥系统”(the episteme of exclusion)。如詹明信把“第三世界”文学看作“民族寓言”的论述广为人知。在后现代场景里,詹氏在同情地回顾鲁迅的民族情怀时,多少借他人之酒杯,对于美国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的失落不无感叹。这固然显示其难得的国际主义胸襟,但从某种全球景观中看20世纪中国文学,就未免见木不见林;他对鲁迅的卓越解读却重复了五四即现代的神话。
在西方“现代性”理论也众说纷纭,为中国文学的多元现代性研究提供丰富资源。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将现代性分为两种的说法,与上述崇拜进步、科学及理性的现代性相对的,是由波特莱尔所“非凡”、“原创”界定的“美学现代性”。波氏声称“现代性是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强调对美的感官的现时把握,所醉心的是都市“时髦生活的景观,以及成千上万游手好闲的人——罪犯与被供养的女人——在一个大城市底层浪荡的景观”。同一般自诩与传统决裂的现代主义者不同,波特莱尔的时间意识含有某种悖论,即在现时的美的探险中,对于“永恒”的艺术价值却抱“怀旧”之情。李欧梵先生在80年代就引用卡林内斯库而强调中国文学中的美学现代性,在其《上海摩登》中,对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在美学现代性的基础上更从日常生活和印刷文化的层面上发掘现代性内在机制。他举出像商务印书馆主编的《万有文库》等丛书、良友图书公司的《良友》画报等,对现代文化的建设产生重要作用,而其中体现的“现代性建构”就其启蒙及理性特征而言,与五四式的现代性追求有交合,也有区别,它并非诉诸革命的群众运动或乌托邦狂想,而在个人和民族国家之间扩大某种“公共空间”,致力于现代知识系统的建构、公民意识的培养及都市日常生活包括家庭等“私人空间”的想象。
在近年来文学研究地貌变动中,“国族想象”一语不胫而走,当归功于安德森关于“印刷资本主义”和“民族想象共同体”的论述。所谓“想象共同体”不仅有赖于个人对“民族”的想象,也属于某类“文化制成品”,首先是报纸和小说。 20世纪初在梁启超等流亡日本的改良主义者所主办的《清议报》上,频频疾呼“四万万同胞”,而此跨国杂志由现代交通之便迅速传遍中国内地,倾动朝野,实即体现了印刷资本对于“想象共同体”的建构和传播发挥了史无前例的作用。“想象共同体”理论在藤井省三先生的《鲁迅〈故乡〉阅读史》一书中得到出色的应用。当20年代初民国教科书中选入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时,意味着白话胜利取代了文言,而在这一“语言转折”的文化变革中,民国政府与新文学运动联手作战,印刷资本主义更立下汗马之功。令人惊异的是,这个短篇在此后半个世纪里历尽“正典化”之沧桑,却见证了印刷资本与民族国家建制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觉得安德森有关报纸和小说中“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论述尚有待探索。如果这个由“时钟和日历”计数的时间是伴随世界殖民主义而俱至的话,那么在中国场景里却与本土历法产生滑稽的、并非和谐的联姻。如在《申报·自由谈》中的“游戏文章”讽刺当局,而利用传统的时令节气作文章则是《自由谈》中常见的修辞策略,既迎合民俗,为一般读者所喜闻乐见,同时援引传统文学典故,作文体的戏仿表演。虽然这样的讽刺最终起到维护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作用,但其间在本土的时间意识中蕴涵着日常衣食住行的文化空间,并非“空洞时间”所能涵盖。换言之,安德逊理论应用到中国语境时,有一定的局限。
这种报纸的“批评功能”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可借重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的论述。哈氏认为,在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正处历史的上升时段,他们同贵族统治阶级作合法斗争时,如咖啡馆、沙龙、剧场等成为他们个人之间交换政见的“公共领域”,其间所形成的“公意”也通过议会、法院等机构付诸实现。 受此理论的影响,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批评的功能》一书将18世纪英国《旁观者》(Spectator) 等杂志看作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历史的局限,难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有的批评者指出,哈氏这一论说忽视了无产阶级或女性的公共领域;有的汉学家将之应用到晚清民初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争论。 但理论本身应当是开放的,就其应用来说,也应当将之与具体语境作必要的调整而限定其适用之程度。
在理解所谓“鸳鸯蝴蝶派”文学方面,我觉得对于中国式“公共空间”的探索仍有可为。这将投光于历史,纠正对该派仅生产娱乐文学的误解,并使研究不局限于“纯文学”角度的评价而引向更有意义的与印刷资本及其意识形态的关系方面。如王钝根(1888—1950)、周瘦鹃等主持的《申报·自由谈》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某种“公共空间”的批评功能。尤其是哈贝马斯说到像李查生的畅销小说《帕美拉》开拓了“文学的私人领域”。书中宣扬的普世人文价值,即从“自愿、爱的社群及修养”等方面培育资产阶级主体,与“公共领域”中自由运用“理性”的精神息息相通。若从这一“私人领域”的角度来看鸳蝴派有关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空间想象的言情小说,或许更能理解与为民族国家建构服务的文学“正典”之间的紧张关系。
的确,对于“全球现代性”作出见木又见林的回应是更为复杂的:在大力挖掘“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同时,也应当“重写”像茅盾所代表的文学现代性。虽然这一“宏大叙事”不等于“小说中国”,当然也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大潮中的一朵姿态横生的浪花,在民族国家及其主体的追求和建构中有多少英雄儿女为之捐躯献身,歌泣不止。这样的“重写”肩负双重任务:一方面响应全球文化冲击对地域历史记忆的威胁,另一方面体现本土的“问题意识”,对于文学“正典”作进一步的“去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历史讲话,更有利于对于“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挖掘。
书写“另类现代性”经验固然重要,关键的是如何充分挖掘本土的现代性矿源,脱离不了我们的历史记忆。无论是主流还是非主流、被压抑的,都如李欧梵所说的“历史的幽魂”:
我们来追溯历史,都是一种直线进行式的。他(指本雅明)认为应该进行一次历史意识的革命,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历史要从现在的立足点上来看,把现在的紧迫性、都市生活的紧迫性作为历史的前景来观察。他的一个理论就是:历史就像一个幽魂,当我们感受到很强烈的刺激和危机的时候,它就以一种阴魂式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回忆过去,没有时间的顺序,历史以一块块的幽魂、一块块的片断进入我们的世界之中。我们对历史的看法也是一样,不是把历史当成一种很客观的、很平稳的叙事。
在这里“历史意识的革命”启发我们思考怎样书写历史以回应当下的挑战,涉及事件、记忆、虚拟、再现、现代性反思、承认政治及自我身份等复杂问题。
本书在已发表的几篇文章的基础上改写、扩充而成,事实上仍在检验自己书写茅盾的最初构想,也是为了帮助读者在更为深广的视野中理解茅盾早期小说的复杂意蕴。尽管本书对历史脉络从理论、传记、文类、文学场域等方面作了多重复合的“浓描细写”(thick deion),然而历史的头绪欲理还乱,触及的问题,无论旧的新的,提出的恐怕多于解答的,何况不得不顾及研究的现状时,更难免顾此失彼。虽说是像重写文学史,但似乎在尝试作一种“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 的历史书写,即以文学为中心,而向文化研究的多元取径开放。文学研究当以读解其符号象征系统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为能事,对于认识一位文学巨匠来说,难在揭示其形式上的匠心独运,如本书试图读出茅盾小说中“时代女性”所蕴含的进化史观的典律和语码,如在短篇小说《创造》中如何通过空间与性别之间错位的巧妙表现而使读者认同其“革命”的隐喻。其表面上使用“家庭喜剧”的形式而颠覆时尚趣味及其代码也是作者为争取小资产阶级读者所用的艺术策略。对这些形式问题的探讨,我想比一般理解这篇小说“对女子教育失败”的主题性阅读或许来得更有兴味。这也是文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所揭示的不仅如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2—1988)所说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亦属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所从事的与形式密切关系的“感知史”(the history of perception)。在叙述20年代的思想、文化背景时,本书着眼于勾画对“长篇小说”形式有关的内在脉络,因此在章节安排上不像一般文学史的平铺直叙、条分缕析的写法,尤其最后一章围绕“乳房”一词作一种横截面展示,与现代汉语历史变迁、都市性文化、视觉与小说叙事等问题相联系,借此洞幽烛微,对茅盾小说的某些细节作进一步解读,同时也试图探索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方法的可能性,因此在章节安排等体例上不尽统一,叙述中或有前后照应或枝节横生之处,这些或许需要读者加以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