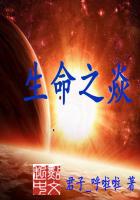其实这些批评家对“革命”的理解停留在内容表面,显得过于狭窄,茅盾的辩护也就事论事。如果从三部曲作为“革命加恋爱”的模式来看,无论是《幻灭》还是《动摇》都表现了作者的坚定不移的宗旨,即为了重构革命的美妙神话,使之成为人们的希望之旅,一再粉碎个人爱情及小家庭的梦想,这在《追求》中故技重演,却发挥至登峰造极的境界。小说一开头说同学会里,王诗陶、龙飞和章秋柳是“情场三杰”,并引用法文Les Trois Mousquetaires,即与大仲马的名作《三剑客》相附会。王诗陶是“三角恋爱的好手”,章秋柳是“恋爱专家”,而龙飞是个“恋爱悲剧”论者。从一开头就这样突出这三人,让读者吊足胃口,其实是虚晃一枪,整部小说很少讲到龙飞和王诗陶的恋爱故事。但从结构上看,小说大部围绕着三对恋人,即以章秋柳与史循为主,张曼青与朱近如、王仲昭与陆俊卿这两对为辅,从教育界、新闻界乃至跳舞厅、酒馆等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层面,表现了“大革命”之后的都市青年不甘沉寂,重又燃起希望,努力加入现存机制,改良社会,同时也实现他们爱情及小家庭的梦想,而最终结果都一样:与现状的妥协皆属徒劳,而难免再度的幻灭。尤其是小说的结局,王仲昭突然接到电报说他的未婚妻遭险而危在旦夕,他本来脆弱的小算盘也被无情的碾碎,这一笔未免留有刻意斧凿的痕迹。其所揭示的现代生活的不可预测性,却必然落入历史前进的铁腕,另一方面爱情被表现为猥琐、病态的领域,从而使男女“私情”失去了文学表现的正当性。由此至《追求》已经暗中完成了文学“现代性”转向“革命性”的内化过程,这对于“革命文学”的贡献便难以道里计。
容易被忽视的是,失败之处却意味着成功的开端,即在“时代女性”的形象塑造中,作者进一步探寻其与革命叙事的动力关系,迂回而坚定地呈现更为清晰的内在线路,在技巧上的累积和进步也可圈可点。不像《幻灭》和《动摇》中担任配角,此时章秋柳被置于舞台中心,一面接续了慧女士的角色,用大段独白表现其心理时间,让她的思想和行为主宰叙事的主线,又像孙舞阳那样,在叙事结构上牵制全局。作者更面对挑战,直取擒贼擒王的手段,让章秋柳和残忍的时间遭遇,更明确地在她的时间意识中注入“未来”的理想,不像慧女士单单诉诸本能与享乐的欲望,而通过她的拯救史循而凸显精神升华的伦理主题。但这毕竟是章女士一己的理想追求,更何况混杂着都市的逸乐与颓废,最后也功败垂成,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
透过心灵之窗所展示的章秋柳,像慧一样“善于恋爱”,敏感而激烈,极端的个人主义,但她是反叛型的,具有社会关怀和同情心。在写她去探望病中的“同志”王诗陶那一段,极其戏剧性地表现了她的出格形象。早在《幻灭》里,我们见到王和东方明相爱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何等兴高采烈,朝气蓬勃,但现在革命潮退,王回到上海,东方明已经牺牲,她却怀了孕,此后前景一片黑暗。王诗陶不想屈从“自嫁”或“被嫁”的公式,仍希望能把握自己的未来,想“把孩子打掉,海阔天空去过奋斗的生活”。章秋柳回答说:
我是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没有。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人生,甚至理想的恋爱,都是骗人自骗的勾当;人生但求快意而已。我是决心要过任性享乐刺的生活! 我是像有魔鬼赶着似的,尽力追求剎那间的狂欢。我想经验人间的一切生活。有一天晚上我经过八仙桥,看见马路上拉客的野鸡,我就心里想,为什么我不敢去试一下呢? 为什么我不做一次淌白,玩弄那些自以为天下女子皆可供他玩弄的蠢男子? 诗陶,女子最快意的事,莫过于引诱一个骄傲的男子匍匐在你脚下,然后下死劲把他踢开去。
说完这番话,她提空了右腿,旋一个圈子,很自负的看着自己的袅娜的腰肢和丰满紧扣的胸脯,她突然抱住了王女士,紧紧的用力的抱住,使她几乎透不出气,然后像发怒似的吮接了王女士的嘴唇,直到她脸上失色。
这里重现了慧女士的性格特征,但更具歇斯底里的爆发力。但是当王诗陶告诉她,另一位同志赵赤珠事实上为了生计已经在街头“淌白”,操皮肉生涯时,章秋柳受了极大的震动,愤恨之极:
她回到自己的寓处后,心里的悒闷略好了几分,但还是无端的憎恨着什么,觉得坐立都不安。似乎全世界,甚至全宇宙,都成为她的敌人;先前她憎恶太阳光耀眼,现在薄暗的暮色渐渐掩上来,她又感得凄清了。她暴躁地脱下单旗袍,坐在窗口吹着,却还是浑身热剌剌的。她在房里团团的走了一个圈子,眼光闪闪地看着房里的什物,觉得都是异样的可厌,异样的对她露出嘲笑的神气。像一只正待攫噬什么的怪兽,她皱了眉头站着,心里充满了破坏的念头。忽然她疾电似的抓住一个茶杯,下死劲摔在楼板上;茶杯碎成三块,她抢进一步,踹成了细片,由用皮鞋的后跟拼命的研砑着。这使她心头略为轻松些,像是已经战胜了仇敌;但烦躁随即又反攻过来。她慢慢的走到梳洗台边,拿起她的卵圆形的铜质肥皂盒来,惘然想:“这如果是一个炸弹,够多么好呀! 只要轻轻的抛出去,便可以把一切憎恨的,亲爱的,无干系的人,我,物,一齐化作埃尘!”她这么想着,右手托定那肥皂盒,左手平举起来,把腰肢一扭,模仿运动员的掷铁饼的姿势;她正要把想象中的炸弹向不知什么地方掷出去,猛然一回头,看见平贴在墙壁的一扇玻璃窗中很分明的映出了自己的可笑的形态,她不由得心里一震,便不知不觉将两手垂了下去。——呸! 扮演的什么丑戏呀
这里的叙事切入了政治层面。东方明“受命令要下乡去”,应当是去搞农民运动而牺牲的。赵赤珠也是《幻灭》中的人物,和史俊同为一对革命恋人。大革命失败,两人回上海,“穷到半个铜子都没有了,又找不到职业;他们是不准革命的;因此就断了生路。”所谓“不准革命”在当时的阅读语境里,乃指不准从事国民党的“革命”,隐含他们受当局“白色恐怖”的迫害。这就是茅盾谈到的在写《追求》期间,因为听到有关“清党”以及同志牺牲的事而“痛心”、“发狂”,在小说中通过章秋柳的愤怒发泄,曲折表达了对共产党的同情。但我们可看到小说是在都市背景里被阅读的,王诗陶和章秋柳之间讨论她们的未来,不外是日常生计、孩子、婚姻及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一切都有关都市新女性的生存困境及个人发展的问题,直到40年代仍是张爱玲、苏青的不竭话题。
作者自白《追求》自始至终贯穿着作者的“悲观主义”,是“一件狂乱的混合物”,这集中表现在章秋柳这一人物身上。茅盾从革命大风大浪中退到书斋写小说,据他自己说,“因为那时适当生活 ‘动’ 极而 ‘静’,许多新的印象,新的感想,萦回心头,驱之不去,于是好比寂寞深夜失眠想找个人谈谈而不得,便喃喃自语起来了。”可以想象作者在写到上述章秋柳的带有歇斯底里的戏剧性表现时,不光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而这种“喃喃自语”也大有变成“狂乱”的呓语的可能。作为“时代女性”的艺术形象,章秋柳比慧女士、孙舞阳更复杂而矛盾,也更含有作者难以抑制的激情爆发。她那种“无政府主义”的破坏倾向与她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形成鲜明反差。就在上述的一幕之后,她自言自语:“完了,我再不能把我自己的生活纳入有组织的模子里去了;我只能跟着我的热烈的冲动,跟着魔鬼跑!”
事实上,《追求》的写作过程出现了失控的症状。该小说作于1928年4月至6月间,据茅盾的《回忆录》:“到了四五月间,我却完全被这些不幸的消息压倒了,以至我写的《追求》完全离开了原来的计划,书中的人物个个都在追求,然而都失败了。”所谓“不幸的消息”指的是在“白色恐怖”下革命同志的被捕、牺牲,他的悲愤心情在上述章秋柳的描写中得到曲折的反映。虽然我们不清楚他“原来的计划”是怎样,但不无反讽的是,此时的章秋柳只能“跟着魔鬼跑!”似乎和作者的政治义愤背道而驰,至于她跟着魔鬼跑到何处,接下来怎样,当然会使读者好奇。不过,的确在此后的情节中,秋柳的“魔”性如无轨列车一直引向“剎那间狂欢”的性高潮,但另一方面——我想同一般对《追求》的负面理解唱点反调——出于作者对魔性的殊死反抗,却妙笔生花,挽狂澜于既倒,揭示了她的“神”性,让她穿上革命的时间意识的盔甲,展开其自我超越亦即茅盾的自我救赎之旅,最后极其诡异地导致了对于都市欲望的“否定之否定”的悲壮结局。同时我想指出,在这一段失控的叙事中,通过章秋柳表达了作者对于造成“大革命”失败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反思,这就有必要回到《追求》的写作环境及历史脉络,揭示一些不曾为学者注意之处,作一些解码工作,或更有助于对于章秋柳这一角色的理解。
茅盾《回忆录》中说到在写《追求》时,所听到的“消息都是使人悲痛,使人苦闷,使人失望的。这就是在革命不断高涨的口号下推行的 ‘左’ 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各种可悲的损失。一些熟识的朋友,莫名其妙地被捕了,牺牲了。对于盲动主义,我与鲁迅议论过,我们不理解这种革命不断高涨的理论”。所谓“盲动主义”涉及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根据近年来对于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期间扮演的角色的解密研究,1927年间在由斯大林、布哈林控制的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路线在如何开展群众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重要分歧和激烈争论。在北伐进入高潮的形势下,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一面继续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一面迅速发动农民运动,实行没收土地等政策,使“一切权力归农会”,试图建立苏维埃式无产阶级专政,在与国民党合作的框架中掌握北伐革命的领导权。但陈独秀认为中共及其工农力量还不足夺取政权,并提出要扩大势力,必须对小资产阶级作出让步。同样在开展农民运动及没收土地政策方面,他主张向小地主作让步。陈独秀认为,暴风骤雨式的湖南农民运动打击面过大,连亲共的国民党“左派”也受到惊吓。而且,当汪精卫觉察到斯大林的策略时,决定“清党”,同共产党决裂。事实上莫斯科的方针与“大革命”失败有直接关系,但事后斯大林仍颐指气使,责怪错误在于中共未忠实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
在“大革命”中,茅盾自言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对于共产国际操纵国共合作的内幕所知有限,但痛定思痛,对于当日的“左”倾“盲动主义”则耿耿于怀。在描绘了上述章秋柳的愤激之情之后,作者意犹未尽,又写到王诗陶的影像如噩梦般缠绕着她:
她无可奈何的阖了眼,一些红色的飘动的圆圈便从眼角里浮出来,接着又是王诗陶的惨苦的面容,端端正正的坐在每一个红圈上。然而这又变了,在霍霍地闪动以后,就出奇的像放大似的渐渐凝成了一个狞相。呀!这是东方明的咬紧牙齿的狞相!红圈依旧托在下面,宛然像是颈间的一道血线。章女士惊悸地睁开眼来……
她恨恨的想,用力咬她的嘴唇,皱紧了眉头。现在的情绪,矛盾纷乱到极端,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她痛切地自责太怯弱,但是血淋淋的红圈子始终挂在她眼前,她的光滑的皮肤始终近于所谓“毛戴”,她赤着脚乱走了几步,又机械的躺在床里,对天花板瞪眼。她努力企图转换思想的方向,搜索出许多不相干的事来排遣,但是思绪的连环终于又倔犟地走回到老路上,她几乎疑惑自己的神经是否起了变态,在对她的自由意志造反。……因为这是高热度的同情,所以不能挥去血淋淋的红圈子,所以那样惊悸,所以流入于怯弱么?
这一大段梦魇及心理刻画表面上是由王诗陶的惨境及赵赤珠的“淌白”所引起的,伴随着章秋柳对于享乐的人生观的自我质询,这些对于当日上海“新女性”来说,具有普遍的意义。但在她的梦魇中出现的东方明及挥之不去的“血淋淋的红圈子”显然是一个具政治含意的象征指符,自然会使人联想到革命志士的鲜血或国民党的血腥屠刀,然而对“红圈子”这一意象的丰富内蕴稍作推敲,也何尝不是指使茅盾痛心疾首的“左”倾“盲动主义”? 章秋柳所表现的恐惧折射出茅盾在写作《追求》当中的鲜活感受,也即对于1928年继续发展的“盲动主义”的反应,这不仅是指瞿秋白,恐怕也包括其他人。在小说里东方明是“受命令要下乡去”,意味着他牺牲于农民运动之中,与胡也频、柔石等遭国民党捕杀的革命烈士有区别。
在三部曲里,《追求》最富政治性,而对章秋柳的艺术表现也直接牵连到50年代的政治实际。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刻画章秋柳的大段引文在1954年的修订本中被完全删去了。这“红圈子”的噩梦段落为三部曲与“革命”的直接联系提供了重要见证,即不光是对“过去”的反思,也是对“当下”的批评。而且对于理解章秋柳这一人物身上所体现的都市与革命的双重主题的剧烈冲突,也极其重要。这一段被删掉,或许也与那个带引号的“毛戴”有关,指的是什么,令人费解。
在茅盾《回忆录》中并不讳言1927年对于“工农运动过火”的反应:“当时农运 ‘过火’ 之说早已传播,我们也知道党中央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陈独秀的,一种是瞿秋白支持的毛泽东的,而且还听说这两种意见反映了当时在武汉的国际代表之间的不同态度。”茅盾的反应是一面“感到由衷的欣喜”,一面也“存有疑虑,譬如把农民家中供的祖宗牌位砸了,强迫妇女剪发,游斗处决北伐军军官的家属等。尤其对后者,我们议论较多,认为我们现在手中还没有军队,万一这些军官反到蒋介石那边去了,局势就很困难”。而所谓“工农运动过火”,这是陈独秀的看法,也是《动摇》所描写的。尽管茅盾对反动派口诛笔伐,但以情色的讽喻描绘了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如上文言及的癞头农民瓜分地主小寡妇,即为一例。
有一个细节反映特定历史境遇的语言使用,也关乎章秋柳在革命与恋爱上的选择,即章秋柳看到被戏称为“迭克推多”(按:英语dictator,即“专制暴君”) 的曹志方在十字街头演说,遭到旁人指斥:“呔!反动派好大胆! 敢来扰乱后方秩序么?”这里“反动派”在修订本里作“共产党”。原本的“反动派”一语表现了当时一般人所认同的“革命”历史语境,就像上面提到赵赤珠和史俊是“不准革命的”,也属同样情况,不同的是“不准革命的”出自叙述者之口,在修订本中被删掉。后来曹志方向章秋柳求爱,并要她跟他一起去做“土匪”。他说:“除了做土匪,还有更快意的事么?……我只想出一口闷气,痛快的干一下。”这里的“土匪”一词在公共流通中,通过历史语境,已产生新的特定含意。在《追求》中,曹志方与张曼青、王仲昭截然不同,他显得蓬勃向上,最富革命造反精神,当时有的女读者表示:“我爱曹志方,我也爱章秋柳”,觉得章秋柳爱上了行尸走肉的史循,很不值得,因此“盼望作者把她的梅毒医治好了,叫她同曹志方结婚,那么,《追求》就算是 ‘追求’ 得有出路了”。然而章秋柳不愿意跟曹志方去当“土匪”,可理解为她的小资产阶级的局限,也出于她对自己前途的选择。
谈到三部曲的政治性,在茅盾那里,不能忽视的是文学的中介功能。正如他转向文学,不光离开了政治实践,他对“大革命”失败作反思,目的在于使“革命”重新获得某种普世的意义。而且在驰骋于想象之际,必定受到文学的范式、典律和代码的制约,甚至写到情之所纵之时,不免和主观愿望相违背。《追求》所表现的政治倾向不一定为党内某一主义或路线张目,则转化为意蕴丰富的文学形象及某种文化姿态。后来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为三部曲作辩护时,声称要把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力量,而他写小说也抱着争取他们的目的。这听上去像是为陈独秀的小资产阶级路线招魂,然而陈在1927年7月已被罢职,所以与其说是在文学领域中坚持陈独秀路线,毋宁是像章秋柳拒绝曹志方去当“土匪”一样,乃是一种人性的姿态,即不主张激进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