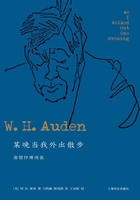茅盾写三部曲的内在紧张,在《追求》中的章秋柳身上得到激情的迸发而达到世纪末式的辉煌,而他的现代主义的美学探索亦臻至极致,尽管行将就范,臣服于“历史必然”的铁律。对此时的茅盾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英雄主义的表现,为给他的“自然主义”画上悲壮的句号,或更确切地为自然主义完成自我的“救赎”,虽然结果是同归于尽。如果说,从慧女士到孙舞阳,作者试图淡化她们“肉感”的负面意义而使她们无论身心两方面都与革命更达到精神上的合一,那么在章秋柳那里,茅盾直接使用她的肉体作为“革命”的祭牲,在时间框架中担任消解反动的“过去”而成为充满希望的“现在”的桥梁。这一时间意识的探索使作者经历了政治与美学、道德与激情之间的剧烈冲突,甚至陷于身心交瘁的境地,因而对他此后的创作带来严重的转折。
《追求》见世后,横遭批评,如钱杏邨认为书中“长于恋爱心理的描写,对革命只把握到幻灭与动摇”,而“章秋柳这个女子,是具有世纪末的痼疾的,是病态的”。“这种作品我们是不需要的,是不革命的”。因此这部小说的“革命”意义一向被低估,其在三部曲中内在逻辑的延伸以及其间的复杂与吊诡之处亦未得到充分关注与诠释。茅盾自己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对于左翼批评,作了低调的自我辩解,其修辞的暧昧之处颇值得玩味。他承认当时写三部曲的幻灭、悲观和消沉情绪,在《追求》中达至顶点:
……因为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这是因为我在那时会见了几个旧友,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你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也许会因亲爱者的乖张使你失望而发狂。这些事将来也许会有人知道的。这使得我的作品有一层极厚的悲观色彩,并且使我的作品有缠绵幽怨和激昂奋发的调子同时并在。《追求》就是这么一件狂乱的混合物。我的波浪似的起伏的情绪在笔调中显现出来,从第一页以至最末页。
但即使虚心面对批评,茅盾还是要“固执”地声称“很爱”《追求》,的确从政治和美学两方面来说,这部作品对于作者的存在都异乎寻常:“人家说这是我的思想动摇,我也不愿意声辩。我想来我倒并没动摇过……”“同时我仍旧要固执地说,我自己很爱这一篇,并非爱它做得好,乃是爱它表现了我的生活中的一个苦闷的时期。”然而他又认真忏悔:“我很抱歉,我竟做了这样颓唐的小说,我是越说越不成话了。但是请恕我,我实在排遣不开。我只能让它这样写下来,作一个纪念……”我们也许要问:“实在排遣不开”的仅仅是悲观消极? 其中还包含写作的冲动,甚至某种期待的满足? 为什么仍然“很爱”这样“颓唐”的“表现”? 为什么对于人家说他“动摇”又颇感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