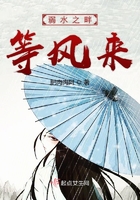一转及此,古宓立时感觉到额际渗出一层细密,并有顺着脸颊流淌的趋势。
不加护短的讲,跳舞对于古宓而言,还真是有一丁点困难。
古典舞,古宓一时起兴倒曾学过,但也仅限于两天学期记录,一不小心崴脚后再没敢深入,而那些一知半解的旋转、翻身、弹跳节奏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况且,这场合,要跳也该是那种极致狭义的巫舞吧?
巫舞,嘀咕着这个词,古宓暗忖着,顾不得形象地咧嘴做个深呼吸,吹一口垂遮于眸的那缕发丝,面冲着那透射着点点霞彩的阴晦天际,本欲无力的耷拉下脑袋,不料这个动作做的过度了些,眼前光线瞬的一变,眸底登时一闪而过几颗亮晶晶的碎星星,脚下也随即一软,尚未来得及搭手抓扶住什么,身体已经一个踉跄向后跌坐而去···
穿了就穿了,原以为赚取了个勉强算得不错的头衔,未曾料想,费劲周折至此,一谷之主竟是巫合之主,巫主也就罢了,不就是个名号?常言道,死要面子活受罪,为了异代过活,可以一忍再忍,但这巫舞,身为清白人家的好女儿,众目睽睽之下,该怎样扭来扭去?
种种这些,方是古宓真正纠结不清的一系列问号,即便是向后跌倒的那一刻,脑壳里也照旧在搅扯这个闹心的破事儿。
当然,古宓这一跌,势必会跟着跌倒一大片。
这一大片,可想而知,当然不是一大片人,而是一大片眼睛。
毕竟,台面之上,杵立着的本就无几人,空间大的很,根本不会祸及到她人挨摔,加之,那个年代尚无眼镜,没有就是没有,就像古宓自认为的道理一样,咱是好人家的女儿,总不能凭空捏造跌破“眼镜”吧?
况且,民间某个犄角旮旯有所流传,曰:溺谎,言繁者,易,偶遭雷劈之遇。天大地大,过活最大,清白的过活,尤为上上大。
但是,这一跌,现场的情势,倒果是随之不容乐观了。
白玉栏杆外,拥候的是一谷之民,从襁褓到拐杖。白玉栏杆内,颔首的是一谷之祀,从主祀到长老,不论老弱病幼,不分尊卑贵贱,古谷几辈子传延至今的一百八十三名后人,凡筋骨能参与者,除去那一落逃新郎,一一列示在席。
所以,一见这新上任的一谷之主,于大典之上,青天晨曦之下,正欲身献巫舞之际,忽的没一点预兆地来了个倒趔,单是用后脑勺想一想,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效该多难言喻其撼罕性。
而当事人自己,这会处在先前那一连串的混沌之中尚未回得过神,绞尽脑汁冥思苦想这祭祀之上的巫舞到底该怎样上演,是不是像极那些影视剧中跳大神者,抡着一根所谓的法器踮左脚翘右腿嘴里念念有词招摇打幌子,之余,心头慢慢掺杂起一波更胜一波的抱怨。
双手捧着额头,古宓耷拉着脑袋,方才那份本欲一扫阴霾的精气神全没了踪迹,不经意瞥见吊挂在脖颈的那条水琉璃,心中更觉甚是憋屈,当下便咬着牙恨恨地使劲揉起自己眼睛来。
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滴泪,成此生怨,该是怎样一种悔断肠的恨,怎样一种无以泄的怨,方可羽化得了这种不命结劫?
被摄来这几个日头的煎熬,古宓觉得,该忍的,忍了,不该忍的,貌似也已做过忍让,自认,耐性已经熬到了极限,什么谷主什么巫女,这些原本就不关己事,跟自个八竿子打不着边,何况本就是个空有其名的假头衔,处处受刁难没得半点自主权,赶鸭子上架似得,此时此刻受够了,既然可以这样稀里糊涂穿过来,就一定可以原样穿回去。
偶,只是想回去,想要回家而已,回去自己原属于的那片空间,哪怕要历经更多,也无所谓,不想再在这异代遭混沌之罪,偶只是单一的想回归原轨道,回去偶自己的家。
紧紧握着那粒水琉璃,古宓越想越气,手上的动作不自觉愈发加大了些气力,没几下,眼皮就有了肿胀感,瞳孔也有些微涩,只是,眸子眨了又眨,合合闭闭直扯得太阳穴生疼,愣是没从眼眶挤出什么东西,鼻头反倒有了酸酸的反应,仿似要有液态物体外流趋势。
人家说,眼鼻相通,古宓抹一把鼻下人中,再摸摸自个眉眼,不晓得为何这个惯言的通效说法偏偏于己身难以应验,外因内因主观因素客观因素都具备的此时此刻,理不透何以想哭都找不到腔调,只是想掉颗眼泪,一滴就足够了,把这一切结束了,哪怕回到原点处须得承受失恋的苦涩,如此简单的一件事,它为什么就变得复杂了呢?
再说雉儿,不明就里瞅着自家主祀踉跄着后跌,一时更是傻了眼,条件反射般暗叫一声“谷主···”,嘴巴张了又张,嗓子愣一个字没能发出音。
在古谷,新主大典,巫舞相较于整个环节而言,可谓其中最具压轴性的一棒。依祖规谷制,献舞之人,当为谷主,原因有二:其一,舞,不是一般的舞,而是巫舞;其二,巫,不是一般的巫,而是巫主;两者交之,巫舞合一,方预示祥瑞之气,佑民避疾,护谷祈福,天礼、地礼、谷礼通之,三望、五祀、七巫成之。
对此,古谷之人明了,然而,古宓并不知情,在她现在看来,这根本是一场闹剧,而且是胡闹之剧,较之自身来讲,甚至是一场悲剧。
暂且不论穿前怎样,酸甜也好,苦乐也罢,至少,那是个通透的世界,而穿后,在这一方境外之地,一切没了谱,没了原则,一环一环,每当自觉解开一点点迷惑时,死结着的一扣扣链锁总会相反系得更杂乱,故此,她恼了,恼到脑海中只有归去的残念。
“谷主,何故受惊?”抖抖衣袖探出玉手,东菱主祀微欠身,掩去眉间那抹异色,率先打破空气中流动的不寻常气氛,淡淡开口道,“宓妹妹,可有损及?”
后背硬生生撞击到宗祠那扇厚重木杉面漆朱门框檐,身体随即坠滑,不偏不倚一屁股跌坐在隆起足有四十五公分的那道门槛上,古宓方呲牙咧嘴疼过劲,正为努力了半天却挤不出丁点眼泪一事逼得几欲发疯,乍一听这半冷不热半温不火怎么品怎么夹带嘲讽的几句话,压抑着的情绪顿时涨潮般失控。
“无碍,不劳费心,猫哭耗子假慈悲,走远点,讨厌你知不知道?全是因为你,少假惺惺作态,偶厌恶你至极,Goout!”
过火的一气吼完,古宓一把打开那双伸向自己的水形手,径自拽着门框站起身。余光捕捉到某人花颜迅疾一闪而逝的那份仓促,古宓嫌恶地哼一声别过头,没好气地拍了拍搅成团的衣襟,乱七八糟扯正踩在脚下的曳地丝衫,临了不忘毫不吝啬杏眸圆瞪着补奉一记自认的杀伤力十足的白眼。
见状,东菱主祀面上瞬的一滞,挂着的浅笑难掩地一黯,弯曲的葱指略僵合拢成搭握状时,指甲一点点嵌进掌心,刺痛了麻木的知觉。
她东祀,加上这一辈,已经暗暗隐忍了三代,次次均以这种不变的烂说辞施压被迫放弃参选资格,这一回,依旧如一,老古怪们一个个轮番前来言喻木牌占卜出的那一套神鬼之说,无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她东菱以大势为先,自甘放弃这谷主位子,殊不知,自己在乎地根本不是这简单的一席之位···
如此想着,东菱主祀敛隐起眉间那抹不易察觉的神色,袖口里的指甲却深深嵌进掌心,既然选了她西宓担此重任,为了堂而皇之的大局,她东菱可以成全,只希望,有朝一日,千万别回求,不然,作为一个自认并不大度之人,貌似甚难料想会怎样接纳那些驳蔑斥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