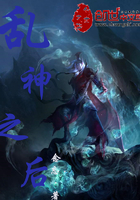还没有走到河边。你就听到了古尔图河在喊,在叫。象是一支千军万马的队伍在向什么发动攻击。你等不及走到河边,你举起望远镜。你看到了千军万马,它们是裹着黄沙泥土的水浪。它们一浪高过一浪,一浪大过一浪,正在向一道阻止了它们前进的大坝发动着攻击。
站到了大坝上,你的身体能感到大浪起落时带起的水雾。你看到平整的坝面上,散乱着被大浪抛上来的残树断草,你还看到了一只没能逃跑掉的黄羊的尸体。你踩在大坝上,好象觉得大坝在微微地晃动。
这道大坝,是你带着人修建起来的。你太知道这道大坝的重要性了。在旱季在枯水期在一年里的大部分日子里,它显得没有什么用处,甚至有点多余。但是到了七八月份,到了洪水期,它就和生死存亡这样的大事密不可分。
如果没有这条大坝,或者说有了这条大坝,又让洪水把它冲跨,那么他们建起的房子开出的地种出的庄稼,将在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古尔图会马上又回到洪荒的年代。还有人,将近三百个男女老少,也不知会有多少在突然来到的洪水中无处逃生。
这道坝是生死坝。这是一场战争,敌人就是面前的洪水。这道坝就是决定胜负的阵地。你目前只有一个任务,带领你的部下,打退敌人的进攻。你喊来了六个人,他们是队上的干部。一个副队长,一个指导员,一个副指导员,还有三个排长。
你们七个人站在大坝上商量怎么样来打这一仗时,看到了正在河边转来转去的老朱。开始他没有看到你们,也走上了大坝。等看到了你们他站了下来。你们也看到了他,可没人给他打招呼。他只是个兵娃子,还是个犯了错误的兵娃子,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在古尔图发生的大事中起什么大作用。你们看着他,没有理他。老朱还不算太笨。看出你们眼神里表现出的意思。老朱转过身,下了大坝,向营地走去。
走在营地中间的纵横交错的小路上,老朱看到了老根的房子,他站了一会,看了那房子一会。他没有再往前走。他向右边绕了个弯。避开了老根的房子。他想他怎么也得提一只野鸡去啊。上次在老根家,老朱就看出来了,老根和小凤很喜欢吃野鸡。
你下了命令,队上的男人和女人全来了。你要指挥他们打胜这一仗。他们的武器不是枪不是刀,而是坎土曼铁锨还有推车挑筐和草袋。有句老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让大家把离大坝不远的一座土丘挖掉,搬到大坝上来。让大坝再增高一米,那样大水就不可能越过大坝冲到营地和庄稼里了。
从早上干到晚上,又干到第二天早上,大坝眼看着高大起来,直到你觉得不会有多大问题了,你才让大伙回去休息休息。你说谁也不能脱衣服。睡着了也得一只眼闭着,另一只眼睁着。只要听到钟声要马上赶到大坝上来。你还让女人们把家里生活必用的东西收拾好,准备让西边的沙漠里转移。
不是大坝已经加固了吗,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别人可以这么想,你不能这么想,咱共产党咋打下来的天下,有一点你作为一个基层的指挥官不止一次听上级首长说过,战略上要藐视敌人,但战术上一定要重视敌人。这道大坝看起来很牢固,但在这样凶猛的洪水面前,一个小小的蚂蚁窝一个老鼠洞,就可能成为洪水的帮凶,让洪水把大坝冲垮冲毁。我们的失败往往是因为轻敌和麻痹大意。
不能犯这样的错误,这样的错误会毁掉太多的东西。你让三个排长各带一个五人组成的小组,每个组在大坝上守护巡逻八个小时。你说你也不离开大坝。你就在离大坝不远的沙土地上,让人搭了个草棚子,作为你的临时抗洪指挥部。以便随时处理大坝上发生的紧急情况。
老朱是其中一个巡逻守护大坝小组的成员,选中他主要是看他壮实如牛。
一个白天过去了,大坝稳稳地立在那儿,一点事也没有。从大坝上往古尔图河的上游望过去,好象洪水也小了一点。你松了一口气。站在你旁边的人也跟着你一起松了一口气。如果说,再过一天还没有事,那么这场战役,你肯定是赢了。不过,你对三个排长说,你们盯着点,水火无情,可不敢有一点儿戏。
你的了不起再一次得到体现。大坝到底不是钢筋水泥的。连着几天洪水的浸泡和拍打,被蚁穴和鼠洞破坏过的大坝的下方和内部,出现了松软和塌陷。但是等到我们的人用眼睛看出问题,已经有一股小小水流穿透了大坝,开始可能只是个手指头粗的洞,但不到十分钟就变成了一条胳膊粗的洞。
发现这个洞的小组,就是老朱在的这个组。当时天上的星星不剩几颗了,东方出现了一抹鱼肚白。他们在大坝上走着,听到了向着营地一边的大坝下面有汩汩水流声。他们马上下到大坝下面,看到了有一个正在变大的漏洞。
只过去了十分钟,你就赶到现场。你看到老朱这组的人正手忙脚乱地用土和草袋堵着漏洞。但看起来一点效果也没有,水正越来越大的往外吐涌。你马上意识到如果半个小时内不能堵住这个洞,那这道你亲自带人修起的大坝就会完全崩溃。而要堵住这个危险的漏洞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草袋塞住水里边的漏处。
马上让人上到大坝上,向漏水的那片地方投扔石块和装满了泥土的草袋。同时你让指导员快回营地把所有男人喊来,同时让妇女们做好转移的准备。不一会,营地那边响起了急促的钟声。不一会就传过来了鸡飞狗叫驴吼人喊的嘈杂声。
那个漏洞现在还不大,其实只要有一个草袋从漏处填塞进去,就能马上排除险情。只是洪水浑浊,看不见漏洞的准确位置藏在水中的何外,只能凭着感觉往水里投放草袋和石块。水流又很急。扔下去的草袋和石块落到水里,就被冲到了一边。大坝上站满了赶到男人还有一些女人,对付那样一个漏洞这么多人根本用不上。你看到投向水中的草袋在洪水中打着旋不知冲到了何处,你感到巨大的一个危险正在你的脚下形成,你甚至在想是不是该让大家离开大坝,往安全的地方逃跑了。
这个时候,你听到了耳边有人在悄声地对你说话。你转过脸看到了老朱。老朱说,队长,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堵住。其实你也知道有一个办法。但你了解你手下的这群男人。他们全是在远离江海的北方和西北长大,对水这个东西不很熟悉,多数象你一样属旱鸭子一类。让这些人下到水里还不如那些草袋和石块呢。老朱好象看出了你的心思。老朱说,让我下水。
你问老朱,你会水吗?
老朱说,会一点。
你挥了一下手,大坝上的人不说话了。大家让开一条道,让老朱走到水里。这时天边的鱼肚白变成一抹红。站在大坝上的人们已经互相看得清脸了。老朱好象看到了老根还有小凤。只是好象,他来不及看清楚,也不可能看清楚。他想,只要别让洪水把营地给冲了,大家就可以接着把没有做完的事情做下去了。
老朱接过你让人递给他的一个草袋。跳到了水里,老朱和草袋一起沉到水里。不大一会,老朱又从水里冒出来。你看到漏洞还在喷涌,缺口已经有水桶那么粗了。
你看着老朱,老朱看着你一脸的焦急。老朱说是他已经看到那漏水的洞了,但水太大了,草袋被冲走了。
你问老朱行不行,要是不行就上来吧。老朱说,再给我一个草袋。
你让人给老朱递过一个装满了土的草袋。老朱又抱着一个草袋沉到水里去。
你和大坝上的人全盯着水看。水浑得象黄泥汤,其实什么也看不见。但还是要盯着看。
一会过去了,又一会过去了。还不见老朱上来。
突然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那个正在喷涌的漏洞,水一下子小了。大伙儿冲上去,一阵草塞土埋,漏洞就找不见了。大坝转眼间又恢复了牢不可破的姿态。
老朱把漏洞堵住了。
大家又聚到水边,准备象迎接英雄一样把老朱从水里迎出来。连太阳也把脸探出了地平线,把鲜亮的红色投在水面上,它好象知道水里面很冷很冷,它要把火一般的温暖送给我们的英雄。
但老朱就是不肯从水里钻出来。
直到半个时辰过去,老朱才浮出水面。只是这个时候的老朱,已经和漂在水面的树枝断草没有两样。
荒地里有一棵胡杨,已经老得不行了,全身上下看不到一点绿色,没有一片树叶子。它站在那里,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活着,谁也说不出它的年岁。
老朱就埋在这棵胡杨树下,这是古尔图的第一座坟墓。
你让全队的男男女女都来到墓地,在老朱面前低一会头。
你把一把鲜的野花放在老朱的墓前。不仅仅是因为他用生命保住了大坝和营地还有庄稼。
老根和小凤也象你一样放了一把鲜野花。只是他们心里想的和你心里想的不可能是一样的。
还有雪儿,也放了一束花,不知她心里想的什么。
老朱不在了。老根和小凤不说老朱。好象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和他们来往过。
老根和小凤再也不会说起老朱。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不会在心里记起老朱。
这长长的夜,静静的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间屋子里,又躺在一张床上,总要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吧。
老根说,咱们再试试吧?
小凤说,算了吧。
老根说,没准,这会就行了呢。
小凤说,折腾半天,还是不行,让人更难受。
老根说,要不,咱们就离婚吧。
小凤说,什么,你说什么,我没嫌你,你倒嫌我了。
老根说,我哪是嫌你,我是想让你过女人真正的日子。
小凤说,为这个事,和你离婚,别人咋样看我?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老根叹了口气。
小凤说,行了,就当咱俩是亲兄妹吧。
老根又叹一口气,比前一声更重。
到雪儿屋子串门,去的次数多了。小凤和雪儿越来越熟。人一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事了。
说着说着,不知怎么就说到了谁谁谁又生孩子了。
是雪儿先问小凤的。
雪儿说,凤姐,你和大哥咋不要个孩子呢?
小凤说,唉,咋说呢?
雪儿说,要是不好说,就别说了,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是顺口问问。
小凤说,妹子,你不知道,你大姐苦啊。
雪儿说,苦事,憋到肚子里,会越憋越苦。
小凤说,可不是吗?不能想,一想,死的打算都有。
雪儿说,有多大的事,还犯着去死。
小凤说,妹子,你是不知道啊,要是轮上你,你没准也会这么想。
雪儿说,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苦事情。
小凤说,我倒不是不愿说给你听,你还是个大姑娘,我怕你还听不明白。
雪儿说,你爱说不说,反正憋在心里,难受的是你,又不是我。
小凤说,就当你是我的亲妹子,我说给了你,你可不能再说给别人了。
雪儿说,亲妹子不会做让亲姐姐不高兴的事。
小凤说,雪儿听。小凤一开口,脸就红了。说得有点吞吞吐吐。边说边看雪儿,倒是雪儿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象是在听小凤说吃了什么饭,穿了什么衣服,走了什么样的路。小凤眼下说的事,好象在雪儿听来也是平常的事。
小凤说到了一半,说不下去了,小凤的眼圈子发红了。
雪儿没跟着小凤难受,只是说,看大哥的样子,不会啊。
小凤说,说得也是,他也说,我不在的时候,他的那个东西,也能硬得起来,可一见到我,一碰到我,马上就变成面条了。你说,是不是怨我,我是扫帚星,还是个丧门星。
雪儿看着小凤说,大姐,面相这么善,心肠又那么好,会有好报的。
小凤说,我也觉得,咱从没干缺德事,老天爷咋给我这么个小女子过不去呢。
雪儿说,这个事呀,不怨天,不怨地,还是怨你。
小凤说,什么,真是我的事啊?这怎么可能呢?
雪儿说,我以前也听说过一件事,和你的这件事,很象。
小凤说,那你快说说吧。
小凤说完了,又轮到雪儿说了。说的还是同一件事。
说着说着,又是小凤的脸红了。雪儿说着这个事,和她说别的事一样,音调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一个字,一句话,说得清楚极了。让小凤不想记住也得记住。
听雪儿说完了。小凤脸象是蒙块红布。
雪儿看小凤没心思坐下去了。雪儿说,凤姐,天不早了,你回去吧。
小凤说,不急,反正回去也没事。可边这样说着,小凤边站起来,往外走去。
雪儿看着小凤背影,脸上露出一点笑。
这天晚上,是小凤主动对老根说,咱们再试试。
苞谷长到一个人高了,算是长大了。长大的苞谷,在叶子张开的最顶处,开出一簇花穗。在苞谷的杆子的三分之二外,会斜着生出一个长圆形的苞谷棒子,棒子头上有嫩嫩的细须伸开,向着上面的花穗伸开。这时的苞谷棒子没有籽粒,它在等风吹过来,风在这个时候,象个媒人象个红娘,风把那些花穗摇动,花穗上的花粉就会飘落下来,落到了苞谷棒子的头上细须上。于是一粒粒的苞谷籽就从棒子的深处钻了出来。
这样的季节,空气里会多出一种气味。到了夜晚,这样气味比白天更浓重。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野地里还是在屋子里,无论是坐在外面看月亮,还是躺在床上想心事,都能把这种气味吸进身体里。
过了二天,小凤到雪儿屋子里。
小凤的脸是红的,不是那种表皮的红,是那种从皮肤下面的血管里渗出的红。润润的红。
雪儿看到小凤脸上的红,雪儿知道小凤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小凤了。
小凤一下子抱住了雪儿。
小凤说,你是姐的恩人。姐不知该怎么谢你。
果然不一样了,小凤说话也一下子柔了好多。
雪儿说,我可是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全是你自己的事。
小凤说,答应我一件事。
雪儿说,那要看什么事。
小凤说,等我有了孩子,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你都要当他们的干妈。
雪儿说,好啊,这是我的福气啊。
好久没和老冯喝酒了。你对兰子说,炒两个菜,我把老冯喊来。
你去找老冯。老冯的屋子里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