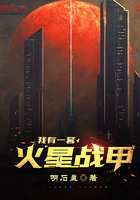戴小白帽的茶馆掌柜抖着沙白胡须劝说:
“姑娘家,小声点,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知道周周围围有没有仇家?冯会长、李总指挥、李参谋长何等样人?谁敢撞他们!敢撞他们的会是寻常之辈?小心点,少吃亏。不要连凶手都没弄清,自个先着了活。”
经老掌柜这么一点拨,玛依拉方才感觉到事态非常严峻,危险就在周围,这才停息了怒不可遏的叫嚷。
延子松关切地询问:
“你俩今晚咋个休息?”
“我就守在冯会长身边,哪里也不去。”玛依拉执着地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舒燕说罢问延子松:“那你呢?”
“那就一块陪陪冯会长和李总指挥他们吧。”延子松说着起身,陪二位姑娘回到冯特民的灵堂。
灵堂已空荡荡的,院内寂无人声。
玛依拉终于发出憋在心里好久的疑问:
“奇怪,冯会长生前朋友、战友、同志托洛托洛(好多好多)的,听我哥说,他们团结得细不(实在)好,为啥守在他身旁的,就我们三个?咋回事?他们不知道!”
舒燕苦闷地说:
“我也闹不明白,就连最要好最熟悉的人也没见一个,咋回事?”
“咋回事?茶馆掌柜不是告诉我们了吗?敢刺杀冯会长他们的肯定不是等闲之辈,或许大有来头。本该来奔丧吊唁的,兴许都已身不由己,或许是遭遇不测,或是被追杀逃亡,连他们自身都已难保,哪顾得上!所以,老掌柜劝我们小心。”延子松好不轻松地解答。
“有这么严重?那我们也会有危险?”玛依拉此刻感到危机就潜伏在身边,不由不信,不寒而栗。
舒燕忧郁而忿忿不平地说:
“我也觉来了,人们的心态变了,眼光都不一样了,有吊唁的,有观光的,有看热闹的,就是没有公开敢为冯会长说好的。新伊大都督府若不裁撤,那情形就会大不一样的。唉,真的变天啦!”
延子松点头认可。
玛依拉悲愤地说:
“那就让他们不明不白地死啦?我不甘心!那拉提草原见面时,他亲口说,过几天给我回答,是不是决定要娶我。两个礼拜过去了,既看不见我哥,也听不见他捎话,我等不及了,才把羊群撂给妈妈跑来了,谁知太晚了。若是早两三天来,兴许他会和我回草原去,我们已结为夫妻。唉!咋这个样子?”玛依拉怀着满腹遗憾,仍不忘甜蜜的过去并珍惜着对美好未来曾有过的憧憬。
“不明不白当然不行。即使你玛依拉不来,我舒燕也定报此仇。”
延子松轻声承诺:
“悄悄的,我和你们一道去。不过,得先探知谁是凶手呀?”“谢谢延壮士。”二位女子不约而同齐刷刷地握住了延子松的大手。送葬之日,伊犁镇台来向在场人表示:“杨将军惊悉冯会长、李总指挥、李参谋长不幸遇刺身亡,非常震怒,责成本镇台迅速侦破此案,严惩凶手,决不懈怠。请大家给本镇台一点时间。”心知肚明的人无不暗骂:真是贼喊捉贼!延子松、玛依拉和舒燕分头查访三日,按照约定的时间,三人陆续来到烈士墓前,互通情报后,大失所望,均无结果。不仅如此,都发觉有跟踪盯梢的情形。
怎么办?是知难而退?三个人的回答都异常干脆:“不!”
在返回途中,突然从白桦林中冒出一蒙面人,惊得三人一愣,怔得玛依拉和舒燕手足无措,延子松正欲出手,那人忙揭下黑纱迎上来,对延子松悄声说:“我是马凌霄的部下,遣散民军缩编时,我们被合并到马得元营下。刺杀冯会长他们,据说是大鼻子干的。”
延子松激动地紧握那人的双手,连说:
“谢谢,谢谢。知道谁支使的吗?”
“那就不知道了。肯定是绝密,只有问大鼻子啦。恕在下不能久陪,告辞。”
延子松等用感激的泪光送走那位知情人后,便分别返回冯特民住所,准备了枪支器械。为了安全起见,便于相互照应,一男二女只好在里外间休息。
一直处于悲愤中的玛依拉始有点兴奋,满怀信心地对子松说:“知道了谁是凶手,那就好办啦!只要我们大家麻家捎乎麻家(齐心协力),大仇一定能报。”
“一定能报。到时候,你和舒燕守在门侧接应,你们还没成婚,卧室里不方便。记住。”
玛依拉顺从地点头应承。
子时一到,延子松和玛依拉、舒燕立马动身。
大鼻子马得元的营地,延子松去过几次。他先翻过墙去,探明动静后,才把玛依拉和舒燕拽绳索接应过去。
延子松摸到马得元的新住处,黑屋子传出呼噜声。因为玛依拉和舒燕脱去了皮靴,故而步履轻盈无声,顺利地接近了门两侧打盹的卫士,用匕首一人结果了一个,而后守在门侧。
延子松摸入大鼻子卧室,嗤地划亮了一根火柴,点着了煤油灯。只见大鼻子死死地搂着美人香甜地酣睡在床上,一动不动。
玛依拉见灯光一亮,不由分说,极不甘心地擅自撞了进来,她要亲眼见见大鼻子是怎样可恶之人,她想抢先亲手宰了大仇人。
延子松从容地摘取了挂在墙上的盒子炮,背在自个身上。玛依拉也不甘落后,扑上去抢了那把挂在床头的马刀,直想砍下去。延子松一挥手制止了她。
马得元依然沉睡不醒。
延子松手持腰带宝剑,故意干咳了一声又一声,睡眼惺忪的马得元不由大惊,见一男一女手持利器站在床前索命,哪顾得人间羞丑,本能地去摘枪,不得已亮出裸体,臊得玛依拉急背转身去。
大鼻子见枪已挂在延子松身上,便去提刀,马刀也已落入大背身的女子手中。这才山穷水尽,傻了一对白眼,双膝跪在床上求饶:“延壮士,你饶命,饶命啊!”
“饶命不难。”延子松言下之意,大鼻子尚有保全性命的可能。大鼻子有了一线生机,赶忙说:
“延壮士有啥要求,尽管说,只要马某人能办到的。”
“不难,你肯定能办到。”延子松点了点头,接着说:“老实告诉我,是谁支使你杀冯会长他们的?都给了你什么好处?”“杨,杨,杨、杨将军。他如今是一省都督,有密令给我,马某岂敢不从?冯会长他不谋私利,对大家好,大家也都夸他好。冯会长跟马某从无半点私人怨恨。若不是执行军令,马某岂可做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叫世人唾骂,让万人痛恨,遗臭万年啦!实在不得已呀,延壮士!五千两赏金和这个女人,你都拿去。”
大鼻子讨饶之时,那女人已被惊醒,她从枕下摸出令箭小刀,刷刷刷朝延子松掷去。说时迟那时快,延子松耳听手动,三把利刃被宝剑当当当拨落在砖地上。
大鼻子又吃一惊,相好数月,又送黄金,又送秋波,又送胴体,又送温柔,居然不知匡时引荐的这位美人有投掷暗器之本领,真是脑袋掉了还不知是谁取的。
这一惊使玛依拉后悔不迭,忍无可忍地调转身来,怒发冲冠地吼道:“你杀了我的人,你也去死吧!”吼着一马刀劈下,大鼻子伏身一躲,马刀落在那一丝不挂的女人肩头上,惨叫不绝。玛依拉紧接着又一刀砍去,削下了大鼻子的一条胳膊。大鼻子痛得嚎叫声冲天,惊动了四邻五舍。
延子松见拖延不得,急忙补了一剑,算是对死难烈士最解恨最过瘾的祭奠。
三人匆匆蒙面离开,自此各奔东西。
延子松眼下心愿已了,便打马上路,欲回他魂牵梦绕的桃源去,伺机而动,再刺幕后的元凶。
那么,冯特民的同仁骨干都上哪里去了呢?除了调离赴任的,郝可权、李梦彪闻讯逃亡。邓宝珊也在缉拿名单之内,不得已避入俄领事馆,拿到俄国护照,经霍尔果斯取道西伯利亚,辗转回到京津,转赴陕西,在华山下和老同盟会员郭希仁、刘霭如等相识,参加了“共学团”,密谋讨袁大计。于1915年又参加了讨袁、靖国诸战役,其志至终不衰。
杨缵绪被逼无奈,于当年八月借母亡奔丧之机,离开新疆,绕道俄国返回湖北。
至此,伊犁革命领导核心和骨干分子已被杨增新基本肃清,伊犁革命仅有余波微澜而已。
但是,伊犁革命的影响远不可用伊人逝去或逃亡的时间来衡量、来截止,它为新疆民主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章。它曾推翻了清王朝在该地区的封建统治,实行了短暂的共和自治,粉碎了清王朝西迁的阴谋,使其不能把新疆作为东山再起、复辟帝制的根据地。伊犁革命虽未能理想地完成既定的历史使命,但它给近似一潭死水的新疆思想、文化界投掷了一颗重重的石子,激起一连串五彩缤纷的浪花,冲破了禁锢已久僵化保守的封建思想,为民主革命在新疆迅速传播和胜利,为新疆伊、塔、阿三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迎接和平解放活跃了思想,准备了干部,利在千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