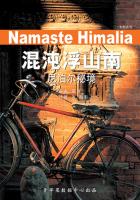自从1990年我首次翻过天山进入天山南麓,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了南疆大地。南疆淳朴的民风,多种宗教相互交融的文化历史,神奇的自然景观吸引着我一次次地走进她的怀抱。
在南疆我去得最多,停留最久的地方还属和田。2003年,我因工作需要前往和田支教,在那一年的生活中,除了解和田地区的民俗外,也对和田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期间我转遍了和田市的玉器店,骑摩托车考察了和田籽玉产地——玉龙喀什河。支教生活结束后我也成了所在学校的鉴玉“专家”,同事只要买玉都来向我请教,或拿来玉石让我鉴别。美誉天下的和田玉共有两个产地,一是发源于昆仑山,最终汇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玉龙喀什河。这条河流全长300多公里,其中下游100多公里是次生玉石矿床,是和田籽玉的发源地。其原生矿则深藏延绵数千公里的昆仑山深处,是和田山玉的发源地。在和田期间,我经常听到玉石贩子提到黑山,因为河中籽玉的原生矿都来自那里。还听说,在黑山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村落,那里除了雪山、河流、原生玉石矿外,还有生于昆仑山而从未走出过大山的人们……
沿着玉道走向黑山村
和田是因和田玉而驰名的城市,但到过和田的人们也很少去探究和田玉的来龙去脉,甚至听说过黑山的人也寥寥无几。正是由于我多年在南疆的考察活动,黑山的山流水,黑山村采玉人的传奇故事,都已深深刻入了我的脑海,我做梦都想去黑山看个究竟。2006年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利用春节假期,组织了6人的“玉河探源”小分队,迎着大年初一的晨曦离开了乌鲁木齐,踏上了踏勘玉河之源的征途。
距和田市140公里,地处海拔2800米昆仑山前山地带的喀什塔什乡是进入黑山的门户。“喀什塔什”在维吾尔语里意为“玉石”,因此,许多人也称它为玉石乡,在人民公社时期这个乡也叫火箭公社。全乡共有11个行政村,1569户人家,5900多人,其中,黑山村和尼萨村是全乡最偏远的不通车的村落。从乡政府到黑山村有20多公里山路,骑毛驴要走一天,而尼萨村则要走两天时间。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火箭公社为了从黑山运出一块大玉石,在山梁上修了一条近25公里的小道,这就是黑山村通往外界的唯一道路。
喀什塔什乡只有一条街道,它直通乡政府,我们到达时已是大年初三的下午。几十米长的街道两旁除了一家饭馆,一个摩托车修理铺外,便是几间破旧的房子。虽说是冬季,白天在阳光的照耀下,没有一点寒意,小商贩们干脆在路两边摆摊叫卖。这里很少有外人光顾,能见到的只有当地的维吾尔人。他们熙熙攘攘地站在马路中间,闲暇地享受着阳光。我们几个着装鲜艳的外乡人在人群中格外抢眼,淳朴善良的村民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不一会儿就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当知道我们要去黑山村时,他们感到很诧异,因为在冬季黑山村气候条件非常恶劣,玉河的源头也被冰雪覆盖,挖玉和贩玉的人也绝不会在这个季节进入黑山。
春节期间,乡干部都回和田休假了,乡政府的大院空空荡荡。热心村民找来了看门的老人,给我们打开了一间空房子,里面有4张床,没有被褥,据说这是乡政府的招待所。一切安排妥当后,在我们的维吾尔族队员居来提的努力下,找到了一个名叫托乎提·尼牙孜的维吾尔族向导,并租用了他家的4头毛驴。
大年初五,天刚蒙蒙亮,我们的小分队在村民的簇拥围观下离开了乡政府。冬季的昆仑山似乎异常温暖,贫瘠的大地上几乎看不到积雪。离开乡政府没多久,队伍就开始沿着蜿蜒的玉道向西南方的山梁走去。由于受塔克拉玛干沙漠气候的影响,昆仑山前山地带气候极其干燥,我们所经之处扬起的粉尘在天空中飘浮,久久不能散去。上山的坡度越来越大,海拔也迅速升高,在尘土中行进的我们,无一例外个个大汗淋漓,完全成了“土人”。经过4个多小时的连续行军,我们翻过了第一个3500米的达坂,迎面碰上了一支由几十头毛驴组成的运输队——驴帮。这是昆仑山中最常见的运输方式,也是现今新疆为数不多的专业驴帮。
在干旱少雨的昆仑山,适应性极强的毛驴是山里人唯一的运输工具。按当地的行情,一头毛驴往黑山村送50公斤货,可以挣30元,但这要往返3天,行走60多公里山路,用城里人的价值观衡量真是不可思议的廉价。我们的向导托乎提·尼牙孜也是驴帮中的一员。他家有6头毛驴,他和两个儿子常年奔波在喀什塔什和黑山村之间,跑驴帮的收入是他家5口人主要的生活来源,全家一年近一万元的收入在村里算很不错的了。
毕竟是冬季,随着海拔不断地升高,昆仑山上的气温也越来越低,小道两旁枯黄的小草在凛冽的山风中左右摇摆。我们在接近第二个达坂时已经是下午5点,连续8个多小时的行军使我们的身体热量基本耗尽。在寒风中我们紧跟驴队,迈着“太空步”喘着粗气缓慢地向上攀登。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攀登,我们终于到达了达坂顶部。这个所谓的达坂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隘口,而是一座实实在在的高山。我们望着走过的道路,顷刻间内心涌起轻松和安宁的心绪。向南远眺,海拔7282米的慕士山白雪皑皑,气势磅礴;脚下一条“之”字形的小道贴着陡峭的山坡直达谷底;不远处纵深的玉龙喀什河在夕阳的辉映下宛如一条银色的丝带向南延伸,消失在雪山和云雾之中。在享受这美景的同时,我拿出了卫星导航仪,记录下了第二达坂的坐标和3850米的海拔高度。
昆仑达坂上的牧羊人
紧贴峭壁的玉道经过多年来人畜的踩踏和雨水的冲刷,有的地方变成了狭窄的深沟,沟底一尺多厚的浮尘借着风势漫天飞扬,刮得人睁不开眼睛,透不过气来。小路沿着陡峭的悬崖向下延伸,我们小心翼翼地跟着驮队在悬崖峭壁上向河谷走去。当我们正接近一处悬崖时,一个骑毛驴的人从峭壁的一侧风驰电掣般向我们冲来,惊得我们瞠目结舌。等毛驴到了跟前我们才惊奇地发现,骑驴的“大侠”竟是个老太婆!我们的向导说,这个女人就住在达坂上。
也许她长期孤零零地生活在达坂上,我们的到来使她显得异常兴奋,带着我们踏着厚厚的羊粪来到悬崖下。这里有一个不足6平方米的小石屋——她的家。只见石屋的门上挂了一个破麻袋,屋外的角落里有一堆用破棉袄盖起来的积雪,屋内除了吃饭的用具和铺在地下的被褥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东西。经居来提询问得知,这个女人今年才26岁,结了两次婚,她男人为了挣钱平时在外跑驴帮,大部分时间不在家,她一个人常年在这个达坂上放羊。当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眼看去的老太婆原来是个26岁的少妇。
风渐渐大了起来,吹得石屋子周围的羊粪漫天飞舞,弄得我们大伙儿从头到脚都是羊粪。一天的行军令我们口渴难忍,女主人似乎看出了什么,急忙点火融雪烧水。对在达坂上生活的人来说,水和燃料都是很珍贵的。牲畜的粪便是这里唯一的燃料,水则要用毛驴到1000米以下的河谷中驮水,一个来回至少要5个小时。无奈之下,每当下雪的时候女主人就不得不收集被风吹到低洼处的积雪。燃料实在是太珍贵了,水只是烧到有点温,女主人就给我们端了过来。望着碗里浑浊地漂浮着羊粪的水,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世界也太不公平了,同一片蓝天下,却有着如此不同的人生。在贫瘠的昆仑山,艰苦的生活环境对生命的摧残远远超过了身处繁华都市的人们的想象。
离开石屋后,我们又遇到了两个牵驴赶集的牧羊人,每头毛驴背上都驮了一只刚从后山捕获的猎物,他们说是小鹿,但据我观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岩羊。他们说,捕获的猎物运到乡里一公斤肉能卖10元钱。一个上了年纪的牧羊人怀里抱着一只雪鸡,说是带下山去100元能卖掉。他还告诉我们,黑山村里50元就能买一只雪鸡。到达黑山村后我们还看到一位老者在众目睽睽之下剥狐狸皮。仔细想想村民的处境,我们只有同情,没有任何权力指责他们,毕竟,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
天黑前我们终于下到了谷底,跨过了玉龙喀什河上的小桥,这里离黑山村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暮色中,站在营地向北仰望,我们下来的达坂就像一堵墙,从谷底向上攀爬的“之”字形路线清晰可见,这就是通往黑山村的必经之路。我的GPS导航仪显示:谷底的海拔高度2730米,达坂顶端海拔3850米;从谷底到达坂直线距离850米,这意味着在短短的850米距离之内海拔就上升了1120米。这真是一个令人“绝望”的达坂。后来在居来提的建议下,大家干脆把这个无名达坂命名为“绝望达坂”。
太阳还没照到河谷,酣睡中我们就被赶集人的吆喝声叫醒。天气格外晴朗,湛蓝的天空飘浮着几朵白云。我们轻松地踏上了进村的小道。在村口我们遇到了一个老大爷,他肩上扛着坎土曼,手里拿着一个捕猎的夹子。向导托乎提·尼牙孜告诉我们,这个大叔叫依明·尼牙孜,是黑山村有名的“大巴依”(维吾尔语意为“有钱的富翁”)。他从年轻时就与玉石结下了缘分,由于玉石在维吾尔语里叫“塔什”,所以村里人都叫他依明·尼牙孜塔什大叔。我们向塔什大叔说明来意后,他热情地邀我们去他家住。
黑山村是喀什塔什乡11个自然村中较大的一个村子,它以前叫黑山大队,有两个相距6公里的小队。塔什大叔的家在一小队,现在叫喀让古塔格村。从远处的山坡向下俯视,如果没有那些林立干枯的杨树,黑山村就像一座废弃已久的远古村落。
我们踏着厚厚的尘土沿着狭窄的巷道进入了村子。村民似乎早已知道我们即将到来,狭窄的街道两旁站满了好奇的人们,成群的孩子奔跑着为我们开道,霎时间整个街道尘土飞扬,我们似乎来到了一个黄土的世界。喧闹中我突然发现在远离人群的地方站着一位满面沧桑的老人,只见她牵了一只山羊,脖子上骑着一个又黑又瘦的孩子,孤零零地站在那儿注视着我们。我看着她,怜悯之心由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