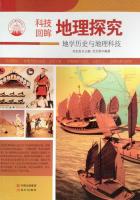一大群鸬鹚着一袭黑衣站在岸边,很冷酷,像警察。它们在晾晒翅膀。它们潜入水里抓鱼,水渗入毛发。因而,一旦上岸,它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打开翅膀晾晒一番。而鸭类们一天到晚都在水中浮游,毛上有油脂,不沾水,不渗水,也就省去晾翅的麻烦。
嗖——一只山斑鸠从芦苇荡里蹿出来,如箭一样射向远处。
一只白鹭静静地,雕塑一般,面向东方凝望。这是一尊淑女雕塑,美妙,娴雅。它一转身,我看到它嘴里叼着一条小鱼,它毫不客气吞咽下去了。
嗳——嗳——一行大雁高声鸣叫,我一抬头,它们已变成一条黑线,向南远去了。
一只凤头,在水里只露出一颗头,一看到我,迅速潜入水中不见了,好长时间也不露面。
一只麻灰色体型硕大的鸟,突然从我身边的芦苇丛里站起来。哦,大麻鳽,它多见于南方,北方很少见。它行动隐秘,如果它不动,你几乎很难发现它。它一头扎进芦苇丛,再也没有出来。
一只沙锥鸟站在沙路上,一动不动。这是它一贯的表现,一旦危险来临,它就会一动不动,它以为你看不见它。没人时,它玉树临风,走来走去。它的嘴巴像锥子,又尖又利,纵是躲在沙子底下的虫子也难逃命。
一只灰扑扑的伯劳,带弯钩的嘴巴上正挂着一只挣扎的虫子。它捕到食物的神气样子使它看起来像个小猛禽。
一只短趾百灵顶着强光,在我面前的河堤上来回踱步。它实在调皮,我一举起相机,它就藏进芦苇荡。我一离开,它就钻出来,在路上走动,离我不远不近,故意挑逗我。
戴胜,穿一件黑白斑纹的衣裳,头上顶着一朵花,把尖尖的嘴巴插进沼泽,拽出一只扭动腰肢的长虫子。
五只大天鹅静静地舒缓地游动。它们从来都是那么从容优雅。很多白骨顶围着大天鹅打转转,和大天鹅一比,它们就显得太聒噪了。
一只鸟站在老树桩上,孤孤单单地看我,似乎揣着一个什么心事。
两只硕大的蜻蜓重叠在一起,它们一个背着另一个,一边交尾,一边在高空中飞。白骨顶抬头呆呆傻傻地看着这一幕。它们的本领可真大,它说。
艾比湖以水鸟和荒漠鸟最为多。看来它们就要走了,进行秋季的长途旅行去了,就要向我说再见了,就要向故乡告别了。我站在湖边,长时间凝视它们,向它们道别,心中充满了依依不舍之情。
我的朋友们,祝你们一路平安,明年再见。
留下来的幼鸟
傍晚,西边一片殷红。
几年前,艾比湖宽七十公里,现在只剩下十二公里。脚下是松软的白碱滩,每逢刮大风,海浪漫延过来,会淹没白碱滩。
湖边沙滩上,零零落落,躺着十几只麻鸭的尸体。它们迁徙到艾比湖,准备集群,到遥远的欧洲过冬。但不知何故,它们亡命于此。护林员说,已经死去了三十多只,可能得了什么病。畜牧医生前一天解剖了三只尸体,分析病因。
一只麻鸭卧在我脚下的乱石上,奄奄一息。它的小黑眼睛水水的,像将要熄灭的蜡烛,闪烁着最后的微光。我轻轻抱了抱它,拉开它的翅膀,翅膀没受伤,完好无损。它的脚爪软弱无力,撑不起它的小身体。麻鸭虚弱不堪,用一只黑眼睛勉强打量着我,全身颤抖着。它的眼神清清楚楚地说:请帮帮我吧。我扭过头去,不忍心再看一眼那求生的呼唤。我无法帮助它。我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郁闷难消。
红脚鹬在水边走来走去,等待同伴。
六只灰雁唱着歌展翅飞翔,呼唤伴友来集群。
深紫色的水面上,有许多密密麻麻的小黑点,那是集群的鸭子,它们在水面上飞速滑翔,划出一道道水线。
大白鹭,黑鸬鹚,它们蓄势待发。
夕阳落尽,傍晚就要降临。众多的鸟儿将要开始它们漫长的远行。它们就要离开此地了,到南方去过冬,直到明年春天才回来。
小麻鸭听着远行的号令,它焦急了。它的黑眼睛又亮了亮,拼命地张开脚爪,想让身体站立起来,它不愿放弃最后远行的希望。可是它失败了。它想站立的希望落空了。它的努力使它更加虚弱。它绝望而孤独地哭了。
它遭遇了不测的命运。
另一只麻鸭独自卧在水里,无法走动,无法游泳,它向远处大声鸣叫的群鸟投去既羡慕又凄凉的目光。
它多么痛苦啊。
它独自留在沙滩上,脱离了迁徙的队伍,它就要接受死刑的宣判。
一只蜥蜴,身上的颜色酷似岩石,两只前足撑着地面,拖着长长的尾巴,徘徊在病恹恹的麻鸭身边,向它献上无限的同情。
而另一只针尾鸭卧在沙滩上,耷拉着翅膀,等待死亡降临。
一只小滨鹬也生病了。翅膀一扇一扇,在岸边扑棱。我将它握在手中,它那么小,只有一个乒乓球大小。它的嘴巴黑黑尖尖,身体温软。它在我的手心拉稀了,拉出绿色泥浆状的屎粒。我放下它,它又挣扎着扑腾到浅水里,水淹没了它。它无力游泳,赶紧掉头上岸。不用说,它走不了,将会被孤零零地丢弃在岸边。
这是一些幼鸟,长途迁徙对每一只幼鸟都是一次残酷的严峻的考验,许多幼鸟都将在这种艰难的迁徙中丧命。
沙滩上有一串很清晰的大野猪的脚印。一行小野猪的足印弯弯曲曲,停留在一只死去的野鸭尸体旁。紧挨足印,有一小堆鸭毛,几片碎骨。看来,有一只野猪带着小猪仔,半夜来到湖边吞吃了死去的幼鸭。护林员说,春天,这只野猪带了四只猪仔,经常出现在这一带。
盐壳子
有一片湖泊完全干涸了,两三年没有水注入,湖底盐化了,露出白色的盐壳子。沙鼠在盐壳子上,在沙包上打出无数的洞。
我沿着干涸的湖底走。里面有一行行清晰的足印,是鹅喉羚和野猪留下的,看来它们多次来找水喝。在某一处,公羚羊拉出一大堆颗粒状的粪便,公羊每隔几天回到同一处拉粪,这些粪告诉同类,请注意,这是我的领地,别来骚扰。
两次等待
天色越来越暗。西边,玫瑰色和粉色相互浸染,装点出一个华丽辉煌的天空。集群的鸟儿在绚丽的高空吹起远行的螺号,一波三折。它们慢慢腾腾,频频回头,一眼一眼地看故乡的山,看故乡的湖。它们的举止,让我感到心酸。
我们穿过高高密密的芦苇丛往宿营地走。就在芦苇丛朝两边分叉的小路正中央,一只野兔,在前方一米处,端端正正地坐着,动也不动。它微微笑着,注视我们。真令人惊讶,这正是昨天在此迎接我们暮归的那只野兔呀。难道,它计算好了我们返回的时间,在此恭候?见到它的一刹那,一股温暖甜蜜的潮水漫上心间。一天的暴晒、疲惫、伤感,此刻全都被这只野兔的等候消解掉了。可它为什么一连两天在同一处等候我们呢,仅仅是顽皮好奇的天性吗?它的等候像一个谜,又像一道神秘的光,笼罩着我的思绪。
又前行不过半里路,一只年幼的小兔子,同样坐在前面蜿蜒的、杂草密布的小路上,以万般可爱、楚楚动人的模样,迎接我们的归来。
它的灰身体小巧玲珑,它的两只耳朵端立。它端视片刻,一个扭身,一个弹跳,就藏进芦苇丛了。可它又没有全部消失,它站在一个高台上,两只耳朵支棱在一个大草墩上,一双明黄色的眼睛越过芦苇秆,欢欢喜喜,半露半掩,打量我们。我总是相信,等候我们的不是野兔,是两只精灵,是神派它们来的。它们接受了神的旨意。
大圆球
晨曦时分,整个天空先开始蔓延着一层粉色霞光,过一会儿,是淡青色,过一会儿是白色。一轮粉红色大圆球悬挂在两棵胡杨树间,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地升起,最后完全脱离树梢。
太阳出来了——
我激动地大声喊叫。我的呼叫声吵醒了一只睡觉的小狗,汪汪汪——它从胡杨树底下站起来,睡意蒙胧。
太阳升高了,又高了。水红色的圆球变成金黄色,闪烁着亮晶晶的光芒。大圆球偏离原来的轨道,和一棵更高的胡杨树重叠了,被树杈分割得朦朦胧胧,好像那枯树的枝枝杈杈聚合起全部力量,托起了大圆球。
大圆球的粉红外衣脱掉了,金黄外衣脱掉了,换上一件奶白色的衣裳,耀人眼目。
大圆球离开枯树了。几只小黑鸟绕着大圆球,急速抖动翅膀,来回翩飞。更多的小鸟,在密林中叽叽喳喳鸣叫,只闻其声,不见其身。
扑簌——扑簌——轻轻的脚步声传来,我一扭头,小狗在林中跑动。似乎在晨跑,它跑一圈,又跑一圈。它的嘴巴里叼着一团纸,东奔西突,身体时而直立,时而躺倒。
大圆球终于完整地悬挂在高空中。它的周围金光四射,让人无法睁开眼睛,好像它的庄严和辉煌不能让人随便观瞻。
一只大黑鸟对着大圆球在空中舞蹈,它欢庆太阳升起。接着,它直线前行,一头扎进胡杨林。
小狗被那金光震慑住了,它蹲坐在我的脚下,一双小小的绿眼睛直愣愣地看着那轮大圆球,它被迷住了。
一匹棕黄色的马绑在一棵树上,它仰起头,看着耀眼的大圆球忍不住弹蹄嘶鸣。
原先清凉的空气中注入暖流。这边那边,小鸟的鸣声,一声接一声地相互传递,好像在传递接力棒。
东边一片黄晕。
许多小生命还在睡梦中,正待唤醒。
灰色的天空不知不觉变蓝了,又蓝了。
是谁在劈柴?是谁家的小羊在咩咩叫唤?
小鸟的叫声密集了,响亮了。
胡杨树静静站立,树叶金黄明亮。
四周静谧。
晌午,翻过一个山包,来到胡杨和芦苇伴生地。这里土质松软,地面泛着一层盐碱。有一片枝干光秃的芦苇,顶着大大的芦苇花,像一个一个大毛毛球,毛毛球中间,一棵胡杨独独地站着,看起来虚虚幻幻。
下雨了。先开始雨滴都是浑圆的球体,像个小水晶球,从空中密集地滚落下来。可没一会儿,雨点又变成一条条雨线,密密斜斜地从空中织下来。真奇妙。
南飞的燕子三五成群,在这雨线里来回穿梭,叫声响亮,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