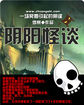一只不愿凑热闹,在离群很远的地方,独自玩耍,游过来游过去,看起来心事重重,它是不是遭到爱情的打击了呢?它游一阵,扭头朝后看一看,不知道在看什么,一遍遍重复相同的动作。后来,它把头朝后拧啊拧,拧成一个麻花状,啄身上的水珠玩。玩了十几分钟,大叫一声,飞到半空中,旋转三圈,又回到水面。它要向新的爱情宣战了,它的姿态告诉大家,它是勇敢的,它绝不服输。
五只排成一条纵线队伍,在水面平静地朝前划游,它们不紧不慢,平和舒缓。它们静悄悄地浮游,好似在水面弹奏一曲悠扬动听的钢琴曲,自如娴静。它们的身后,留下一条细细长长的黑色水线,光在水线上一闪一闪。
一只海鸥大声唱着歌,从五只天鹅头顶飞过。它慢慢地降低,降低,在低空盘旋,它对下面的同伴说:“你们好,干吗装得一本正经。”
五只天鹅,连头都没有抬一下,我行我素。海鸥讨了个没趣儿,嘴里嘟嘟囔囔着,飞走了,向空中一片小岛飞去。它以为那真是小岛,还没等它飞到呢,瞧,小岛散开了,分成三块,越来越薄,薄得像一层纱,最后完全消失了。
海鸥闷着头飞,快到跟前,一抬头,咦,小岛呢?不见了。真奇怪呀,它说。它碰了一鼻子灰,很没趣地飞回来,失魂落魄地落到水面上。
五只天鹅偷偷地笑了。
凤头麦鸡
天空是深深的蓝,蓝上面有几朵小船一样的云,飘来荡去。
我在湖边捡拾玛瑙,一边捡一边向湖岸接近。两只凤头麦鸡相隔不远,一只站着,一只蹲着。黑白条纹的花衣裳看得清清楚楚。它们头顶各有一撮羽毛朝天翘起来,好像小姑娘扎了一条马尾辫子。接着,站着的向蹲着的靠近,嘴里咕咕哝哝。它们面对着面,商量着什么。它们的羽冠张开了,这把大扇子骄傲地立在头顶,点缀着蓝色湖面,那么好看。它们一起振动翅膀,双双飞走了。这是一对情侣,它们刚刚从远方飞来,莫不是商量着在此地安家的大事情。
猛禽
猛禽的脚步总是紧紧跟随众多的鸟儿。但它们喜欢落在岩石上,藏在崖壁上,伺机偷袭某一只落单的鸟,美餐一顿。果然,我看到一只秃鹫,突然从不明处跃起,它那尖厉的啸叫乍然响起,它凌空翱翔掠过高空。
秃鹫一来,所有的鸟一哄而起,高声鸣叫。另一只猛禽朝空地上一棵枯树飞过去,盘旋一圈,落在一个大树杈上。树上有个大大的巢——那是谁的巢呢?它块头很大,几乎和向日葵圆盘一般大。猛禽停落时,那双敏锐的眼睛和耳朵四处搜索嗅闻,好一个精明机警的家伙。它的嘴坚硬地向下弯曲,翅膀有力地四下击打,锋利的爪子攀住树干,那爪子可是它捕食的好家当。
猛禽的种类在新疆非常多,有五十多种,它们被称为“天空王者”。所有的猛禽都享受特殊待遇,是国家一级或二级保护动物。
那是河谷边的一棵杨树,猛禽的巢就高高挂在上面。那只猛禽飞进去再也没出来,坐在巢里,安安静静孵蛋呢。一只小兽偷偷摸摸正朝那个巢爬过去。我搞不清那是个什么兽,麻灰色,小耳朵,圆咕隆咚的,爬起来很费劲。它爬到洞口,往里瞧了瞧,天哪,它要偷吃鸟蛋。它真不害臊,也不知天高地厚,很有可能它没看到猛禽飞进去。我等着看一场好戏呢。巢里的猛禽妈妈早有防备,探出身子,用它那铁壁一样的翅膀朝前一扑打,小兽朝树干后一闪,打了个趔趄,差点一头栽下去,慌不择路溜之大吉。
沼泽地上的雪融化了,在草墩和草墩之间,还残留着一汪一汪的水。我扒开草墩,里面藏着一些银白色的小穗儿,在光滑的绿茎上轻轻摇曳。我采下一株小穗儿,把表面的绒毛拨开,谜底就露出来了。你怎能相信,那是一株花,它躲藏在丝一般的白毛绒当中,露出黄澄澄的雄蕊。这花是不是同类当中第一个传达春天喜讯的?幸亏有那绒毛的庇护,因为春天的夜晚还是让人感到一丝寒冷。
傍晚,我返回时,在河谷边的崖壁上,看到一个十分惊人的景象,整个一面岩壁,有三十几米长,全被一种鸟儿筑了巢。我惊讶得连声尖叫,天哪,天哪,太神奇了。鸟儿们把河岸搞得窟窿密布,像个筛子。不过在我看来,那更像一个鸟儿的村庄,一户挨着一户,窗户贴着窗户,密密麻麻。后来我得知,那是岩沙燕,岩沙燕喜欢在陡峭的河岸上筑无数的巢,形成一个鸟儿的村庄。
我的常客
4月的光洒遍每一个角落。遍地的荨麻,细而高的狗尾巴草,低矮碧绿的兔耳草,它们一起在风的奏乐中翩翩起舞。
我坐在院子褪了色的小方桌前,享受光的照耀。
野草可劲地长,荨麻草更是疯了似的,长得有一人高了。许多小鸟对荨麻草情有独钟,站在草尖上晃啊晃的,我呆呆地看它们玩,好像荡秋千的不是鸟儿,是我自己。我变小了,变轻了,成了一只小鸟,和它们一起在那里荡。
最喜欢站在荨麻草上的是一群一群小麻雀,哗啦——一个黑影子从天空一闪,黑压压落下一大群,并不久留,好像不是为了捉草籽吃,只为了经过荨麻时,在草尖点一下,逗留一会儿,也不知它们到底图个啥。更多时候,它们排成一排,站在泥墙上,东张西望,蹦蹦跳跳,叽叽喳喳,极其活跃。偶尔,它们也会安静下来,闭着眼,打盹,晒太阳。
有一种鸟是我的常客。它们有一掌长,小头,长身子。灰背,白腹,脖子上戴一个黑项圈。它们总是冷不丁落在院子里,点着碎而快的步子朝前走,趾高气扬,像个小王子。每当它们点步子时,又细又长的尾巴也跟着一点一点,拍打地面。有一次,我看到它捉了一只白色小虫子,在地上一磕一磕。咚咚——咚咚,发出一种很古怪的磕碰声。我以为它啄小石子呢,低头一看,它锲而不舍,啄啊啄,终于将可怜的虫子吞下去了。又一次,它跟在我身后,亦步亦趋,模仿我走路。我一转身,它惊叫一声,慌慌张张飞走了。我后悔得要命,早知它跟着,就让这个跟屁虫自由自在玩到底。
黄头鹡鸰
变天了。铅色阴云布满天空,森林间升起紫纱帐。这纱帐绕过岩石,绕过峡谷,轻柔缥缈。“滴滴滴”,草丛里传来几声婉转的鸟鸣。我循着声音悄悄爬过去。一只鸟儿正在草丛间欢快地觅食。它敏捷地从一棵小草尖,跃到一棵小树上,攀住它的一个枝丫,摇啊摇,动作轻盈又迅疾。
抬头的一刹那,它的头颈和腹部两大片金黄的茸毛,闯入我的眼睛。非常耀眼。多美的鸟儿。它的毛色和花纹让我两眼放光。它披黑白相间的花衣,尾部别一把小刀,约一指长。我对着鸟谱认出来了。这个鸟中佼佼者,被人们称为草原一枝花——黄头鹡鸰。因长相出众而大名鼎鼎。
有三只。它们相隔约一米,跳跳停停,在歌声中觅食,看起来相当自信。这种自信大概来源于它们美丽的身姿和鲜艳的羽毛。在我见到它们的一刹那,有些冲动,想给三个家伙画一张素描图。但我绘画的水平太差了,画了几张都不成样子。看起来有些败坏它们的形象,只好作罢。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它的模样已经装在我的心里了。
另一次我弯腰吃力地在山路上走,气喘吁吁。
细雨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
到下午,红彤彤的大太阳冲破雾纱,在天空晃啊晃。几朵云奇妙地变幻:这边,两只野鸭子在水浪里赛跑,身后留下一行细细的水线;那边,一枝水仙花才盛开,花瓣上挂着露珠,似乎要滚落下来,却又悬在那里。
山路盘旋而上。河流高声欢唱,一路陪伴着我。河床一会儿宽,一会儿窄。河中巨石突兀,浪花翻滚,轰轰作响,气势惊人。有一处,宽银幕样的瀑布从天空垂挂下来,一条银色的链子将天上人间合为一体。
一只黄鹡鸰在这个通天梯上点水玩耍。它敛起翅膀,飞速地点一下,再点一下。小水花随着它的小圆身子跳跃着。它实在太顽皮了。我替它担心,怕它被那巨浪般的瀑布吞掉了。我欣赏它玩耍的模样,看了好几分钟,才明白,是多余的担心。它天生就是戏水的大玩家。一个天才。我一颗心也就放下,悄悄地乐了,还为它鼓掌,不知它是否看到。
又隔了两天,我正在草地上,在太阳底下洗脸,叽叽——叽叽,河边林子里有鸟儿乱叫。我赶紧绕到木泥屋后,天哪,一个高高的独枝上,一只鸟儿正在高歌。小身体,腹部是一片麦穗般的金黄。它在晨练吗?它的心情看起来好极了。它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来回折腾,好像故意给我——这唯一的观众表演着。我受宠若惊,激动得又蹦又跳还咋呼一声:黄头——鹡鸰!呵呵,我的呼叫声差不多把鸟儿吓了一大跳!小家伙愣了一下,跳了一个蹦子,很快又平静了,有些嘲讽地盯住我看了一阵子。我为自己终于记住了某几种鸟的芳名自鸣得意。
我常背鸟谱,记下它们的模样。可一旦这个鸟突然光临,我就傻了眼,大脑里一片空白,它们的名字我全忘了。这一次,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