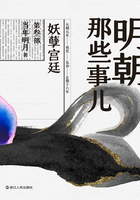女人庆幸地说:
“啥把式么,头一回学手哩。”
“啥!头一回?好!胆大心细,我这头今后就交给你了,我的妻!”
孝先兴奋而又风趣地学着戏腔道。
“不交给我还交给谁?别起,全剃光,把头皮好好搓洗一下,看垢甲锈得多厚。”女人说着将头剃得光光的,胡子刮得净净的,反复搓洗着头皮。
“就是么,二十多年了,今日才觉着洗头的滋味,光头好!太舒坦了。从今以后,咱就扮做个和尚,领上个花里胡哨的小媳妇,和和美美地过日子,来个风流快活一辈子。好不好?”孝先油腔滑调,风趣话说个没完没了。
“好啊!你好我也好,咱全家好。”女人说着,将汉子搂在怀里,把脸贴上亲了一下,说:
“还是怪扎人的。”
“扎你一辈子哩。”
小两口开心地笑了。
喜讯!振奋人心的喜讯。
麦子扬净一量,竟有二十四石!孝先两口儿高兴得咧嘴直笑,尤其是孝先,做梦都笑出了声。你想,他能不乐吗?二十亩收二十四石,不曾听先人说过。麦子丰收了,如果光自个儿吃,六年都富富有余。媳妇不久要生孩子,今年他算得上喜上加喜。
孝先算计着,赶割糜子前,一定要趁热把房子盖出来,晾晾干,寒露以前,无论如何得把媳妇搬进去。他把锯子、刨子、凿子、锛一一磨快,拉开架式做木工活,锯呀,刨呀,锛呀,凿呀,门框窗框套出来了,就叮叮、当当、喳喳、嘎嘎做起门窗瓤子。木屑飞溅,刨花拖地。孝先手中的刨子推得正欢。“五哥,歇了晌再干,看把你慌的,累的,满头大汗。”孝先见媳妇提着茶壶身子一腆一扭地来了,就停下手,坐在刨床上歇息。刨床是一根锛平了的直榆木大凳子。孝先注意了下媳妇的身子,那肚子越来越大了,心里也喜也忧。他暗暗鞭策自己,房子定要抢着盖,搬进去越早越好,可不能叫媳妇在窝棚里生娃呀!
双杏见汉子望着自个儿愣神,莫名其妙地说:“盯着人家肚子瞅啥?难看死了!都怪你,当年就给人家扣了个肉锅。还好,野荒了哨的;要在家乡,不叫人笑话?羞死了!咋见一块儿玩耍过的女娃子,人家还正踢毽子丢沙包哩。”
孝先哄小孩子似的说:
“那有啥不好见的?难看啥,羞啥?你扣肉锅,算你本事!旁人笑话,她还扣不上哩。我左看右看,这大肚子好看,威风,说不准还是双胞胎哩!”
“五哥你坏,你狠,这么点大的女人生一胎都难心,你还指望两胎,要人的命!”女人摸着肚子又娇又嗲地靠在汉子身上道。
听到“要人的命!”孝先不由心里暗暗紧张,因为他的母亲就是生孩子大出血而死的。他见小女人天真无忧,不忍心说那些令人恐怖的事情,只能存在心里,忍着,忧着,一心盼望着女人能顺顺当当地生下孩子。为此,他尽一切努力创造可能的良好的条件,尽量少叫女人劳累,最好让她什么都不干,他才放心省心,于是他再三叮咛:
“别提茶送水的,饭也我来做,记住了吗?”
可小女人却说出一段令孝先出乎意料的话:
“茶也不送,饭都不做,你叫我干坐直躺着,能给你生下大头儿子吗?你不是好心害我吗?”女人几句话说得汉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干瞪眼愣在那里,几次欲言又止。女人见状,扑哧笑了。
“说你懂,你啥都懂;说你能,你啥都能,就是女人生娃的事情你不懂。你没听说过‘怀娃婆,莫躺着,走走路儿身子活;怀娃婆,莫坐着,干点轻活力气多。莫坐着,莫闲着,一步一步朝前挪,身子活套好生娃,力气多了不难过。’”
“嘿!真是隔行如隔山,天有九重天。小丫头子,还懂这么多!谁教你的?”孝先听了媳妇的这番话,如迷途知返的行人,如大梦方醒的痴汉,如饥渴待哺的婴儿。
“娘教的,娘又是婆婆教的。”
“你妈真是有心人,老早就给女儿教会了这些。”孝先不无佩服感激地道。
“女人嘛,干啥务啥,这有啥?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教会的还不止这些哩。”双杏引以为豪地说着笑着。
孝先接过女人递来的茶碗,一气喝光,递还了碗,说:“去坐在框子上缓着,我得赶活儿。”
女人一起身,孝先便风风火火地干起来。当女人右手拄着窗框,扭着身子起来,准备回去做饭时,孝先手里的窗瓤子好了,门也好了。女人见了大喜,说:
“只指望你庄稼活儿是个好把式,就能过日子;没承想,木器活儿也这么在行。你真能干!”
“能干还在后头哩!”孝先逗趣地道。
“走着瞧吧!”女人也风趣地缀了一句,一扭一腆地走了。
一切就绪了。孝先抢盖房子的工程也开始了。
孝先一个人要盖一套房子,又是抢盖。只好脚不沾地,手不放空,一步紧似一步,一项紧接一项,干得异常紧张,分外繁忙。地基槽子起开了,快抱石头,砌好;井水挑来,赶紧和泥;用桶子提了稀泥灌抹一遍,再去和草泥;草泥和好了,就一摞一摞地背土块,两手从屁股后面抠着,一摞就是八九块。双杏看在眼里,干着急,爱莫能助。椽花走好了,树枝铺均匀,麦草铺好了,又得拼命抢着上房泥;不抢,一场风来,铺在椽子上的麦草就会不翼而飞。虽然累得腰酸背痛,手麻臂困,但还是抵销不了由衷的喜悦。
双杏体贴地坐到他身边,举起两个小拳头,给汉子一会儿捶肩、捶背,一会儿捶腿、捶腰。孝先舒心地享受着。捶着捶着,孝先喝了碗茶水,一骨碌翻起来,又跳进泥坑。他要和二遍房泥,抹墙的泥,打炕面子、炕柱子的泥,还要去拉草运苡子……
孝先就这样不要命地忙活了半个多月,一套三间一明两暗的房子终于齐整地亮在了女人的面前。女人乐呵呵地端详着,就像赏花一样,满眼的笑。
女人一边观赏丈夫汗水的结晶,一边提拉着正在缝合的小儿衣裳。孝先抱着一大块几十斤重的炕面子来了。女人快活地问:“盘炕?五哥。”
“赶紧把炕盘了,早烧早干。等把糜子收了,炕也烧干了,咱就早早搬进新房去,也来个妆新。”孝先信心十足捎带点俏皮口气道。
“还妆新!要不要大老远请些人来闹洞房?娃娃都胡蹬乱跳快出世了,不害臊。”女人含娇带嗔地戏说道。
“不用请人,咱自个儿闹还不行?害啥臊!”孝先逗趣道。
女人爱情洋溢地瞅着汉子,重重地说:
“泥水活儿,你也这么能干!”
孝先看着女人手里的小衣裳,回敬了一句:
“女娃子家,针线活儿也这么能干!”
“五哥你,你坏,笑话人家,这些针头线脑活儿哪敢跟你比!”她说着笑着,随汉子走了进去。
真是忙人嫌天短,闲人愁夜长。转眼工夫,几天过去了。三个烟囱冒烟了。糜子也开镰了。
糜子扬净入仓了,炕也烧干了,墙也抹得光溜溜的了。
孝先两口欢天喜地搬进新屋,亮堂堂的,暖烘烘的,宽展展的,不是天堂,胜似天堂。小两口终于结束了八个多月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终于给那餐风露宿近似野人的日子划了个圆满的句号。
小两口你望望我,我瞅瞅你,喜悦之情无法形容。孝先终于按捺不住地说:
“自个儿盖的新房,自个儿盘的暖炕,不妆新,你不后悔?”说着扑了过去,女人温存万分地斜依在汉子怀里,娇娇嗲嗲地说:“你不乏呀!防着点,快生了。”
双杏即将临产,孝先时刻提心吊胆。小女人脚未出门,肚子已挺出门槛。但她还是坚持做力所能及的活计,尽管行动起来好累。
为了顺产,为了给汉子创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境,她依旧黎明即起,从不睡一个懒觉,出出进进,在她眼里有做不完的家务活儿。这不,刚把玉米珍子干饭蒸好,捞了点咸豆角,正要动刀切,耳旁传来丈夫那熟悉的脚步声,随着门吱呀一响,女人扭头一瞧,汉子披银戴霜地走进来,络腮胡茬上结满了霜花,活像个白须烂灿的老大爷,喜滋滋地一手提一只白色的大兔子。
“杏儿,你看这是啥?”
“哎哟,你当我是个傻子,连兔子都认不出!”
“自打乌鞘岭以后,可怜你了,也可怜了肚子里的娃,就没见过肉星儿。赶你把咸菜切好,我把它扒了皮,开了膛,就可下锅了,兔子炒咸菜可好吃了。”孝先似有欠疚地道。
“好是好,时节长了不动荤腥,也不知馋是个啥滋味。”女人略有喜色地道。
“好!”孝先听了女人的话,一转身出去了,眨眼工夫,提进来两条血淋淋的肉东西。女人见了似有惧色。孝先用凉水洗涮了下,三下五除二,一顿刀剁得零零碎碎。他扶妻子坐下,自个儿把火烧旺。
只听刺啦一声,野生的美味已挥发出来,扑鼻的香气刺激得小两口垂涎欲滴,食欲大开。随着锅铲的翻动声,香气弥漫了整个里屋外屋。孝先锅灶上的利索精干,女人早在康大叔家就已领教得心悦诚服了,加之肚子不方便,她只好坐在炕桌边观看。嗵嗵嗵,孝先把金银花干饭盛了上来,大盘兔子肉菜也端了上来,小两口坐在炕沿上动起了筷子。孝先拣了块兔肉放进女人碗中,自己才吃起来。女人将肉放入口中品尝着,美滋滋地刚要下咽,忽然侧面吐了出来,接在手心。孝先惊诧地伸过头来问:
“咋啦!不舒服?”
“你吃吧,我就着吃些咸菜。”
“为啥?不好吃?”孝先紧紧追问。
“好吃是好吃,要是生个豁嘴丫头,以后咋嫁出去?”女人顾虑重重。
“为啥吗?”孝先继续追问。他认为女人不沾荤腥太遗憾了。
“你没听老人说,怀娃婆莫吃兔子肉,生下豁豁嘴没手逗。老家有几个豁子,我见过,可难看哩?不能为解馋误了后人,对吧?”
“有那么玄?!”孝先不敢相信,满腹狐疑。
“以防万一,不可不信。你快吃吧,啊。”女人一不吃,孝先也索然无味地搪塞了几口便走了。
双杏正洗着碗筷,孝先又冰不拉碴地提着野味进了屋,兴冲冲地说:
“这你总可下口了吧?”
“啥东西?”女人新奇地看着反问。
“野鸡!”
“好漂亮呀!头次见,要能养着就好了。”女人兴高采烈地道。
“短时节是养不活的,收拾了吧,啊?”孝先央求着,女人点了点头,可把孝先乐呵坏了,那动作利索得真是说时迟,那时快,一瞬间,毛拔个净光,膛也开好了,不一会儿,美滋滋的香味又扑入双杏鼻中,挑逗得她直流口水。热腾腾的野鸡肉端上来后,小两口重新入座,双杏吃野鸡,孝先吃兔肉,小两口有史以来,消消停停地坐在自家热炕上,大盘大盘的野味,吃了个痛快,吃了个过瘾,饱饱美美地解了一次馋。
双杏的野鸡肉还没来及吃完,孝先又拖着一头野猪回来了。野猪也是双杏没见过的,站在那儿看稀罕。孝先边剥皮边说:“这皮结实得很,等明春熟好了,做皮鞋是上等的。”
这以后,几乎天天有肉吃。吃着吃着,有一天大太阳,天气格外明朗,双杏无意中从小玻璃镜里发现自个儿白胖起来,心里不由得吃惊。午饭时,她只顾给孝先夹肉。“多吃点,几个人的活儿你一人干,身上掉了几斤肉,脱了几层皮,趁着冬天能放着,好好补一补。”
“那你咋不吃?把肚里的娃也补一下,不好吗?”孝先大惑不解地问道。
“我补胖了,娃也补胖了,我能生得下来吗?还是等生下再补吧。”
孝先一听“生得下来吗?”犹如五雷轰顶,再不相劝。
是呀,双杏能顺利地把孩子生下吗?
立冬第二天,窗外就飞起鹅毛大雪。双杏坐在窗前缝制婴儿衣服,抬眼外望,漫天梨花飞舞,迷茫茫,扰得人眼花缭乱,什么也看不清,这是她入西域以来见到的头场大雪,好新鲜,好壮丽。只是昨晚肚子已闹过阵痛,慌得孝先手足无措,额汗豆滚。这会儿虽已平复,可以坐着干些什么,但孝先严禁她出门,所以无法到户外欣赏塞北冬季的风光,只能隔着白色的窗纸开开眼界。
孝先在外间忙着,粗柴已锯成短截,靠墙堆得老高。细树梢折得齐刷刷的,也摞得高高的。早饭虽已吃过,锅里水添得满满的,灶里放好了随时可以起火的干柴。
“五哥,点火烧水吧。”女人的口气略含焦灼。
孝先急忙点了火,快步进了屋。女人已丢了针线活儿,靠在被子上,用手揉着大肚子。
“咋样,又痛了?”孝先急切地问。
女人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孝先坐到女人身边说:“我来揉吧。”
“去,你那手劲多大,没分没寸的,又不是空肚子。”女人挡住孝先伸出的大手。
孝先下了炕,又去烧火。
“五哥。”女人颤声叫着。孝先赶忙进了里屋,见女人痛得额头渗汗,手还揉着。孝先上了炕,让女人靠在怀里。女人缓缓地说:“把我挪到那儿,快了。”孝先如搬价值连城的瓷器似的,轻轻将女人挪了个位置,缓缓放倒,又在那半个铺着干净细沙的炕上,垫好枕头。女人用左手拽下棉裤,孝先没明白啥意思,尚在那儿愣着。
“脱呀!不叫你脱时,你急死慌忙抢着脱;叫你脱,你又犯傻了,穿着裤子咋生娃呀!”女人忍着疼痛,还情思悠长地数落着汉子。孝先这才动起手来。
“只许脱,不许看,啊!”女人警告着。
孝先把被子盖好后,就要下炕。女人又说:
“水烧滚了,把木盆烫洗一下。”
孝先“唉”了一声下炕去了。刚照女人吩咐把盆烫洗过,又听女人呼唤:
“五哥,五哥!”吓了孝先一跳,他连忙进屋,只见女人额头流汗,咬着牙关,两手死揪着被边,身子鼓动着,肚子一起一伏,高耸着,接着喊叫着:“娘呀!”
这一叫,惊得孝先六神无主,再能干、再有本领的人,此时也一筹莫展,急得打转转。不知怎么的,扑嗵一下,他竟跪在地下,嘴里不住喃喃而语:
“菩萨保佑,上天保佑,祖宗保佑,孝先诚心求你们了,两代单传啊,让我媳妇平平安安生下娃,我发誓,积善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