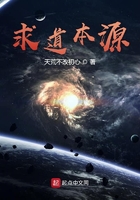背後傳來緩緩的踢水聲,一步一步地接近著,直至距離黑袍人背後不過五米前後便停了下來,呼吸聲既慢且穩,似乎對黑袍人所做的事沒有多大的驚奇。黑袍人暗暗用力,卻是連個小指頭亦動不了,只覺身體不是自己的,就像被鑲嵌在岩石之中,難以動彈,這樣的經歷實在是從未試過,已猜到背後那人不知動了甚麼手腳,如果對方有心殺了自己,現在實在是無計可施。雖然他素來不喜多言,但此刻也只得開口問道:「你是誰?想怎麼樣?」
隔了良久,只聽見水聲潺潺,那人卻遲遲不作回應,似乎在猶豫著甚麼。
那人正欲開口之際,一刀勁風猛襲而至,竟然是黑袍人那柄古怪方劍。那人知道厲害,急忙躍後,那怪刀距離自己胸前不過尺餘,隨即一張黑袍急擲過來。那人心中吃了一驚,也不知黑袍人是如何突破自己的控制,心想萬一黑袍人借這時刻攻來,實在是危險之極,當下連連躍後,拉開了距離,隨即右手一伸,想要再「封住」黑袍人的行動。
豈料「乒」的一聲,黑袍人已衝到之前升降機處,正一躍而下,二人目光一接,對方的樣貌均深深印在腦中,然而黑袍人卻見對方正戴著一個舞台劇般的白色面具,看不見本來面目,但見其身材婀娜,皮膚白嫩,卻是個女性,當下哼了一聲,身體已直墜下去。
那人見黑袍人已去,默然良久,口中喃喃道:「是個少年嗎...銀色頭髮...金色眼睛...」
這次事件讓許多「大腦」損毀,亦即好些市民「正式」死亡,數字達數百人之多,然而政府不知用些甚麼手段,竟無聲無色地壓下這些事件,並沒引起甚麼恐慌。也許在這個世代,已沒多少人會憂心旁人遇到「不測」,因為再大的不測,也可以救活過來,不過是換個身體而已,古時有一個老詞彙:「擔心」,例如說我很擔心妳,本是表達關懷的暖語,但當活著的人已沒有甚麼危險,連死亡也已不需擔心時,這個詞彙似乎亦失去了應有的意義。
數日後,星期日,晴天。
在市中心繁華之處,一家頗有格調的法式餐廳,在不多的客人之中,一位少女坐在開放式的小圓桌旁,陽光被通空的天幕遮了大半,卻還有零碎灑落少女肩頭,暖洋洋的。
她手中拿著書本,已將近讀完,而桌上幾本書正整齊地放著,在這個所有文字都已經電子化的年代,這樣拿著幾本書悠閒地閱讀實不常見。而少女面前放著一只象牙白的茶杯,下面墊著藍邊白碟,杯中餘下小半杯紅茶,旁邊是一個小巧的茶壺。少女蔥指微動,又翻過了一頁,長長的睫毛隨著視線微微晃動,似乎看得極快,不過兩、三秒,又是下一頁...
輕風過處,少女的一頭黑色長髮似被微微壓過,青絲微揚,柔而不亂,她的膚色甚是白澄,挺鼻薄唇,雙目是茶色的,看起來既明澄又深邃,看起來就像水彩畫中的人物一般。
看著看著,少女打算翻到下一頁,書本卻不知被誰的手遮住了,壓低下來,書後是個穿得怪模怪的青年,頭髮的顏色就像打翻顏料一般,旁邊有兩個青年一左一右的站得比較後,穿得也大同少異,一看已知並非善類。抓著書本那男人打了聲招呼,肆無忌憚地說道:「美女,跟我來一次,多少我也付得起。」背後兩個男伴擠眉弄眼的,竟似有合圍之勢。
少女吃了一驚,連忙捧起台上讀物,轉身要走。
「喂!我在叫妳!妳聾了嗎?」那男人凶巴巴的,一手抓起少女右手,書本登時掉滿了一地。少女吃痛,皺眉道:「快...放手...」左手連推,卻哪推得開對方?
「喂!客人!你在幹甚麼?快停手!」旁邊的侍應提聲喝道。他雖跟少女不算熟稔,但少女既是這餐廳常客,又見這男人如此禽獸,當下忍不住出手制止。
「彭」的一聲悶響,侍應應聲倒地,正是被那男人打了一拳,鼻血長流,只覺頭腦一暈一暈,這拳確實不輕,又聽到那男人冷冷地道:「你敢再便再多說一句,我就讓你換一個新殼…」手中不知何時已多了一柄折刀,反手握著,似乎對方只要再說一句,便會猛刺下去。
侍應只覺背後一人大力拉走自己,正是餐廳的年長同事,低聲道:「別多事,你傻了嗎?難道不知他是誰?」原來那人乃是此區富豪之子,拿刀砍人,或是先姦後殺也早不是第一次,反正家中有的是錢,也不怕別人告發,大不了賠錢給受害人製作複製體,再罰款警戒了事。
那少女這時已被按在桌上,不住掙扎,喊叫道:「停...手...不要...」然而這等呼叫不但毫無阻嚇之效,反倒讓對方獸性更上一層樓,淫笑道:「妳既然裝高貴,我就在這裡上了妳,哈哈!」又補上一句:「妳給我好好完事,別擅自斷線...」隨即壓下頭去,想要強行索吻。
富豪之子所說的「斷線」乃是「大腦遙距技術」成功應用之後的詞彙,原來當主體受著過大壓力或痛楚之時,大腦跟「複印體」之間的聯繫會強行切斷,以免過強的信號傷害大腦。然而自主決定之下,本體亦可先自主維持「連線」狀態,皆因複印體一旦斷線,以後亦不能再作連接,不能再用。因此主體可自行決定是否維持連線狀態,避免輕易廢棄造價高昂的「複印體」。「廢棄」從前是叫作「死亡」狀態的,然而肉體雖壞,大腦卻是活著的,政府官員為免眾人多想從前,故此後來已被修正為「廢棄」二字。
那富豪之子竟然真的想就在此處行事,這時已將少女的衣衫扯開一邊,騷胸半露,眼見好事將成,身旁卻無一人阻止,更有些人拿出手機拍照,似乎覺得甚是有趣,又沒甚麼大不了似的。
「擦」的一聲輕響,一切似乎就這樣凝住,過了兩秒,才聽見「冬」的一記悶響,一顆圓滾滾的東西掉在地上,滾了開去。
少女目瞪口呆,眼見剛才那野獸般的臉面早已不翼而飛,噴出來的鮮血正灑在自己臉上,掉在口中又腥又咸的,想到此處,不由得急忙轉身,嘔吐起來。
剛才那滾開去的圓球正是這富家公子的狗頭。
富家子的兩個同伴眼見頭子突然被砍掉,登時連退幾步,口中不住呼喝,說甚麼:「你小心點」、「你不想活了」云云,卻腳下抹油,轉身急奔而去。
少女嘔吐漸止,這才回頭張望是誰出手救了自己,眼見身旁正站著一個少年,身穿黑色休閒服,頭戴黑色鴨舌帽,髮色卻是銀白色的,甚是奇特。又見他右手握著一柄銀色餐刀,就跟尋常的餐刀一般,就只有刀刃處沾著一抹血紅,卻不知他是如何出手的,快得匪夷所思。
那黑衣人隨手丟下了餐刀,彷彿剛才的事不痛不癢似的,就這樣舉步離開。那少女呆了半晌,看著對方背影漸離漸遠,才意識到對方剛剛是救了自己,理應要說聲謝謝,但想起對方手起刀落的樣子,卻又害怕起來,正猶豫間,對方已走得遠了。
眼見對方轉進小巷弄之中,少女也轉了進去,尚沒追上幾步,只覺右肩忽然酸痛,卻是被人狠狠抓著,隨即拍的一聲,自己已被推到牆邊,背脊好不疼痛,手上的書本散滿了一地。
「妳跟著我做甚麼?」一道冰冷的聲音鑽進少女耳中,但更冰冷的是頸上的感覺,不知被甚麼東西輕壓著,又薄又冷的,似乎隨時都要在自己喉頭一拉而過。
雖然不過數秒的沈寂,卻令人覺得極是漫長,少女好不容易才吐出了幾個字:「我...我沒惡意的...謝謝你幫了我...我...叫林映雪...」
那少年靜靜地瞧著少女的雙眼,似乎信了,才慢慢將雙手鬆開,右手一轉,那「利器」已不知藏在哪裡,似乎是銀色的,隨即說道:「妳們這種東西...別想跟我套近乎...」轉身便去。
這次少女卻不敢再追,心中不解為何對方似是充滿著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