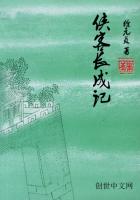从维熙
光阴如逝水东流,到今年的7月11日,孙犁辞世已整整五周年了。
此时,他的文魂正走在故乡的土地上,走在溢满荷香的花丛中。生前,中国文坛留下他那一生布衣布履的身影,此时仍然与中国的泥土一色。
在我记忆里,孙犁一生是没有穿过西装的,能不能这么说,孙犁从里到外都闪烁着中国文化的情结。在一篇文章中,我曾把孙犁的人文气质与在津门生活过的弘一法师(李叔同)联系起来;尽管这种对接并不一定完全严丝合缝,但其清淡洒脱的文魂,却与李叔同有着许多近似之处。当然因为他们所处时代的异同,其笔锋涉猎的生活,由于历史年代的差异而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从其恪守文学的清淡和远避喧嚣的人文行为的轨迹去探寻,这两位文学大师的生命的脚印,履痕却极其相似。
诚然,年轻时参加了革命的孙犁,不可能产生“晨钟暮鼓”的禅佛思绪,但从拒绝尘俗(包括官场)的情愫上去体察,他们却有着若干绝对近似之处。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的晚期,社会转型孕生了若干浮躁之气之后,孙犁仍然坚守文学初衷,这在中国当代文学星空中,怕是只有寥寥几颗了。这里需要诠释的是,老而弥坚的孙犁,绝不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存有疑虑——正好相反,蹲过牛棚、在“文革”中饱受凌辱、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的孙犁,对中国的伟大变革,内心是充满激情的。
曾记得,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陪同康濯去探望他时,他在谈笑中曾引用“从此我们可以自由呼吸”这句歌词,来表达畅快之情,这足以说明孙犁对历史新时期的到来,是怀着十分圣洁感情的。这是必须阐明的一点。在悼念孙犁的诸多文字中,我曾见过另一类文字,他们在感叹大师离世的同时,把老人禁锢于怀旧的世界里——中国文苑里倒有一些此类的人面狮身的标本,始终不肯反思过去;而孙犁不是,孙犁只是拒绝时尚中的金钱因素对文学清纯的腐蚀,导致文学精神移位,而发出音响,他说:“文学要是与金钱联姻,难免滋生婊子般的文字。”因而我在悼念孙犁师长的文章中,使用了“一个清纯文学年代的终结”的说法,以表示一个后来人对前辈人孙犁,坚守清纯田园的礼赞和追思。
还让我们永生不能忘却的,是孙犁从来不自视为师。尽管评论界把孙犁视为文学流派中“荷花淀派”的旗帜,但他从没有承认过某某人是他的学生,并多次把这个文学流派说成子虚乌有。这与时尚中那些喜欢拉山头,竖大旗,梦中也想当文苑精神图腾的某些文官,在精神境界上,有着楚河汉界的根本区别。可以这么说,时尚的文苑太多了喧嚣和炒作,太少了甘居寂寞的文曲星辰;由于文学中商业因子的猛增,一切都在进入人为的经营和策划之中,文学这个宇宙间的自由落体,充填进来许多非文学的斑斑杂色,因而我把孙犁驾鹤西归,视若一种对“痛苦”的完全解脱。
记得,在孙犁逝世之后,有一天我与莫言通电话,话头不知怎么一下就跳到孙犁辞世上来。他说:“中国只有一个孙犁。他既是个大儒,又是一位‘大隐’(隐士)。按照孙犁的革命资历,他如果稍能入世一点,早就是个大文官了;不,他后半生偏偏远离官场,恪守文人的清高与清贫。这是文坛上的一声绝响,让我们后来人高山仰止。”接着,他说了一件文坛内鲜为人知的往事:他在文学上蹒跚学步时,处女作发表在他当兵的时候,那篇小说名叫《民间音乐》。他怎么也想不到那篇东西被孙犁读到了,老人家立刻写了篇评论文章,让他永生难忘。莫言自我调侃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这个歪瓜裂枣,能在后来步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那篇评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今天成为一个作家,也要以孙犁的人文精神为前导。”说实在话,我只知道我们这一代作家中的刘绍棠、房树民、韩映山和我——以及下一代作家中的铁凝、贾平凹受到过孙犁的文学滋养,当真不知道在文坛中如日中天的莫言,在初学写作时也受到过孙犁的关爱。后来又从报纸上看到,诗人孙敬轩以及作家林希、肖复兴,也都因倾慕这位文坛大师,而与孙犁有过精神交往。
在孙犁辞世的那天早晨,津门下起了霏霏细雨。这是苍天为之泪落。津门百姓自发地来到他的家庭灵堂献花,室内容纳不下了,就摆在室外;室外又摆放不下了,就摆在门口;门口也堆放不下那么多鲜花了,一束束鲜花一直摆满了通往孙犁宅院的小巷。这是大地为之动容。中国文人浩如烟海,但能在辞世之后,受到庶民百姓如此爱戴的,怕是只有孙犁一个了。
何故?
灵魂圣洁是无价的——孙犁具有这样的灵魂。
只有这样的作家笔下的文字,才能赢得人文精神的永恒!
(选自2007年7月11日《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