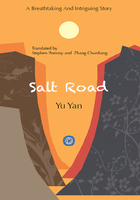我在普罗旺斯刚待了一年时,我们的新邻居乔琪特就带着我采摘野生菇类——季节性的采集活动。
“知道这些是什么吗?”她亮出了她的篮子,里面装满了一大堆长着橙色柄和帽的植物,它们混杂在松针、快要腐烂的橡树叶和污泥之中。这时,我正在为户外午餐布置餐桌。
“唔,看上去像蘑菇。”凹面的蘑菇伞上面,有一圈圈近似于彩虹橙色的同心圆,还闪烁着一点点铜钱绿。“但是和我以前看到的都不一样,”我犹犹豫豫地摸了一下,“从哪里弄到的?”
“啊哈,我也这么觉得,”她像没听见我的问题似的,接着说,“我敢打赌,在美国绝对没有这个品种。它们是这儿——普罗旺斯的特产,叫做血菇,意思是说它们的汁水是血红色的。”她从蘑菇的伞上掰下了一块,露出来的菇肉渗出了一点深红色的汁水。
“现在在我们这的森林里,能够看到它们,就在那边的松树和橡树林。它们很好吃。我给你看。”她放下了篮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臂,带我往柴堆走去。“这儿,”她边说边递给我一抱葡萄藤枝条,“把它们塞到你的烤肉架下。”
唐纳德和我把六块砖堆成两层,放进了院子一角一个三面围起来的长方形空间里,下面是我们挖出来的一个浅浅的坑,于是“烤肉架”就成了这一杰作的泛称。我和乔琪特在坑里升起了一股小火,然后把烤肉架放在上面,开始烤香肠、羊肉或者猪肉块,然后便是烤蘑菇。
乔琪特堆好了树枝。“首先我们要洗干净蘑菇。”她说。我把刚刚拿出来的盘子推到了一边,然后她、埃塞尔和我坐在了桌子边上。
“你有小刷子吗?”乔琪特问。
“我想没有。”
“也没有旧牙刷?”
“没有,我们只有正在用的牙刷。”
“好吧,”她说着跳了起来,“我马上回来。”她朝自己家走去。走过我们家的院子和她家的石板露台就到了。回来的时候,她带回来一把旧牙刷和一个大碗。
“你必须刷掉这些灰尘和松针,”她一边往下坐,一边指导着,“看我。”埃塞尔和我都密切观察着她的动作,当她温柔地刷着蘑菇伞和菌褶时,我们都发出了轻轻的感叹声,接着她用手指抠掉了大根的松针和顽固的橡树叶。
“乔治安妮,去你的厨房里拿一条案板和一把刀。”
我照做了。
“现在,割掉每个蘑菇伞柄最下面的部分,一点点就可以了。”
她说。
我按她说的做了。伞柄是中空的,割掉时流出的东西没有蘑菇伞那么多。
“我要试一试。”埃塞尔对乔琪特说。乔琪特笑了笑,把刷子递给了她,然后和她挤着坐在一起,刷着蘑菇。埃塞尔很成功地刷出了许多根松针和一点灰尘,乔琪特表扬了她。
“你把这些刷干净。”她把剩下的蘑菇推到了埃塞尔那边,然后她转头对我说,“我在去比道岩石的路上发现了这些。平常都是猎人先看到,不过这次不是。”她大笑着,解开了扎着红棕色头发的橡皮筋,然后把头发抓得蓬松了一些,又重新绑了起来。
比道岩石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那是一块突兀的巨石,矗立在山谷旁,保卫着我们的小小山谷。好几条山间小路都穿过森林,向山上延伸,一直通向巨石。站在巨石顶端,向北眺望,我能够看到阿尔卑斯山山脉的源头,耕地密布的山谷、小山丘和森林共同构成了我眼前的美景。有一次,唐纳德、埃塞尔和我爬到巨石顶野餐,同往常一样,我们的狗土恩也跟着我们。在巨石上,我们打开了一张餐布,把火腿三明治、新鲜的山羊乳酪和苹果放在了上面。
“还有,九月份的雨水非常充足,”乔琪特没有注意到我还沉浸在想象当中,继续说着,“所以今年我们会收获很多很多的蘑菇。九月的雨意味着十月的蘑菇。就像我们今天这样,血菇最好是烤着吃,还可以用盐腌或者晒干。有些人炒鸡蛋时会和着血菇一块儿炒,不过最好是用鸡油菌。最适合晒干的是牛肝菌,但是这附近很难找到,你得到博迪昂和阿格尼的森林里才能发现它们。它们喜欢海拔高的环境。有些人知道所有秘密的地方。至于鸡油菌……啊,太美味了!”
“你记得你放羊的那个森林吧?我敢保证,那里有许多蘑菇。要找鸡油菌的话,就沿着河边找。”说话时,她修长的手指一刻未停地清洗着蘑菇,她的手指甲剪得整整齐齐,有一只手指上带着一枚金戒指。
普罗旺斯的鸡油菌除了是季节性的食物外,采摘鸡油菌还是一项每年都会举行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仪式,是郊区和城市的美食日历上浓重的一笔。加入采摘鸡油菌的行列,便意味着开始理解普罗旺斯的美食与乡村风俗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最为顽固的都市人也将其珍藏为文化意识和美食遗产的一部分。这是我在普罗旺斯的生活中,最为重视的事件之一,不管经过了多少岁月,它似乎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我总是特别喜欢蘑菇。在二十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我住在南加州,那个时候,人们认为嫩白的蘑菇头都是国外产的,野生食用菌的五彩世界还没有成为我的法国生活和加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鸡油菌长得像一个小小的喇叭,很漂亮,呈淡杏黄色,”乔琪特解释说,“喇叭的一边会比另一边更长、更大一点。下面的菌褶是波浪形的,不是直的。你放羊的时候可以顺便找找看。”
这些年,我从乔琪特那儿学到了许多,首先学到的就是蘑菇的知识。她是我在普罗旺斯生活的头两年里认识的,不是那种典型的本地女人。她出身于一个政治气氛活跃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父母分别是左翼画家和学校教师。然而,她同许多农场主的妻子一样,尊重本地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因为成长于战争年代,所以她天性节俭,物资贫乏的年代和动荡岁月深深地影响了她,她珍惜每一份她制作的食物。
我们从乔琪特和她的丈夫丹尼斯手上租下了这个小房子,搬进去后,她就照顾起了我们最初的生活。她很耐心地教给我普罗旺斯乡村食物的传统,然后又通过我,教给了我的下一代——埃塞尔。我也感到她有一种强烈的个人情结:她不希望她的邻居——尤其是外国邻居——没有很好地了解当地的生活传统。这些传统大部分都是围绕着食物——栽种和收获的方式、采摘和清洁的方式、烹调和保存的方式以及庆祝的方式。看到我,她觉得她找到了一个很好学的学生。
“在森林里,我还希望你能注意到血菇。你现在知道它们长什么样了,那么就在橡树和松树底下寻找它们的踪迹。你还有可能会发现牛肝菌,我觉得你应该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继续解释前,她甚至没有停顿。
“它们的菌伞很圆,大小不一,但是没有菌褶,只有海绵一样的东西,奶油白的。不要被有黄色海绵一样的蘑菇给糊弄了,那些都不好。寻找蘑菇是本地生活的一部分,”她宣称,一边还检查着埃塞尔的劳动成果,“每年秋季,我们都很期待去采摘蘑菇。现在你也可以了!”
这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但是尽管乔琪特在烹调和食用野生蘑菇上都是权威,我还是很自然地有一种恐惧感。小时候住在南加州时,妈妈曾经很严厉地警告我们,千万不要接近前院草丛中周期性冒出来的白色和棕褐色菌类植物,因为我们不懂得辨别可食用菌和毒蘑菇,即使是碰一下毒蘑菇,都有可能感染上疣。根据她的想法,这种东西最好还是留给小妖精和仙人们去解决吧,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她用昂贵的新鲜蘑菇炖红葡萄酒煮鸡,那些蘑菇都是她从镇上的高级蔬菜水果店买回来的。
在葡萄枝上烹调的血菇慢慢地释放出了一阵温暖的大蒜香。当乔琪特为它们刷橄榄油时,油滴入了滚热的炭火中,发出嘶嘶的声音。我的蘑菇导师在盘子里放上了几块金棕色的蘑菇,于是我拿着牙签戳起来一块,突然间我感到一阵不安,妈妈的警告在我的脑海中回响着,但我还是咬了一口。血菇的口感很结实,有一点点粗糙的质地。我吃下的这块还带点泥土的气息,一点点松树味、大蒜味和橄榄油味也混杂在其中。看着埃塞尔吃下了第一个蘑菇,然后是第二个,我在想,她的儿时经历和我的该有多大的不同啊。
蘑菇刚刚烤好,唐纳德就回来了,于是我们聚在一起继续享用着,直到吃完了所有的蘑菇,然后我们用玫瑰红葡萄酒——丹尼斯从学校回家吃午饭的路上买的——洗干净了血菇。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乔琪特吮吸了一下手指,然后又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很棒,不是吗?”
“很棒。”我赞同地说,然后舔干净了嘴唇上的最后一点橄榄油。
午餐后,埃塞尔、我还有唐纳德一起回到了羊舍。我把剩下的干面包喂给了山羊们,接着,我们三个走进了森林,寻找蘑菇。我们把羊群关进了羊圈里,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把它们带进森林的话,那么大部分时间都会花在照看这群羊身上,而没有时间去寻找蘑菇了。我带上了一只篮子和一把刀。乔琪特告诉过我,要用刀砍下蘑菇,而不是扯出来,这样才能为下个季节的生长留下孢子。她说,通过那种方法,才能使蘑菇重新生长。
我漫步于森林中,不时地在锋利的杜松木丛中穿梭,避开异常低矮的松树树枝,眼睛还要始终盯着地面。树丛下的光线很暗,泥土因为下雨变得很潮湿,散发着似乎刚刚松过土的气味,像泥炭味一样浓重、刺鼻。我捕捉着菌类的芳香。我找到第一丛蘑菇后,马上就有一大堆血菇从发霉的层层树叶中冒了出来,我知道我被迷住了。这就像是一场寻宝之旅,只是奖品不是小时候从伍尔沃斯买的小玩意,而是野生蘑菇。我在法国的一座森林里,采集我自己的食物——而我成功了。
那天我照了张相,不过现在已经褪色了。我穿着一件橙色羊绒孕妇外衣,里面是一件紫色高领毛衣,头发往后在颈背处扎了个马尾。我的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而脚边是我的收获物。
那天我找到的蘑菇里,有些是一丛丛紧紧地生长在一起的,还有些是独有自己的一片天空。有一个异常巨大的蘑菇柄上有一团团黄色,脉络却是红色的。当我碰到它伞下的海绵体时,那上面晕开了一团深靛蓝色。这个东西看上去非常邪恶,我十分确定它有毒,因此我把它扔到了一边。
当唐纳德坚持说该往回走时,我的篮子里已经装满了蘑菇,有蓝色的、灰色的、紫色的、棕褐色的、金色的、白色的和棕色的。我每样都留了一点,没准其中就有能食用的,然后把那些明显太老的,正在腐烂的或者满是泥的蘑菇都给扔掉了。
回家后,我马上敲开了隔壁乔琪特家的门,向她展示我的收获。她迅速地在里面挑选了一番,把其中大部分都丢到了一边,只留下了一打左右。我的确发现了鸡油菌。“不错,不错,”她一边说着,一边挨个仔细检查着手中挑出来的四个。“这些都是牛肝菌,是最好的,里面还有血菇。很好,很不错。太棒了。”然后她告诉我,那些扔掉的都不是毒蘑菇,只是没有一个好吃的。
“那这个呢?”我从篮子里扯出一个红色的大蘑菇。
“噢,这个太恐怖了!根本不行,一点都不好!这是撒旦的牛肝菌!如果你吃下肚,它会让你大病一场的。马上把手洗干净,还好你没把这个同其他的混在一起!”我点了点头,于是她笑了。
“你知道它有毒了吧,不是吗?”我觉得她似乎很为我自豪。“接着,拿着你的蘑菇,按我教你的方式把它们洗干净,再做出一顿煎鸡蛋来吧。”她说,指着鸡油菌,“剩下的可以当牛排的调料。”
唐纳德在厨房的木炉子里升起了炉火,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开始清洗蘑菇。因为天色已晚,而我们肚子很饿,我拿出了一些面包、橄榄油和新鲜山羊奶酪当做我们的零食。我小心翼翼地把鸡油菌切成均匀的长条,然后和着青葱、盐和辣椒,用橄榄油在锅里煎炒。这时,它们散发出的味道使我们的小厨房都弥漫着一种陌生的香味,还带着一点点霉味和油腻味。变软后,我将半打搅拌后的鸡蛋倒了进去,然后撒上了欧芹。鸡蛋煎成饼状后,我从中间把其中一半轻轻翻起来盖住了另一半。等鸡蛋的边缘变硬,而中间还很柔软时,我把这道菜盛出了锅。我用那天采摘的绿色食物,迅速地做了一道沙拉,然后我们都坐下来,开始享用使用野生蘑菇做的第一道家常菜。
第二天,我做了一道炖肉,用的是牛肝菌和血菇。我把它们同大蒜、洋葱和黄油搅拌在一起,直到它们的颜色变成了淡棕色,然后我往锅里倒入一点白酒去渣,接着我用新鲜的凝乳和一些捣碎后的杜松子做成了调味汁。牛肝菌闻起来的味道和鸡油菌有很大的不同。牛肝菌含有更多森林的香味。根据乔琪特的建议,我想把调味汁浇到牛排上,但是和价钱较贵的牛排相比,加了格鲁耶尔干酪的意大利面会是更好的替代品。
那之后,我几乎每天都去寻找蘑菇,直到十一月份初,第一场大雾的降临,蘑菇的季节也结束了。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吃到各种不同做法的野蘑菇,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牛肝菌和鸡油菌炖兔肉和黑橄榄。而对于其他那些在森林里找到的不同种类的蘑菇,我们仅仅是把它们混在一起,然后用黄油、葡萄酒和大蒜调味,再把它们堆在烤肉上或者加到沙拉里。
我成了一个很成功的蘑菇采摘能手,埃塞尔和唐纳德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得不晒干我们找到的血菇,或者眼睁睁看着它们坏掉。我们吃不完这么多新鲜的蘑菇,于是,我们的另一个邻居玛丽告诉了埃塞尔和我怎么晒干蘑菇。洗干净蘑菇后,我们把它们切成条,然后用针线把切成的条穿在一起。我们很自豪地将蘑菇装饰物挂在木炉旁的椽上风干,接着,我们把它们装进罐头里贮藏起来。
普罗旺斯人对于采摘蘑菇有一种显而易见的热情,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根植于普罗旺斯人的集体记忆中——过去,蘑菇是乡村家庭餐桌上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出于一种对于寻找和采摘的热爱,这种热爱将普罗旺斯人与自然和土地联系在一起,即使他们已身处城市中。
在过去,知道蘑菇所藏的秘密之处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在食物上的安全感,就像在笼子里养着兔子或者在园子里种着蔬菜。如果有人收获了特别大一筐蘑菇,那么他在告知邻居或者亲戚时,还会带有一种沾沾自喜的胜利感。如果说食物带来的安全感已经不是主要推动力,那么那种胜利的情绪和对美食的期待仍然存在着。
这种感觉也降临在了我身上。不久之前,一位朋友的、非常富有的兄嫂从巴黎来旅游。在阿格尼附近,他们登上了圣特克瓦湖边的小山,寻找野生蘑菇。
“看这个!我们听说你很喜欢采摘蘑菇,所以我们也去摘了一点,看看我们找到的。”那个妻子说,顺手把她的阿玛尼外套放在了我的椅子上。她把一个装满了菌类的大篮子放在我们的桌子上,从里面挑出最好的几个。她在我鼻子底下挥舞着大而肥壮的牛肝菌和一把金色的鸡油菌,然后又把它们放了回去。当她在篮子里挑挑拣拣时,她手指上戴着的大钻戒和金戒闪闪发光,与她指甲里的泥土和手上的污泥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我半开玩笑地问她:“哪些是给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