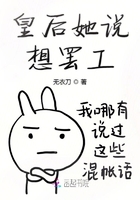住在小白楼的燕子们在白色小楼前的广场上空盘旋飞翔,好像在进行阅兵式前的练习。
它们一边滑翔,兜圈子,一边唧唧唧地叫着,它们的叫声有点儿歇斯底里。
它们在准备吵架,要把冬天借住在它们窝里的麻雀们赶走。
大多数燕子顺利地要回了它们的窝,嘟嘟囔囔清理那些不付租金的房客们留下的破烂儿。
应该是我到山里生活第二年的五月,正对着我窗口那只燕巢的驱逐战持续了好些天,到后来,我发现我的麻雀高邻取得了胜利,不但那个夏天,直到后来我离开,它们还住在燕巢里。
我对住在窗口上方燕巢里的三只麻雀产生感情,是在上一年初冬。
在第一场雪到来之前,燕子们又不告而别。
它们建筑在屋檐下、粮仓里、牛棚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燕巢又一次空了出来。
我向来不喜欢雏燕的叫声,小雏燕叫唤起来可吓人了,它们的父母回来送食物,它们张开比脑袋还大的大嘴拼命叫唤,好像它们的父母都患了近视眼,不能看见它们镶了黄边儿的大嘴丫子似的。
雏燕练习飞翔的时候,总是扯开嗓门,惊叫和惨叫。后来我同情地猜想,肯定是住得太高的缘故。小雏燕探头往燕巢外面一望,马上就眩晕了。
再说我的三位麻雀小朋友,在燕子们飞走的几个安静日子之后,用它们文雅的唧唧啾啾声打破了窗外的静寂。
几只小麻雀在墙檐拐角那里停留,朴素的羽毛上布满初冬晌午发白的阳光。
它们不停地蹦跳。你看见过的麻雀,都是怎样走路的呢?我的高邻是这样走的:它们双脚并拢,向前跳,一、二、三,然后停下来东张西望,或者啄几下地面。之后又是一、二、三,有时候也连跳四步或五步,它们很少一连气跳八步以上。你要知道,它们还有翅膀呢,如果要去远一点儿的地方,它们就不跳了,它们可以打开翅膀飞过去。
麻雀扭头向左右看的速度非常快,向下向上看的速度也很快,它们有一个不但很灵活也很结实的脖子,结实是关键。
麻雀们互相交流的时间比人类多,它们一边说话一边谛听,经常谈得热火朝天。
在那个初冬的晌午,那几只麻雀看上去很开心,它们在墙檐上来回蹦跳,四处打量。它们一会儿把小脑瓜伸出墙檐,向四层楼下面看,一会儿歪过小脑瓜向我工作室窗内看,一会儿依次蹦到拐角那边,叫我看不见,一会儿又蹦回来。
那之后几天便是立冬,天空中开始很正式地下雪了。
我的麻雀高邻把那段墙檐当作它们的起居室。
麻雀们在立冬之前换好了厚厚的羽绒衣,它们的脖子好像没有了,小脑袋直接挨着“大衣领子”。
早在来到小镇的第一年冬天,我就注意到小白楼前广场两边松树林里住着麻雀,大约有近千只,它们每天清早都要开会。
要说麻雀会唱歌实在勉强,你只能说它们进行的是短诗诵读,或者是说唱表演,它们的叫声过于短促,大致使用这样几字:唧、喳、啾。
这几个简单的字音组合起来经常是这样:唧唧。
喳、喳。
啾啾——啾。
北方冬天留下陪伴大地的鸟儿大致有三种:乌鸦、喜鹊、麻雀,前两者更是不擅长歌唱,虽然它们嗓门很大。
小麻雀们音质是很清脆的,虽然不会拉长音、打嘟噜,但是它们的鸣唱在冬日里显得极其珍贵。无论是一只麻雀在窗外木障子上蹲着独白,还是一大群集体朗诵无名诗篇,它们那欢快的语调,总是让人心里很明亮。
每天早晨它们的会议都认真而热烈,如果不是按照祖先的遗嘱为太阳的升起做感恩祷告的话,那么它们就是在讨论去哪里集体共进早餐。
当金红色的霞光消失,白山黑水依旧。麻雀们顷刻间飞得无影无踪,它们的纪律性可真值得学习。
松林安静了下来,如果不是那些遗落在雪地上和矮草上的鸟粪出卖行踪,这里好像从来不曾有过什么鸟雀停留。
我檐上这三只麻雀——松林里的叛逃者——虽然高高地住在松林之外的燕巢中,但是每天早晨也加入那讨论,拼命插嘴。可是群雀飞走后,它们不着急出去。
三只麻雀站在墙檐上,沐浴明媚的阳光。它们每个看上去都肚腹丰满,和贪恋啤酒的大肚男,慵懒滑稽的样子有一点相似,然而从形貌上来说,它们与它们整体和谐。
它们的羽毛丰满蓬松、柔顺,堆到脖颈处,使那小小的脑袋瓜愈发的小,正如上面所说,它们的脖子消失不见了。
它们从头盖顶上描画下来的一道黑墨,直到下颚的,还有脸蛋上的两小撮黑毛,衬托那双圆圆黑黑的眼珠子,显得更加警觉。它们的小爪子,几乎也要被长长的绒毛所遮盖,就像因为寒冷,时刻想揣到袖筒里。
它们这副尊容正如可敬的苇岸先生在写给麻雀的赞美诗里所描述的——它们的体态肥硕,羽毛蓬松,头缩进厚厚的脖颈里,就像冬天穿着羊皮袄的马车夫。
每一位认真观察大自然的人都是可敬的,如果他们能找到一个恰当的比喻,来把我们熟知的事物更生动地形容一番,就会更使人心生无穷的敬意。
别不多言,还是说说我的高邻赠与我的快乐吧。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天空中一朵云彩都没有,天空像一只倒扣的蓝色大瓷碗。北风停歇了,这是寒冬里一个比较温暖的早晨。
麻雀在墙檐上唧唧喳喳,甚至可以称得上大呼小叫,邀请声顽强地穿透两层玻璃,引起了我的注意。等我放下手头的工作,隔窗望向它们的时候,它们就开始表演了。
它们摆出各种姿态,小跳,假装啄食,其实墙檐上什么也没有,飞走,再飞回来。然后三只都跳到拐角后面,再一个一个探出头来,扭动脖子,转动眼珠,好像和我捉迷藏一般,这一次的表演竟然历时五分钟。
另一次使我难忘的,是其中两只麻雀堪称一部独幕剧的表演:
两只麻雀,一位夫人,一位先生。夫人蹲在墙檐上,看上去很不开心。
先生在夫人身边跳来跳去,还探头往下面看,并不断鼓动夫人也来看。
“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夫人说。
可是先生坚韧不拔,他认认真真地唱了一小段歌。这首歌也许是当年向妙龄的麻雀姑娘求爱时唱的情歌。这首歌终于使夫人消了一点气,所以,当先生跳到夫人身边,并挨着夫人蹲下的时候,夫人并没有扭头蹦开。
接着,在先生的轻声呢喃之下,夫人的目光随着他的目光一起向东方眺望。我抓起照相机,拍下了这幅画面。它们紧紧相偎,先生高大强壮,夫人娇小玲珑,它们葵花子一样的黑色小嘴儿紧闭,阳光在上面镀了一层亮金。他们头上的褐红色小帽儿也被阳光照耀得十分鲜艳,啊!多么温馨!多么美妙!那一瞬间,是一个使人“忘我”的幸福瞬间。
如果先生继续保持沉默,它们会那样多依偎一会儿。可是先生又饶起舌来,夫人气得跳到一边去,用尾巴朝向他,给他看背影。先生站起来,跳着,跳着,歪头向夫人发出各式各样的质问。夫人干脆扭过头去双眼望向遥远的虚空,这是怎么说的!这是怎么说的!先生张开翅膀,猛地一拍,跳到墙檐边上,把后背朝向夫人。它又不甘心,跳过身来,想再说两句,但是感觉到无话可说,无计可施,或者说,再也不想辩解……他就那么绝望地把自己缩紧,把小脑袋埋在翅膀下面。
那一场夫妻之间的别扭以它们先后飞回燕巢而结束。
细细回想起来,我见过的麻雀超过几千只,可是,我分不清它们谁是谁,也不知道它们能活多大年纪。
它们是最普通的鸟儿,是住得离人群最近的鸟类,可是我没有交过一位麻雀朋友。
若非我的工作室离被麻雀霸占的燕巢那么近,我可能一生也不会知道麻雀一年四季是要换衣裳的。
我也难以想象在夏天里,孵育期的麻雀有多么辛苦。
在炎热的夏天,我亲眼目睹了一只麻雀,我猜是那一家的先生,在墙檐上来来去去,叼着羽毛、草棍儿,有时是一只蚂蚱,还有看不清的东西,在墙檐上稍事休息,然后飞回窝里去。它是那么消瘦,又细又长,简直叫人怀疑它还是不是麻雀。有好几次,我看见先生叉着腿,站在墙檐上向窝里大声焦急地叫,风吹弹它胸脯的绒毛,将一撮竖起来,它的样子很是狼狈可怜。
我可爱的高邻为什么有时候三只一起生活?有时候又是两只呢?它们每年共孵几次幼雏,每次孵育几个儿女?在我看见三只麻雀的时候,那个陪它们过冬的是它们的女儿还是儿子?它为什么留下陪伴爸爸妈妈?
后来这个孩子它去了哪里?它们分别的时候会不会难过,父母会不会给它叮嘱,一遍又一遍?
麻雀夫妻一生孵育多少儿女?它们住得离它们远吗?它们经常回来看望它们的父母吗?它们在采食的时候能偶然遇见吗?遇见时会打招呼吗?
当然,当然,当然!所有人类能做到的,可爱的麻雀们都会做到,甚至它们会比我们做得更多更好。
我这样猜测着它们。它们是否懂得我和他人言谈时的话语?
它们是否看见了我的一切?它们晚上很晚了还不睡,小声地唧唧哝哝,是不是在议论我白天所做的一些事情的对与错呢?
当我的这些麻雀高邻在借住燕巢第二年春天时,我有小小的欢喜,我已经对它们产生了感情。
可是它们都不曾吃下我的一粒米,我撒向墙檐的所有食物,未曾有一粒被它们笑纳。
多么骄傲的小东西!
有时候我想变成一只麻雀,跟我的高邻生活一段时间。看看夜晚蹲在燕巢里看见的星星是不是和我现在看见的一般大?
我相信作为一个人,在夜晚睡在严实的房子里,肯定会失去很多看见天空中出现神奇景象的机会,这算是一种遗憾吧!
如果下很大的雪,无法找到食物,除了去农家的院子里分享小母鸡的麦粒儿,麻雀们还有什么方法获得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