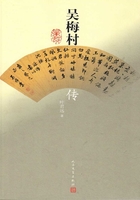我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何会违背自己的意愿,落入了婚姻的俗套。长期下去,我只能失去自我了。在经历了痛苦的反思之后,我决定从婚姻的迷宫里走出来,走进柏林的文学和艺术界。
当时,柏林集中了一批文学和艺术的精英,他们有着不同的派别,分属不同的俱乐部,大家自由地讨论着各种问题。我家的房子虽不够雅致,但面积足够大,经常有各种沙龙在这里举行。
那个冬天,我们认识了一些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像我们一样,生活在城市的郊区,例如作家格哈德·霍普特曼和他的妻子玛丽。在自然主义兴起并引起广泛争论时,他的《日出之前》这个剧本给舞台带来了一种新的东西,这种东西有助于自然主义这个新的思潮在文艺中取得新的成果。尽管这部戏的本质是说教性的,它呼唤的是好公民形象,但它具有抒情诗的笔调,能给人美好的感觉。后来,我常去霍普特曼家做客,他的妻子可以说是贤妻良母,为他生育了三个儿子。我和他很能谈得来,我们之间也曾在大量的书信往来,可惜后来应他的要求,将这些书信毁掉了。他是一个好男人,一丝不苟地维护着他的家庭的美满。
在我结婚之前的日子里,保尔曾有意地避开波希米亚文人的圈子,我们交往的范围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学术界的,但这种情况现在改变了。我从来不曾对文学这样地感兴趣,也许我是想从生活之外寻找一种补偿,或者说是寄托吧。《为上帝而战》那本书的成功,让我树立了对文学的信心。
当我涉足文学时,我感到自己很无知,对乐观主义一无所知,而当时一场新的争论就是针对那种乐观主义发动起来的。新精神所鼓吹的是青春的快乐、活跃和自信,甚至于当我们在处理最黯淡无光、最令人压抑的状态时也是如此。那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人性因素。亨利·易卜生的声名如洪水般漫过整个德国,为我打开了一道堤防的缺口。
易卜生是挪威的剧作家,是十九世纪末最具批判性的剧作家。安德烈亚斯是个语言学家,能懂多个国家的语言,他把易卜生的作品介绍给我,向我朗读挪威语本的原文,一边读一边还译成德语。他的作品多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为妇女解放而呐喊,他把众多女性从漫无目标的迷途中解救出来,我甚至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易卜生最著名的剧本有《玩偶之家》、《群魔》、《海上夫人》等,不同的主人公代表着当时妇女不同的生存状态。可以说,易卜生塑造的这些人物形象,让我感动和着迷,让我下决心沉入其中进行深度研究。
1892年,我出版了《亨利克·易卜生的女性形象》一书,除了分析、阐释易卜生笔下的人物形象外,还在他的剧本的基础上创作了一部童话剧。
这本书的出版,让朋友们对我的文学才能又有了重新的认识。以前,有人向我泼来的“沙龙里的俄罗斯花瓶”的污蔑之词,也销声匿迹了。
通过阅读易卜生,我对戏剧产生了兴趣,我同柏林的“自由舞台”戏剧协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然,他的剧作也让我看清了摆脱家庭束缚的出路。
这时,两座新兴的“独立剧院”出现了,其中一座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布拉姆和易卜生、霍普特曼等人的共同领导下,不断地取得进展。我跟独立剧院的创始人之一马克西米连·哈登的友谊,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而且一直延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霍普特曼博士直到那时,都还想在哲学领域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也在提倡对戏剧的热忱。年轻人为了文学和政治目标,抛弃了他们的学术雄心。我把许多个夜晚都花在跟库聂曼的争论上了,那时他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要一辈子在大学里教书。
当时,在那些我最亲近的人之中,从人性意义上而言,最重要的是乔治·勒德布尔。
我们是在1892年春天相识的。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并没有听清他的名字,他也没有听清我的名字。沙龙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第二次见面时,有人给我们做了专门介绍,我注意到他十分在意地看了我的手。我正要问他看什么时,他粗声地问:“你不是结婚了吗?为什么不戴结婚戒指?”我笑着告诉他,我们忘了买戒指,并且现在也不打算买那玩意了。他几乎是带着威吓的语言对我说:“你得戴戒指!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不戴戒指像什么样!”正在那时,有人以嘲笑的口吻问他,他对波罗曾湖上的夏日和风感觉如何,岔开了我们的话题。他刚刚结束在那儿为皇帝的服务。我禁不住发现这挺滑稽的:我居然为没有戴戒指这件事,在社会道德上受这样的指责。事后,他心情明显低落,而在那之前,他一直精力充沛地与别人攀谈着。
很奇怪,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忘了曾经的不快。几个星期后,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在回来的路上,勒德布尔向我表白了他的爱,说愿意来爱我,让我享受作为一个女人该有的幸福。就像是在为他的想法申辩似的,他又说了一句让我感到莫明其妙的话:“你不是一个女人,你是一个女孩。”
勒德布尔这不可思议的认识,让我感到百般震惊。对我丈夫来说,我确实还不是一个女人。不仅在当时,还在在后来,这种震惊的感觉一直湮没了我,使我无法断定自己对他的态度。我对他可能也有类似的感情,但还有达到一定的程度,甚至只是潜意识的。这份突然而至的感情同样让我感到震惊,也许其强烈程度甚至超过了最有美德的有夫之妇在不知不觉间发现自己开始陷入情网时所体验到的那种震惊。我丈夫的天性与自然之间有一种难解难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会有一丁点的松动,与之相比,神圣的婚约和社会契约,一旦思想出了轨,会是多么地不堪一击。
我很快地受制于这种震惊的感觉。甚至在我们订婚之前,甚至在我们发下永恒的誓言的时候,我们已经各行其是了。但是,我丈夫知道这件事后很激动。他不是瞎子。他宁愿一了百了地把情敌戳死,也不愿跟人谈论这事。他嚷着要找这个人决斗。
我对勒德布尔的感情跟爱情还是有些不一样。换句话说,我更多地是想逃开当时的处境,逃开我和安德烈亚斯之间的压抑氛围。我为这样的想法感到害怕,日夜受着痛苦的折磨,我们俩在一起约会的时间越来越少。出于友谊,朋友们帮助我,为我们创造见面的机会,把我从孤独之中拯救出来。但是,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他因为我而感到恐惧和忧虑,这使他的情绪紧张无比,反过来又使我受到更重的折磨。
我陷在与勒德布尔的情感纠结之中,难以自拔。
这年6月,我决定放弃与勒德布尔的感情,一年之内不再见他。一年以后,我的心放下了这个男人,我们分手了。在这之间,我们已经再次搬家——施马根多夫。那是在柏林的另一片郊区。这样,我们柏林文艺界的朋友交往就没有原来方便了。
我和安德烈亚斯在柏林附近的森林生活了近六年,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婚姻处于崩溃的边缘。主要原因除了不断有人向我示爱外,还因为我和丈夫在婚约中的约定,阻挡着我们走向水乳交融的夫妻关系。
保尔出走后,我和保尔的友谊不再是我们夫妻间的障碍了。对于这一条,安德烈亚斯本来以为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但是他想错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在这一点上是如此的固执。我对身体的坚守又是为了谁呢:基洛特?保尔?还是一个不相干的人?
新搬的房子极小,无法举行沙龙活动,往来的人少了很多。我们居住在一片湖水旁,在大自然的熏陶下,家庭又慢慢地恢复了平静。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我们自己在收拾房子,房租和其它开支下降,家庭的经济紧张状况开始缓解。安德烈亚斯在学校里有固定的授课费,平时给报刊写一些文章。我除了每个月从彼得堡得到一笔固定的费用外,稿费收入也是日渐增加。
这是一种不平常的平静生活,是风暴之后的暂时平静。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无法长期在家里坐下来。我需要出门,透透气——给我的生活和思想寻找更多的生机。我不能给安德烈亚斯想要的东西,我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后来,我决定找一个女佣,找一个既可料理家务,又能照顾安德烈亚斯起居生活的人,这个人最好能够成为家庭中的一员,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一个家庭主妇的角色。这样,我就可以有了更多的自由。
尽管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安德烈亚斯也不排斥。我们进行了细谈之后,他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后来,我们还答成了一项新的协议:在不伤害婚姻的条件下,双方都有和其他人交往的自由。
1894年,我去了巴黎。那时,正值卡诺总统被暗杀,各个方面的人都被卷进了政治的漩涡,文坛也格外兴奋起来。安多瓦内的“自由剧院”开张了,它跟柏林的“独立剧院”相似。霍普特曼的《阿内尔》中的女主人公曾经在柏林由宝拉·康拉德扮演,她后来成了施莱特尔的妻子,安多瓦内在舞台上把它演成一个贫穷、苍白的街头小女孩形象。后来在俄罗斯,我看到了最令人心动的《阿内尔》,它用克制而朴素的拜占庭风格表现了天堂和救世主。
我丈夫在学校研究领域完全在我的知识和理解之外。后来,虽然我们俩关系很近,我成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学生,而且在他的专业方向上显示了才华。但是我的行为只停留在肤浅的表面上。我们就这样自我蒙骗着,直到下一次分别不可避免地到来。
因为我们一直很忙,这让我们之间相处也简单了许多。安德烈亚斯在柏林的东方研究所占有一席之地,这使他能沉迷于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由于这份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培训外交官或实业家,让他们关注亚洲,他只需要拿出部分的学术能力就足以对付。他的同事罗森离开研究所后,从事外交事务,当上了大使,后来又当上了外交部长。他说我丈夫是个书呆子,不懂得如何让学问创造实际的价值,比如别人要求他提供牛奶,他不知道偷偷地生产一些奶酪。不过,在我看来,是我丈夫从牛奶上撇去了奶酪!换句话说,他通过研究不同的部落和它们的方言,就像是提供了一种浓缩的牛奶,这种牛奶从来不仅仅具有学术的价值。
他收到了一些合适的学生。其中,包括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他的索尔夫。尽管如此,安德烈亚斯最终没能保住这个职位,因为别人只准他提供牛奶,这就像个工厂里普工的活儿,谁都可以来做。
所有这一切,与是说是某种外地的压力导致的厄运,还不如说是他本性的表现。
那种生活对他来说似乎是必需的,我很快就适应了,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目标。当我听说他想去波斯湾亚美尼亚的爱齐米阿德欣教区进行考察时,我做好了离开欧洲跟他一起去的准备。我慢慢地像他一样地生活,比如在生活上尽量俭朴,经常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每天锻炼身体等。尽管我生长于北方,有着北方人的习惯,但我的一生都在适应这些变化。我们俩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共同爱好的领域:那就是动物世界。
这个没有人的世界,动物们的生活更加简单朴素,我们人类已不可能再过那样的生活了。我们对单个动物的态度,往往类似于我们对单个人的态度。
安德烈亚斯往往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他的工作之中。相比之下,我就缺乏目标和雄心,我随时准备去适应别人和环境。我甚至说不出,人生的哪些东西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我现在的举止变化不定,跟我早年青春时期相比,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不仅仅表现在我跟青春伴侣的关系上,而且表现在我跟周围的所有朋友的关系上。它还存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之中,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是否会走在同一条路上,他们在一起能走多远?这样的问题相对来说,是没有害处的,我们可以从精神上去回答。可是,现在这样的问题甚至不再出现了,因为我所面对的是我一直都在承担的职责。这种职责是别人无法分担的。
我无论何时想到安德烈亚斯,心中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念头,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冲突的人。虽然我和他的距离太近,让我无法完整地描述他的形象,但我还是愿意尽力把他勾勒一下。这样,别人也可能从中了解到一些为什么。
安德烈亚斯生来就是东西方的混合。他的外祖父是德国北部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移居爪哇岛后娶了美丽温柔的马来西亚女子为妻,后来还写过一本如何照顾热带病孩的书。
安德烈亚斯6岁时,父亲移居汉堡,14岁时家里把他送到日内瓦上高中。在那里,安德烈亚斯显示了他对语言和音乐的浓厚兴趣。他先后在德国的几所不同的大学里学习东方语言,专攻波斯语。1868年,他从埃尔兰根大学毕业,又到哥本哈根大学读研究生,直至普法战争爆发后才被家里招回。
战争结束后,安德烈亚斯到基尔继续从事古波斯语及文献的研究。1882年,政府组织波斯考察团,这正合他的心意。于是,他报名参加,实地考察中东的风土人情和历史。不过,他又有些矛盾:是作为一个怀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欧洲人在那儿开展工作呢,还是如同漫游般地在那儿体验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