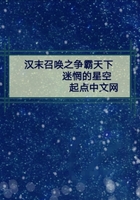一夜的秋雨,把阳安关周围的山山岭岭冲洗得一尘不染,山山葱绿可爱,岭岭青翠悦目。只有那纵横交错的溪流,变得浑浊了,夹带着许多灰尘泥沙,漂浮着枯叶衰草,汇入了西汉水,使这条河中的水位猛涨,咆哮着一泻而下。
钟会骑在战马之上,率领着数万伐蜀大军,急急忙忙地向着阳安关进发。可能是他已经饱览了秦岭的自然风光,产生了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对周围的这山色美景失去了新鲜感和兴趣,因而一路上头也不抬,只是低着头匆匆地赶路,偶尔还自言自语着:“阳安关!阳安关……”
钟会的自言自语被身边的参军羊琇听到,小声地问道:“镇西将军莫非为夺取阳安关而忧虑乎?”
钟会扭过脸去瞅了瞅羊琇,微微地点了点头,低声问:“羊参军,汝以为阳安关可夺取否?”
羊琇不假思索地回答:“阳安关乃蜀中之门户,不夺取此关,伐蜀便将半途而废,无功而返。故而,阳安关非夺取不可。”
钟会又微微地点了点头,沉吟片刻,再次问道:“以汝之见,我军拼上两万兵士,花上十天时间,能否将阳安关夺取过来?”
羊琇摇了摇头,担忧地说:“阳安关地势十分险峻,城池坚固,若是强攻,恐怕伤亡四万将士,花上一个月工夫,也未必能把此关夺取过来。”
“这……”钟会的脸上布满了愁云,忧心忡忡地说:“如此一来,待我军攻下剑门关后,岂不是已无兵可用、无将可使,还谈何灭蜀?”
羊琇淡淡一笑,引而不发地说:“难道阳安关非强攻不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乎?”
钟会紧皱着双眉,无可奈何地说:“我军除强攻之外,又有何计可施、何法可用!”
羊琇含笑提醒钟会:“难道镇西将军忘记了寿春之战?”
“寿春之战?”钟会沉思了一下,脱口而出,“莫非羊参军欲施反间计?”
“此计镇西将军最为精熟,何不再故伎重演,智取巧夺阳安关!”羊琇微笑着说明自己的用意。
“此计好是好,然而向何人去施?”钟会一筹莫展地说。
羊琇收起了笑容,若有所思地说:“据末将所知,阳安关守将傅佥,虽作战勇猛,善于冲锋陷阵,但其智谋却稍显不足,且为人诚笃忠厚,难免有时会真伪不辨。阳安关副将蒋舒,乃志大才疏、追逐利禄之徒,原为武兴督,因治军无方,被姜维革去职务,遣往阳安关助傅佥守关。此人心胸狭窄,对被革去武兴督一职耿耿于怀。镇西将军何不略施小计,离间傅佥与蒋舒,使其二人离心离德,相互猜疑。只要阳安关之守将与副将二人有隙,何愁关城不破!或许还可不攻自破。”
听了羊琇的这番话,钟会脸上的愁云散去不少,紧锁的双眉也舒展了一些。他赞赏地瞅着羊琇,感慨地说:“稚舒之言真乃一字千金,使我如同拨云见日,豁然开朗。”
羊琇款款一笑,谦逊地说:“在其位而谋其政。我既然身为参军,岂能不尽职尽责。”
“看来,我执意要选稚舒为参军,实属明智之举!”钟会亲切地瞧着羊琇,深有感触地说,“古语云: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以为,有其母也必有其子。稚舒有辛老夫人那样仁义礼智信均不让须眉之女中豪杰为母,真是三生有幸!”
“家母……”羊瑗的脸微微一红,欲言又止,略皱双眉,沉思不语。
羊琇字稚舒,乃魏国太常羊耽之子、羊祜的从弟。大概是由于血缘关系亲近的原因吧,他的相貌与堂兄羊祜有些相似:双眉浓而且长,两眼大而且亮,额头宽阔而饱满,体态丰满而矫健,显得神采奕奕,气度不凡。因他比羊祜要年轻十来岁,更显得俊美潇洒,风流倜傥,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股子精明干练劲。家族的遗传使他聪敏超人,过目不忘;家庭的熏陶使他酷爱读书,遍阅典籍,下笔千言,出口成章。这一切,使他在洛阳的那些豪门望族的公子之中颇有名气,就连官高权重、春风得意的钟会对他也极为欣赏。
羊琇少年成名,还因为他有一位传奇式的母亲。其母辛宪英,是魏国侍中辛毗之女,不仅聪颖过人,才华出众,而且深明事理,甚有见识,颇有大丈夫的气度,在魏国朝野声誉甚高。
当初,魏文帝曹丕被立为太子时,曾搂着丞相长史辛毗的脖子激动地说:“辛长史,汝知我内心之喜悦否?”其兴奋欣喜之色,溢于言表。
辛毗回家后,把此事告诉了女儿辛宪英。辛宪英听罢,长叹一声,感慨地说:“太子乃将来代替君王主持宗庙社稷之人。作为储君,不能不为国家之安危而担惊受怕。被立为太子,应该忧愁恐惧,居安而思危,而不应喜悦异常。但当今太子却反其道行之,如此一来大魏岂能持久,国家安能昌盛!”
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辛宪英预言的正确无误,曹丕以魏代汉后,仅仅过了三十余年,魏帝便成为司马氏的傀儡和玩物,曹魏政权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当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之时,辛宪英的弟弟辛敞为大将军曹爽的参军。当时,曹爽的司马鲁芝要率领大将军府的府兵冲出洛阳城去见曹爽,并约辛敞一同前往。在此紧要关头,辛敞十分害怕,不知该不该去,便问姐姐辛宪英:“天子与大将军去拜谒高平陵,太傅关闭了洛阳城门。城内四处传言,说太傅要篡权夺位。姐姐以为如何?”
辛宪英思忖了一会儿,冷静地说:“此事之结果如何,目前还尚难断定。不过,以姐之见,太傅是出于无奈,才不得不如此。明皇帝临终之时,曾经拉着太傅之手,将后事托付于他,此事朝野之人记忆犹新。大将军与太傅。虽然同为明皇帝托孤辅政之重臣,但他却把太傅排斥在外,自己独揽朝政,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既不忠于王室,又无治国才能,且多行不义之事,刑罚繁多,徭役沉重,朝野内外,怨声载道。故而,姐以为,太傅此举,并非要篡位,只不过是为诛灭曹爽及其心腹死党而已。”
听姐姐这么一说,辛敞顿然醒悟,忙说:“如此说来,我就不应与鲁芝一起去见曹爽。”
辛宪英白了弟弟一眼,正色说道:“汝焉能不去见曹爽!忠于职守,此乃人之大义。凡人在遇难之时,尚还有人怜悯体恤;何况汝是曹爽部属,若是放弃职责,此非祥事。为人做事,为人去死,才是尽职。汝只管随着众人而去便是。”
辛敞最终还是听从了姐姐之言,随着鲁芝等人出了洛阳城去见曹爽。
事情果不出辛宪英所料,司马懿在政变之后,只是诛灭了曹爽兄弟与他们的一些心腹死党,并未处置辛敞等其他曹爽的属官。为此,辛敞感叹地说:“我若不听从姐姐之言,几乎成了不仁不义之人!”
这两件事在魏国的朝野广为流。
据《三国志》载:建安二十五年(220),魏王曹操病逝,其长子曹丕继承了魏王爵位,任丞相,改元延康。这年冬天,汉献帝刘协被群臣逼迫无奈,只得遣御史大夫持节奉玺绶诏书,将帝位禅让给曹丕。曹丕假意三次上表辞让,群臣再三劝进。于是在繁阳(今河南临颍西北)筑受禅坛,曹丕登坛受禅,即皇帝位,国号日魏,改元黄初。《三国演义》第八十回“演义”了此事。传,使辛宪英的声誉大为提高。可能是由于这种缘故吧,钟会在出征攻蜀之前,再三恳请司马昭,执意要选辛宪英的儿子羊琇为参军。辛宪英得知此事后,哀叹地说:“从前我为国家之事担忧,今日灾难却降临到了我家。钟会居心叵测,不甘久居人下,我担心他此次率军伐蜀,会生出事端,殃及我儿。”
尽管羊琇遵照辛宪英之命。以母亲年老多病为由,三番五次地恳求司马昭,不要让他随军出征伐蜀。但司马昭听信了羊祜与杜预之言,另有所谋,坚决拒绝了羊琇的恳求。羊琇万般无奈,只好违心受命。临行之前,辛宪英语重心长地叮咛羊琇:“孩子,事已至此,汝就去吧。出去之后,汝要多加戒备。古之君子,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效忠国家;在其位而谋其政,安分守己,尽职尽责。”
正因为如此,当钟会以敬佩和赞颂的口气提到辛宪英时,羊琇又想起了临行前母亲对他语重心长的叮咛,心中未免有些不是滋味,所以略蹙双眉,沉思不语。
钟会不知这其中的秘密,见羊琇沉思不语,他再次钦佩地说:“辛老夫人乃古今少见之巾帼英豪。稚舒方才所言,莫非老夫人授予汝之妙计?”
羊琇尴尬地笑了笑,掩饰地说:“家母年事已高,精力衰退,只求安度晚年,早已不问政事。”
钟会赞赏地瞧着羊琇,高兴地说:“如此说来,稚舒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汝方才所出之妙计良策,若能实现,将使我军几万将士免于伤亡。此次伐蜀之首功,非汝莫属!”
羊琇有点难为情地低下头,不好意思地说:“末将只是抛砖引玉,此计能否得逞,还靠镇西将军精心安排。我不过是愚者千虑,偶有一得而已。”
钟会与羊琇正说着,一匹快马驮着信使从阳安关方向飞奔而来。钟会不由一愣,暗想:难道是胡烈所率兵马出了事?
就在钟会愣神之时,那信使已来到了钟会的马前,飞身下马,单膝跪地,高声说:“小人奉胡将军之命,特来向镇西将军报捷!”
“报捷?”钟会又是一愣,“捷从何来?”
“我军西路兵马在胡将军率领之下,已把阳安关夺取到手!”信使兴奋地说。
“胡将军已把阳安关夺取到手?”钟会惊奇地睁大眼睛,半信半疑地打量着那信使,诧异地问。
“是。我军已把阳安关夺取到手!”信使提高了声调,郑重地回答。
“此话当真?”钟会对胡烈能如此迅速地把阳安关夺取到手觉得不可思议,仍有些将信将疑。
“小人岂敢谎报军情。”信使严肃地说,“小人离开阳安关时,胡将军正令人打扫战场,准备迎接镇西将军及大军人关。”
钟会大喜过望,悬了多日的那颗心终于落了下去。他两眼放出异样的光彩,惊喜地问:“胡将军用何妙计,竟然如此迅速地就把阳安关夺取到手?”
“是蜀军阳安关副将蒋舒主动投降献关……”信使将夺取阳安关的经过叙述了一遍。
“此乃天助我也!”钟会喜不自胜,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仰天长叹。然后,他又用欣赏的目光注视着羊琇,颇为惋惜地说,“稚舒真是料事如神。只可惜那蒋舒已抢先献关,使汝失去一次建立奇功之良机!”
羊琇淡淡一笑,坦然地说:“阳安关已夺取到手,此乃我军将士之福!末将只求尽职尽责,不求建立奇功。”
“妙哉!辛老夫人真是教子有方,稚舒实乃高雅之士!”钟会感叹地说。随后,他便扭过脸去,大声地吩咐亲兵,“传令全军,加速前进,中午到阳安关用饭!”
一夜的秋雨,不仅将阳安关周围的山山岭岭冲洗得一尘不染,而且也把阳安关内那一摊摊的鲜血冲刷得荡然无存,只有那万余具魏、蜀两国将士的尸体,已经被雨水泡胀,像一只只吹足了气的皮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关城内的每一个角落;有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散发出一股股的臭气,招惹来一群群的苍蝇,嗡嗡乱飞……
久经沙场的胡烈心中清楚,如果不赶快把这些尸体清理出去,一两天之后,关城内就会臭气熏天,不仅无法屯驻兵马,而且还可能发生一场大瘟疫,把数万魏军将士送进地狱。于是,他便命令蒋舒带领着归降的三千蜀军将士,把关城内的那些尸体搬运到鸡公山的峡谷中掩埋起来。
蒋舒自骗开关门、献出阳安关后,心中十分得意,以为自己为魏军伐蜀建立了奇功,按理他应该得到重重的赏赐和封侯晋爵。因而,一大早,他便不顾伤痛,吊着那条被傅佥刺伤的右臂,沾沾自喜地前去见胡烈,企图从胡烈那里探听出魏国到底能赏给他多少金银珠宝、封他个什么官衔和爵位。然而,令他失望的是,胡烈好像把他献关立功的事情完全忘记了,不仅只字不提对他的封赏,反而令他带领着那三千归降的蜀军将士去搬运掩埋关城内的尸体。
胡烈的这道命令,简直是一盆冷水,劈头盖脸地朝着蒋舒浇来,把他心中熊熊燃烧的希望之火浇灭了。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哭丧着脸说:“胡将军,此事恐有些不妥……”
“有何不妥?”胡烈白了蒋舒一眼,粗声粗气地说,“我军将士已经连续行军多日,体力消耗甚大,急需休整数日,方可恢复过来。汝所统领那三千兵士,体力无所消耗,且对关城四周之地形和道路熟悉。”
蒋舒虽心中大为不快,但他又不敢当面顶撞胡烈,只好装出一副伤痛难忍的模样,龇牙咧嘴地说:“胡将军,蒋某昨日夺取关城时被傅佥用剑刺伤,现疼痛难忍,恐怕无法担当此任。请胡将军……”
“身为武将,带伤作战乃是常有之事。何况此次搬运尸体,汝只需动口,无需动手,有何不可?”胡烈打断了蒋舒的话,又白了蒋舒一眼,不容置疑地说,“今日午前,必须把关城内之尸体搬运掩埋完毕,不得有误!”说罢,转身而去。
蒋舒呆若木鸡似的望着胡烈的背影,又气又恼,只觉得胸中憋闷得难受,真想撒手不管。然而,他如今已不再是阳安关的副将,而是魏军的一员降将;他如今面对的也已不再是忠厚老实的傅佥,而是严厉无情的胡烈!他第一次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也对自己投敌献关的行为是否划算产生了怀疑。可现在是木已成舟、米已成饭,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他哀叹了一声,勉强地指挥着随他降魏的三千兵士去搬运掩埋尸体。
搬运和掩埋尸体,这是兵士们最讨厌干的事情。他们宁肯到战场上去拼杀搏斗,也不愿与那一具具尸体打交道。因为前者可以表现男子汉的勇猛和强壮,激发出他们的阳刚之气;而后者只能使人一次次地面对死神,从而在心灵上留下一片片不易散去的阴影。有些本来作战勇猛的兵士,在搬运掩埋过几次尸体以后,就会变得心灰气馁,甚至产生变态心理。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胡烈才令蒋舒带领着归降的三千蜀兵,去干这种影响士气和斗志的事情,而不让他所率领的魏军兵士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