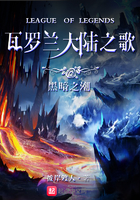(一)主张“开民智”,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作为康有为主要助手的梁启超,同他的老师一样,都持有“教育救国论”的观点,他也认为国家富强的根基在于文化教育。
“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中国之衰乱由于教之未善。
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梁启超还进一步阐述了“民智”和“民权”
的关系。他说:“今日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这就是说,只有首先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然后才能在中国实现民权政治。因此他竭力主张应该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加强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宣传。
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作是“开民智”
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所以,他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这实质就是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培养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上,而人才的培养又必须依靠发展资本主义教育;要建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首先就必须反对和改革封建主义的、培养封建官僚后备军的科举制度。梁启超认为这是变法图强的必由之路。这个主张不仅是在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而且也是一切资产阶级维新派教育思想的共同特点。
梁启超看到了要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必须依赖于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和要培养一支具有专门学识的知识分子队伍,二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这是一种十分卓越而深刻的见解。然而,他却过分地夸大了教育的作用。
在当时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历史条件下,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首要手段,就其爱国主义的热情来说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不从根本上废除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教育救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其他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相比较,梁启超有一点是十分突出的,就是他强调教育要有明确的“宗旨”,即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他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人类与动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做事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更不能没有目的。“事无宗旨犹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他还愤慨地说:“夫培养汉奸之才,亦何尝非人才;开奴隶之智,亦何尝非民智?”他批判了当时传统的养士教育,它所培养的“读书人实一种寄蠹也”,即一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象这样的教育目标,自然是培养不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来的。
梁启超在他所着的《新民说》中,提出教育的目的应该在于培养新一辈的国民——即所谓“新民”。他认为这种“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他并详细地论述了“新民”应具备的特性和品质:“公德”、“国家思想”、“权利义务思想”、“自由”、“自治”、“进步”、“合群”和“尚武”等各种品德。例如他说:自由是“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
自由是针对奴隶性而言的。所以他又说:“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
他竭力宣传“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教育家者,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焉、农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
梁启超的《新民说》洋洋10余万言,引证古今,炉冶中西,激励奋叹,危苦陈言,其用心全在于塑造新的国民。
从实质上来分析,梁启超所谓的“新民”,就是资产阶级的新一代,即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观点和道德修养的人。梁启超的“新民”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是一种进步的教育观点。
年以后,国内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成立起来。在这些新式学堂里受教育的青年。
如饥似渴地觅读新书新报,梁启超的《新民说》就是受他们欢迎的书刊之一。
至于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中国所以衰弱的主要原因,不是归结于清政府的腐败卖国,而是归因于旧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只有个人利禄思想,这个结论,本末倒置,无疑是错误的。
(二)变科举、兴学校的教育主张
废八股、变科举、兴学校,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大贡献。
首先,梁启超对科举制度的腐朽性作了深刻的揭露。他在《戊戌政变记》中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大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才乎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就是说,如果不改变科举考试制度,知识分子仍然被功名所引诱,不愿意入新式学堂,就算开办了学堂,也起不了培养人才的作用。所以梁启超愤慨地指出:“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天下扼腕殷忧,皆以人才乏绝,无以御侮之故,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举不变致之也”。因此,他们向光绪皇帝建议“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类似上述抨击科举制度和八股的言论,在当时梁启超和其他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着作中几乎俯拾皆是。总的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在科举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只能是一些愚昧无知、脱离实际、抱残守缺的封建卫道者。资产阶级维新派对科举制度的这些揭露和批判确是尖锐辛辣,鞭辟入里,触及了封建主义文化教育的本质。由此可见,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站在发展资本主义的立场,所以他们对科举制度的危害性是具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同时,这种批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正是由于他们对科举制度的严厉批判,使人们视八股取士为腐朽的东西,把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从封建统治的文化教育束缚中解放出来。虽然在变法失败后,顽固派曾一度恢复八股,但由于大势所趋,社会风气已开,后来科举终于废止了。
正如维新派人士欧榘甲所描绘的:“斯时智慧骤开,为万流沸,不可遏止也。及政变而后八股复矣,然不独聪明英锐之士,不屑再腐心焦脑,以问津于此亡国之物,即于高头讲章,舌耕口穑数十年,号为时艺正宗者,亦谓诵之无味,不如多阅报之为愈矣”。这种风气的改变,确是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不可泯没的功劳。
梁启超同康有为一样,一方面主张变科举,另一方面也积极提倡兴学校。一方面,他不仅指责了当时中国社会之所以缺乏人才,是由于封建主义的科举制度造成的恶果;另一方面,他又批判了洋务派所谓的“变”只是重视讲求“练兵”、“开矿”、“通商”的办法,这不过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因而他在《变法通议》中明确地指出“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能尽利乎?”“商办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
他所以提出这一系列的质问,目的在于以此来说明洋务派是不知“变”的本末的。梁启超认为变法要有本末。怎样才算“知本”呢他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于开学校”。这就是说,中国欲求富强,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革,它的根本之途必须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
因此,梁启超在《教育政策私议》一文中大声疾呼“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即当道之言维新,草野之谈时务者,亦莫不汲汲注意于教育;然而此议之兴,既已两年,而教育之实,至今不举”。这确是令人十分焦急和慨叹的。
梁启超强调办教育,兴学校,应该注重基础教育。欧美各国在19世纪以后,都“确认教育之本旨,在养成国民,普之皮里达埒法夏哥士等,首倡小学最急之议。自兹以往,各国从风”。所以梁启超指出:“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他批评了当时清政府忽视小学、中学的建立,违背教育次序,先办大学堂,本末倒置。他认为:“求学譬如登楼,不经初级,而欲飞升绝顶,未有不中途挫跌者”。梁启超重视基础教育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和具有深远眼光的。
因此,梁启超在《教育政策私议》中,模仿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状况,设计了一个国民教育制度体系。他把教育分为4个时期: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6岁至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岁至21岁为少年期,受中学教育或与中学相等程度的师范学校或各种实业、专门学校的教育;22岁至25岁为成年期,受大学教育。大学分文、法、师范、医、理、工、农、商诸科。他绘制了一个《教育制度表》如图他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相互关系和性质也作了阐明:“教育之次第其不可以躐等进”。就是说,各级各类学校是相互衔接的,按学习程度递进,不能越级。他还指出,中学、小学、幼稚园属于普通教育范围。小学阶段为强迫义务教育,“子弟及岁不遣就学,则罪其父母”。而分科大学、师范学校、军事学校、美术学校、政治法律学校等,则属于专门教育范围。
梁启超所设计的这种国民教育制度体系,主要仿自于资本主义国家,自然它只能是切合地主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不要说大学、中学,一般劳动人民无法问津,就是义务教育性质的小学阶段,也长达八年,在当时,劳动人民的子弟也是难于享受的。不过从梁启超提出这个完整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民教育制度的思想立场来看,足以表明资产阶级维新派是怀有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坚强意志的。
对学校的经费,梁启超也给予极大的关注。梁启超参考欧美各国的经验:“由国家监督,立一定之法,而征地方税以支办其财政者也”。他提出了下列的建议和措施(1)“学校经费,皆由本校本镇本区自筹。其有公产者,则以公产所入支办之。其无公产或公产不足者,则征学校税,如田亩税、房屋税、营业税、丁口税等,或因其地所宜之特别税法,以法律征收之,以为创设学校及维持学校之用。惟其税目不得过两项以上(其仍有不足者,则禀请地方官酌由官费补助)。其有余者,则积为学校公产”。
(2)学校可收适量的学费,但数目应很少,国家可以规定一个限额,家境贫穷的学生,经查实后,可以免费。
(3)“既定征学校税,如有抗不肯纳者,则由教育会议所禀官究取”。
(4)凡每一学校区,设一会议所,负责管理教育经费。
梁启超的上述建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比较切合实际。
在教育行政管理方面,梁启超也建议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和方法,以保证学校具备一定的质量。
一是国家要加紧制定小学章程,详细规定学校的管理规章制度和课程设置,明确传授哪一些课目。颁发到各地区依令执行。
二是“教科书无论为官纂、为民间私纂,但能依国家所定课目者,皆可行用”。
三是加强视导制度。每省设视学官3-4人,每年分巡全省各学区。“视学官之职,当初办时,则指授办法;既立校后,则查察其管理法及功课。教师之良者,学生之优等者,时以官费奖赏之。其学校所有公产之数及出纳表,皆呈交视学官验视,但划其权限,不许干涉校中款项”。梁启超的这些见解也是很值得参考和研究的。
对教育的投资,梁启超比起其他维新派思想家、教育家来,可算是独具慧眼的。他曾向清政府大力呼吁,认为中国“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他并以欧美、日本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教育的大量投资为例,说“吾闻泰西诸大国学校之费,其多者八千七百余万,其少者亦八百万日本区区三岛,而每年所费,亦至八九百万人之谋国者,岂其不思撙节之义,而甘掷黄金于虚牝乎”。对比之下,他深感清政府眼光短浅,“不惜糜重帑以治海军,而不肯舍薄费以营学校”。梁启超这个批判是颇中时弊的。总而言之,梁启超的废八股、变科举、兴学校的思想,是顺乎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
(三)提倡女学和师范
在梁启超的“开学校”主张中,他特别重视开设“女子学堂”、“师范学校”和“政治学院”,显示了一个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教育家的真知灼见。
梁启超从主张男女平权、解放妇女的立场出发,积极提倡女子教育。他说:“男女平权,美国所盛;女学布蒬,日本以强”。
他批判了封建主义的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教育观点,并斥责这种观点乃“实祸天下之道”。他明确地指出:“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就是说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他认为,女子受教育的情况与国家盛衰是有密切关系的。“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因此,他对当时中国的妇女,“深居闺阁,足不出户”,阅历少,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深感忧虑。他希望能够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
为了实现他对女子教育的主张,他曾计划先在上海创办一所女子学堂,然后逐步推广到各省府州县。为此,他写了一篇《倡设女学堂启》,向当时的社会人士和教育界大声疾呼:“泰西女学,骈阗都鄙,业医课蒙,专于女师。同志之士,悼心斯弊,纠众程课,共襄美举,建堂海上,为天下倡”。他制订了《女学堂试办略章》,对女学堂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他还把日本的女子学校的课程设置向当时的中国教育界作了介绍:“日本之女学,约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言教授及蒙养之法),三国语(谓日本文),四汉文,五历史(兼外国史),六地理,七数学,八理科(谓格致),九家事,十习字,十一图画,十二音乐,十三体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梁启超能够排除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开设女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要改革和发展近代教育事业,必须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梁启超曾有“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的感慨。
为此,他竭力提倡师范教育,并把它当作是“群学之基”,即各类学校的基础,并且说:“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在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里就包括有从“寻常师范学校”到“高等师范学校”直至“师范大学”的比较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可见他对师范教育是十分重视的。
为此,他还详细的介绍了日本寻常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其所教者有十七事:一修身,二教育,三国语(谓日本文语),四汉文,五史志,六地理,七数学,八物理化学(兼声光热力等),九博物(指全体学动植物学),十习字,十一图画,十二音乐,十三体操,十四西文,十五农业,十六商业,十七工艺”。把它提供作为当时我国办师范学堂的参考。